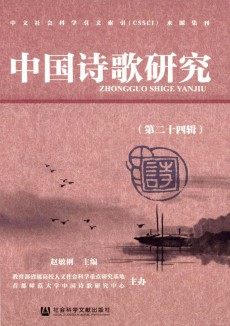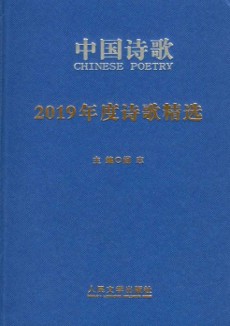诗歌的文学常识大全11篇
时间:2023-05-23 17:21:13
篇(1)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2-0030-02
作者简介:胡婷婷(1983―),女,安徽当涂人,本科学历,中学二级教师,安徽省当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一、高中诗歌写作教学的现状及原因
诗歌写作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甚至可以说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空白。中国有着悠久而优良的诗歌传统,但我们的现代教育恰恰背离甚至抛弃了这一传统。语文教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有关写作教学的文章亦比比皆是,但涉及诗歌写作教学的寥寥无几。诗歌教学从未停止,然诗歌写作教学几尽绝迹,这是诗歌的不幸,更是现代语文教育的不幸。
不妨先找找诗歌写作教学被我们集体“忽略”的原因。
首推社会因素。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深受社会影响的,学校教育教学的内容由社会需求决定,教育教学氛围也受制于社会风气。经济大潮对价值观形成冲击,“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已不复存在,诗歌被边缘化,浮躁与功利早已使诗心荡然无存。其次是高中写作环境的影响。前些年的考试作文写作要求中最常见的几个字是“诗歌除外”,近年在这方面有所改变,但是将作文写成诗歌是万万得不到鼓励的。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表达与交流”部分可以看出,留给诗歌的写作空间也不多。最后要看诗歌自身。对以“快速”“直接”为特点的现代社会来说,艰涩朦胧甚至不知所云的诗歌很难受到青睐。看来,这种“忽略”真不是无心的。
二、高中诗歌写作教学缺失的危害
一种传统,如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向消亡已是必然,即便它曾经辉煌灿烂,我们也不必惋惜。但现在的问题是:诗歌闪耀着我们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没有了诗歌写作教学我们会失去什么?
高中诗歌写作教学的缺失对学生语文素养、个性心理以及健全人格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表达与交流”中指出:“力求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诗歌语言集中体现着修辞性、“破坏性”和节奏性的特点,如果诗歌写作淡出我们的视野,势必对表达个性化、创意性产生影响,对学生个体的特长和兴趣是一种压制,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这显然违背了教育的初衷。
青少年与诗歌有着天然的联系。青少年的思维最活跃、最敏锐,对生活、对人世的体验又非常有限,不太具备深刻理性的逻辑思维。诗歌创作最讲究想象联想,是感性智慧流露于笔端的最佳表现形式。所以诗歌写作是符合青少年的思维特点的,契合了他们的写作心理。相比较其他文体而言,古今中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少年早慧者不在少数。我们的教育不是只为培养诗人,但年轻的学子应该与诗结缘。
中国古老的“诗言志”的旗帜,被一代代诗人和诗论家高举并传递,它赋予诗歌以思想美,是诗歌的灵魂。白居易《与元九书》对诗的解读非常精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中学生的心灵空间需要这些人文素养来滋养,诗歌对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和美的心灵,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笔者看来,中学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读书人、文化人。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包含文化的色彩和诗性的光辉,斩断了这个因缘,无异于让年轻的心灵荒芜,无异于割断了民族文化的血脉!
三、对诗歌写作教学应该持有的态度和努力方向
首先,语文教师要坚守诗歌写作教学,克服思想观念中厚此薄彼的倾向。诗歌写作教学要本着全面提高学生、发展学生的理念,将诗歌写作变成教师教学意识的常态,进而变成教学实施的常态。教师选取诗歌的面应更广,如将当代诗歌纳入中学生的视野;同时解除学生的思想枷锁:诗歌人人都可以写,而且也可以写好。诗歌之于教学,不再只是再创造,还有原创。将诗歌评分纳入到作文评分标准之中,考试的大门向诗歌写作敞开,优秀的诗作一样能拿高分。每个教育工作者若能转变思想,假以时日,诗歌写作对于我们的学生就不再陌生,语文教学也会更健康地发展。
其次,语文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诗歌写作教学之所以被“忽略”,恐怕是它戳到了我们的痛处:诗歌写作有难度,诗歌写作教学不易实施。当诗歌写作并不是必须要越过的山,又有它途可以绕行时,起初的难堪很快被遗忘,甚至立上“此路不通”的标牌。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我们任由这处绝佳景致荒芜。如果任由这种现状继续,的确是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悲哀和耻辱。薪火相传,语文教师须身体力行。语文教师除了要精通诗歌表达方式的赏析、诗歌言志缘情的领悟,更要会写诗,会指导学生写诗,对学生的创作予以正确有效的推进。语文教师对诗歌的认识还应是全面完整的,除了深刻懂得诗歌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外,还要深入了解现当代诗歌状况甚至是当下中国诗坛的尴尬,能站在历史的角度予以审视,带领学生去探究把脉。所以,语文教师要注意自身知识结构的平衡。
有了思想观念的突破和专业知识的加强,在摸索中实施教学,还有许多东西需要语文教师去探索。例如:学生对诗歌写作的认识和兴趣,诗歌写作与现有诗歌教学的衔接,诗歌写作与鉴赏的互动,诗歌写作的指导思想,诗歌写作对传统的继承和对现实的观照,诗歌的个性化写作等。智慧的语文教师当然会出色地攻克一个个难题,使语文教学更加熠熠生辉。
四、诗歌写作教学的现实意义
很多语文教育工作者都不看好诗歌写作的现实意义,这是认识上的误区。诗歌写作之于语文、之于社会,从来就没有丧失它应有的功能。
诗歌写作能促进学生诗歌鉴赏水平的提高。对诗歌具有必要的鉴赏能力利于诗歌写作,也只有让学生切身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完成了诗歌创作者的心路历程,由己推人,才更能与诗人产生共鸣。而这种共鸣与提高,来自于学生的自身经验,不是老师强加的,因而记忆更深刻、持久,学生也会从中收获学习的乐趣。
诗歌写作教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必然要求,是拉近诗歌与生活的距离的重要基础,是学生表达自己、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中国是诗歌大国,诗意曾深深根植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当代诗歌的衰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曲高和寡”的结果,“曲高”是相对而言的,“和寡”是症结。语文教育要在受教育者心中播下诗歌的种子,并培育其生根发芽。诗歌写作教学会给当前诗坛注入一份关注、一份争鸣。
总之,每一位一线语文教师都要更新高中诗歌写作教学的观念,让诗歌写作教学成为一种教学常态。诗歌写作教学会使我们的语文教学更加健康,使语文与传统及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以提升、人格更加健全。
参考文献:
篇(2)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在于坚的诗学观念中,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并深刻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然而,由于二元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于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实际上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悖论,其诗学观念因而也就不适合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用来评判当下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了。
一
在《棕皮手记•1996》一文中,于坚探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文译名的译法,他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1]10笔者以为,这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述恰似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可以在于坚的诗学随笔及批评文章中,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存在,进而理解于坚的诗学观念。
(一)有意义无意义
通过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一书中文译名的讨论,于坚事实上已经发掘出了“有意义”与“无意义”这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 [1]10,“对于历史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对于个人最有意义的东西。” [1]12而“《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1]10。因此,他主张在写下的文字里寻找失去的无意义的时间,而不是追忆“逝水”一般的有意义的年华。基于此,于坚的《棕皮手记•1996》一文里出现了以下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二)历史日常生活
在从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无意义的生活”予以肯定、进而否定“有意义的年华”的基础上,于坚进一步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对立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1]11由此,他反对书写有意义的、形而上的、对存在实行遮蔽的“有结论的历史”,提倡写作无意义的、形而下的、有细节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可能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回到过去的方法” [1]12。“历史”与“日常生活”,是我们可以在于坚的诗学批评中见到的又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三)集体记忆私人记忆
与上述两组二元对立因素有关,“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也是于坚诗学观念中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因素。其中,“集体记忆”与上述“有意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私人记忆”则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的内心或者说诗学观念里,生长着这样的焦虑:“记忆变成了仅仅对集体的所谓闪光的时刻的储存,这种储存又支配着作家们的能指。这样,从相同的价值认同出发的记忆,统一所有人的记忆,人们实际上成了没有记忆的人”[1]11,而“没有私人细节的记忆实际上只是遗忘” [1]12,所以,“历史的记忆方式是对存在的遮蔽” [1]12。于坚指出,为了不遗忘,就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 [1]12,在写作中反对“集体记忆”对“私人记忆”也即存在的遮蔽。
(四)知识写作神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与“知识分子诗人”的论争中,代表“民间诗人”发言的于坚在上述三组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知识写作”与“神性写作”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明确提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2]13-14
这一段话,于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说了很多遍,我们可以在《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等文章里一再发现,于坚数次原封不动地、认真地把这一段话镶嵌进这些文章里去,来表达他对其所谓的“把诗歌变成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2]13的“知识写作”的抨击与不妥协。
联系到于坚在1999年“盘峰诗会”前后相关文字里对自己诗歌处境的近乎不满的描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种强烈的被官方和所谓主流话语遮蔽的焦虑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于坚,促使他发掘出了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并对其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作了几乎不加限制的肯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对其中的前一类因素,如有意义、历史、集体记忆、知识写作等,进行了否定。也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执的选择、坚持和张扬最终形成了于坚诗歌写作的特点。
二
在一系列的诗学批评文章中,于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以“此岸”对抗“彼岸”的诗歌意识,指导着他的诗歌写作,影响着他的诗歌视角和诗歌姿态,以及其诗歌具体的操作方式,其诗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从80年代早期写的以云南高原为背景的诗作,到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写作,再到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诗作”[3],明显的,于坚诗歌写作轨迹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前所述,于坚对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进行了发掘、坚持和张扬,而这样的发掘、坚持和张扬势必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于坚的诗歌因而更关注私人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非常自觉地,于坚试图在他写下的诗歌里消解被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所谓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通常是被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所赋予的。因此,在具体的写作上,于坚的诗歌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种不同寻常的实验,于坚说:“我主张一种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度的诗。”[4]他说,我希望的是“清醒的,不被语言所左右的,拒绝升华的中性的写作”[1]6。
在这样一种自觉的、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于坚的诗歌在诗歌取材、诗题上出现了一种“系列”与“符号”方式(如《作品第××号》,和《事件》系列)[5]219,这样一种中性的诗题模式,显然与他要求诗歌回到“日常生活”、“私人记忆”有关,并由此形成了其诗歌“朴素、直接的口语写作” [5]219倾向,在《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女同学》以及《芸芸众生》组诗里,于坚的诗歌呈现出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经验的大面积敞开,而这些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口语化的觉醒与坚持,在长诗《档案》的写作里更是达到了极致,“《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6]443。大量中性的词语的简单堆砌和不厌其烦的排比,反而造成了一种意外的张力,真实地定义并且客观地叙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迹。
于坚在此间接、直接引用艾略特的诗句,表明这六行诗句里所说的“那个作者”,正是对于中国诗人的写作曾产生重要影响的艾略特。若稍加引申,“那个作者”当喻指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的西方诗人。
(2)“间或也用英语交谈”一句,系引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诗人王家新文章的原句。1998年,王家新曾在《“中国”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一文中,叙述了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同法国当代“新抒情诗派”诗人让-米歇尔•莫普瓦(jean-michel maulroix)会谈的过程,文中有“间或,我们也直接用英语交谈”这样的句子。于坚在此引用此句,有着明显的讥诮意味,暗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
(3)“会吸引了这么多平平仄仄的读者”一句中,“平平仄仄的读者”当喻指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而“这么多”一词,虽系引自查良铮译《荒原》的原文,但在这短短的六行诗句里,已是第三次出现,频率之高,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引用,而带有某种讥诮的意味了。
综合以上诸点,可以发现,《飞行》中的这六行诗句,实则是暗喻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受到了西方诗歌太多的影响,而于坚则以饱含讥诮的口吻对此表达了轻蔑与不满。姑且不论于坚在这六行诗句里体现出来的不满是否饶有价值,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已经不是于坚所坚持的度的、中性的写作了,而是升华的、充满了隐喻的、有结论的写作了。我们惊讶地发现,于坚的诗歌在这里走向了他自己的诗学观念的反面。这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于坚尖刻、不安、大有深意,但是离他自己所倡导的诗歌标准却越来越远了。
五
本文最后想总结的是,拒绝隐喻,拒绝升华,拒绝书写有意义的、有结论的历史,拒绝呈现集体记忆的诗歌努力,作为于坚个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选择和坚持,在当代诗坛上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但是,于坚这一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却应避免作为一种绝对的单一标准,用来评判当代诗人(包括于坚自己)的诗歌。如果于坚因为自己诗学观念的独特价值,就不假思索地借此为矛,刺向不同道路上的诗歌写作者,对其他诗人写作道路的选择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那么,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是对于整个汉语诗坛而言,都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不论于坚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写于1998年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于坚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给“知识分子写作”定性,指其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2]7,指其是“平庸、萎缩、僵硬、小聪明、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蒙羞的垃圾”[2]9,多少显得有点偏激,不能令观者信服。可以说,于坚诗学观念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虽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但是由于这一思维模式自身简单、粗暴的先天缺陷,却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于坚和他的读者走向他自己的反面,令其陷入奇怪的悖论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无论如何,这大约是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不得不始终要面对的、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参考文献:
[1]于坚.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于坚.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3]谢有顺.于坚的诗:站在诗歌的反面[n ].南方周末,2001-04-26(18).
[4]于坚.磁场与魔方[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11.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张柠.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7]李振声.季节轮换[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王光明.以个人方式包容世界——90年代的中国诗歌[j].花城,2002(1):197-208.
[9]伊沙.于坚:喧嚣内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柏桦.从主体到身体——关于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倾向性[j].当代文坛,2005(5):44-47.
[11]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篇(3)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在于坚的诗学观念中,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并深刻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然而,由于二元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于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实际上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悖论,其诗学观念因而也就不适合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用来评判当下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了。
一
在《棕皮手记?1996》一文中,于坚探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文译名的译法,他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1]10笔者以为,这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述恰似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可以在于坚的诗学随笔及批评文章中,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存在,进而理解于坚的诗学观念。
(一)有意义无意义
通过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一书中文译名的讨论,于坚事实上已经发掘出了“有意义”与“无意义”这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 [1]10,“对于历史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对于个人最有意义的东西。” [1]12而“《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1]10。因此,他主张在写下的文字里寻找失去的无意义的时间,而不是追忆“逝水”一般的有意义的年华。基于此,于坚的《棕皮手记?1996》一文里出现了以下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二)历史日常生活
在从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无意义的生活”予以肯定、进而否定“有意义的年华”的基础上,于坚进一步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对立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1]11由此,他反对书写有意义的、形而上的、对存在实行遮蔽的“有结论的历史”,提倡写作无意义的、形而下的、有细节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可能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回到过去的方法” [1]12。“历史”与“日常生活”,是我们可以在于坚的诗学批评中见到的又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三)集体记忆私人记忆
与上述两组二元对立因素有关,“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也是于坚诗学观念中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因素。其中,“集体记忆”与上述“有意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私人记忆”则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的内心或者说诗学观念里,生长着这样的焦虑:“记忆变成了仅仅对集体的所谓闪光的时刻的储存,这种储存又支配着作家们的能指。这样,从相同的价值认同出发的记忆,统一所有人的记忆,人们实际上成了没有记忆的人”[1]11,而“没有私人细节的记忆实际上只是遗忘” [1]12,所以,“历史的记忆方式是对存在的遮蔽” [1]12。于坚指出,为了不遗忘,就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 [1]12,在写作中反对“集体记忆”对“私人记忆”也即存在的遮蔽。
(四)知识写作神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与“知识分子诗人”的论争中,代表“民间诗人”发言的于坚在上述三组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知识写作”与“神性写作”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明确提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2]13-14
这一段话,于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说了很多遍,我们可以在《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等文章里一再发现,于坚数次原封不动地、认真地把这一段话镶嵌进这些文章里去,来表达他对其所谓的“把诗歌变成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2]13的“知识写作”的抨击与不妥协。
联系到于坚在1999年“盘峰诗会”前后相关文字里对自己诗歌处境的近乎不满的描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种强烈的被官方和所谓主流话语遮蔽的焦虑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于坚,促使他发掘出了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并对其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作了几乎不加限制的肯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对其中的前一类因素,如有意义、历史、集体记忆、知识写作等,进行了否定。也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执的选择、坚持和张扬最终形成了于坚诗歌写作的特点。
二
在一系列的诗学批评文章中,于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以“此岸”对抗“彼岸”的诗歌意识,指导着他的诗歌写作,影响着他的诗歌视角和诗歌姿态,以及其诗歌具体的操作方式,其诗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从80年代早期写的以云南高原为背景的诗作,到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写作,再到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诗作”[3],明显的,于坚诗歌写作轨迹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前所述,于坚对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进行了发掘、坚持和张扬,而这样的发掘、坚持和张扬势必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于坚的诗歌因而更关注私人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非常自觉地,于坚试图在他写下的诗歌里消解被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所谓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通常是被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所赋予的。因此,在具体的写作上,于坚的诗歌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种不同寻常的实验,于坚说:“我主张一种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度的诗。”[4]他说,我希望的是“清醒的,不被语言所左右的,拒绝升华的中性的写作”[1]6。
在这样一种自觉的、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于坚的诗歌在诗歌取材、诗题上出现了一种“系列”与“符号”方式(如《作品第××号》,和《事件》系列)[5]219,这样一种中性的诗题模式,显然与他要求诗歌回到“日常生活”、“私人记忆”有关,并由此形成了其诗歌“朴素、直接的口语写作” [5]219倾向,在《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女同学》以及《芸芸众生》组诗里,于坚的诗歌呈现出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经验的大面积敞开,而这些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口语化的觉醒与坚持,在长诗《档案》的写作里更是达到了极致,“《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6]443。大量中性的词语的简单堆砌和不厌其烦的排比,反而造成了一种意外的张力,真实地定义并且客观地叙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迹。
于坚在此间接、直接引
用艾略特的诗句,表明这六行诗句里所说的“那个作者”,正是对于中国诗人的写作曾产生重要影响的艾略特。若稍加引申,“那个作者”当喻指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的西方诗人。
(2)“间或也用英语交谈”一句,系引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诗人王家新文章的原句。1998年,王家新曾在《“中国”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一文中,叙述了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同法国当代“新抒情诗派”诗人让-米歇尔?莫普瓦(Jean-Michel Maulroix)会谈的过程,文中有“间或,我们也直接用英语交谈”这样的句子。于坚在此引用此句,有着明显的讥诮意味,暗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
(3)“会吸引了这么多平平仄仄的读者”一句中,“平平仄仄的读者”当喻指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而“这么多”一词,虽系引自查良铮译《荒原》的原文,但在这短短的六行诗句里,已是第三次出现,频率之高,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引用,而带有某种讥诮的意味了。
综合以上诸点,可以发现,《飞行》中的这六行诗句,实则是暗喻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受到了西方诗歌太多的影响,而于坚则以饱含讥诮的口吻对此表达了轻蔑与不满。姑且不论于坚在这六行诗句里体现出来的不满是否饶有价值,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已经不是于坚所坚持的度的、中性的写作了,而是升华的、充满了隐喻的、有结论的写作了。我们惊讶地发现,于坚的诗歌在这里走向了他自己的诗学观念的反面。这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于坚尖刻、不安、大有深意,但是离他自己所倡导的诗歌标准却越来越远了。
五
本文最后想总结的是,拒绝隐喻,拒绝升华,拒绝书写有意义的、有结论的历史,拒绝呈现集体记忆的诗歌努力,作为于坚个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选择和坚持,在当代诗坛上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但是,于坚这一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却应避免作为一种绝对的单一标准,用来评判当代诗人(包括于坚自己)的诗歌。如果于坚因为自己诗学观念的独特价值,就不假思索地借此为矛,刺向不同道路上的诗歌写作者,对其他诗人写作道路的选择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那么,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是对于整个汉语诗坛而言,都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不论于坚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写于1998年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于坚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给“知识分子写作”定性,指其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2]7,指其是“平庸、萎缩、僵硬、小聪明、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蒙羞的垃圾”[2]9,多少显得有点偏激,不能令观者信服。可以说,于坚诗学观念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虽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但是由于这一思维模式自身简单、粗暴的先天缺陷,却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于坚和他的读者走向他自己的反面,令其陷入奇怪的悖论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无论如何,这大约是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不得不始终要面对的、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参考文献:
[1]于坚.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于坚.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3]谢有顺.于坚的诗:站在诗歌的反面[N ].南方周末,2001-04-26(18).
[4]于坚.磁场与魔方[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11.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张柠.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7]李振声.季节轮换[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王光明.以个人方式包容世界——90年代的中国诗歌[J].花城,2002(1):197-208.
[9]伊沙.于坚:喧嚣内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柏桦.从主体到身体——关于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倾向性[J].当代文坛,2005(5):44-47.
[11]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篇(4)
在众声喧哗的当代诗坛,江苏诗歌的姿态则显得相对安静。每个业已成熟的诗人都有自己创作的个体差异,同时江苏诗歌整体呈现出来的精致、恬淡、平和,构成了江苏诗歌有别于其他省份的一种特殊品质。
罗振亚认为,在一些诗歌远离读者、远离生活的时候,江苏的诗人们正在有策略地全方位“及物”。他们注意协调诗和现实的关系,从自身视点出发,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和感受,呈现“此在”处境和经验。与此同时,他们致力于艺术技巧和思想深度的打造,对时尚和流行的写作风气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和警惕,钟情于艺术自身品位的经营和提升,沉稳内在地多方寻找诗歌艺术的可能性。
霍俊明认为,新世纪诗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日常诗学”的写作趋向,诗歌的写作背景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但这一过程在江苏诗歌中并不意味着诗人耽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反而显示了他们努力超越和拒绝琐屑日常生活的思考。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新的意味和精神。
“南方诗歌”精神的诗学价值
不少与会者认为,新世纪以来江苏的诗歌写作充分说明了地域性和文化根性对于诗人写作的重要性。
何言宏专门阐发了“南方诗歌”的主要特征与诗学价值。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进程中,需要对往昔的传统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不断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更加广阔的精神关怀与现实指向。比如江苏诗人在运用语言的时候,就成功地表现出了吴文化的特点,体现出诗体的优雅和意象的精致。
也有论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傅元峰认为,对“南方精神”的探询,现阶段能够从文本中确切归纳的只是诗歌的某种自由姿态或自由精神。这种诗歌本质的获得和地理方位以及地域并没有直接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地域风格诉求在理论与文本上都有所体现,但并没有取得更大的美学突破,恰恰是强化了文学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特征。
何平认为,新世纪的诗人写作中,“南方”和“北方”没有必要构成一种对抗。诗歌写作不是拟想中的文化认祖归宗,更引起关注的是当下诗歌书写的复杂性经验。
当代诗歌要保持自己的文体边界和精神尊严
与会者还对中国当代诗歌及江苏诗歌发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诗歌标准的缺失、诗歌与现实生活对话能力的缺失等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观念看似繁复多元,诗歌写作也是在差异和多个向度展开,但近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已经说明,诗歌问题已经不单纯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当代诗歌如何保持自己的文体边界和精神尊严,需要诗歌界时时警醒。
篇(5)
目前中学生欣赏英语诗歌的能力有所缺乏,究其原因是他们对英语诗歌的基础知识了解不够,不知道如何去欣赏英语诗歌。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英语诗歌的相关基础知识。
1.英语诗歌的主题
英语诗歌的主题包括节日,感情,地方,人类,动物,自然等。
2.英语诗歌的种类
语言是不断变化的,英语诗歌就像中文诗歌一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诗歌的形式、内容和押韵手法上不断更新。从诗歌的表现手法上大致可分为戏剧诗dramatic、史诗epic、故事诗metrical tale、民谣ballad(包括童谣nursery rhyme)、颂歌ode、挽歌elegy、十四行诗sonnet、说理诗didactic poems、模仿诗parody、打油诗clerihews、徘句haiku、五行诗cinquain、清单诗listing poem、自由诗(free verse)和个体诗individual。从诗歌的内容上来看略分为叙事诗narrative和抒情诗lyrics两种。
3.英语诗歌的韵律
英语诗歌的音乐性除了来自节奏外,还来自韵律,即两行或更多的行压韵。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与中文诗一样,英文诗也出现许多新体诗,这些诗也不太讲究押韵了。对高中生而言,笔者认为只需辨别英语诗歌的首韵和尾韵的押韵方式便可。首韵即指诗歌的每一行都有两个词是想同的,常出现的尾韵为交叉韵型(ABAB)、联韵型(AABB)和同韵(一韵到底,大多是在同一节诗中共用一个韵脚)。如以下这段诗歌:
I saw a fish-bond all on fire,
I saw a house bow to a squire,
I saw a person twelve-feet high,
I saw a cottage in the sky.
这段诗歌的每行都有I saw a,这就是首韵。这段诗歌一二两行结尾fire与squire都押了/ai /韵,三四两行high 与sky都押了/ai/韵。这是典型的AABB形式。
又如以下这段诗歌:
Out of the bosom of the air,
Out of the cloud-folds of her garments shaken,
Over the woodlands brown and bare,
Over the harvest-fields forsaken.
这段诗歌第一、三两行结尾air与bare都押了/ /韵,第二、四两行shaken 与forsaken都押了/k n/韵。这是典型的ABAB形式。
在指导学生掌握英语诗歌的韵律知识时,笔者会让学生自己先朗读一遍,试着找出押韵的单词,还让学生比较自己更熟悉的中文诗歌的韵律,从而使他们的印象更深刻。有时也让学生将打乱的诗句还原,就是让学生根据诗歌的韵律去寻找对句,根据诗歌语言的特点去还原,他们会不断的朗读,去探索和发现合适的排列方式
二、引导学生学会品读英语诗歌
在学生熟练掌握英语诗歌韵律后,笔者在平常的教学工作中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注重培养学生朗读英语诗歌的能力。
1.让学生自己默读一遍,找出诗歌押韵的单词,在轻读中整体感受诗歌的韵律。
2.针对这首诗中的一些知识点和语法点,设置几道选择题,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诗歌的内容。
3.用多媒体设置情境,展现诗歌及诗歌中描述的画面,只听诗歌朗读录音而不读。让学生初步感知诗歌的意境,酝酿朗读诗歌的情感。
4.听诗歌录音,让全班一起大声跟读诗歌。激励所有学生开口朗读,增强诗歌感染力。再让学生自读诗歌,同伴互相聆听纠错。
5.放音乐伴奏,个别学生美读诗歌。音乐与诗歌的有机结合可以增加学生朗读的乐趣,渲染朗读的气氛,更能体现诗歌的美感。
三、将英语诗歌用于课前导入
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笔者注重将英语诗歌用于课前导入,并起到很好的效果。
1.让学生翻译他们熟悉的诗人的著名诗句,并在句中嵌入要讲解的词组,句型和语法,这样能提高学生学习枯燥的语法点和知识点的兴趣,更有利于他们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2.在讲解与诗人有关的课文及诗歌时,笔者会布置学生在课前通过书籍和网络对诗人生平及诗歌写作背景进行相关了解,然后在课堂上检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四、中英文士诗歌互译
挑选一些学生熟悉的较简单的诗歌让学生进行中英文诗歌互译是扩宽学生词汇量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曹植的《七步诗》,先让学生自己通过查字典或者让学生在课本上寻找一些词组和句型进行简单的字面上的翻译,再让学生修改个别单词来押韵,然后将自己的译诗读给同桌听。以下是该诗的参考译文:
They were boiling beans on a beanstalk fire,
Came a plaintive voice from the pot,
“ Oh, why since we sprang from the self-same root,
Should you kill me with anger hot?”
五、开展诗歌兴趣小组,写诗,吟诗和品诗
篇(6)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22-03
海子作为我国著名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更加强调对于新鲜事物的体会,突出不同事物在观赏者眼中的质感,强调诗人心中情感。陌生化是海子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已经成为海子诗歌的特点。陌生化一词首次提出是在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创作中,主要是希望改变人们生活的单一性,让人们对于新鲜事物重新获取兴趣,真正体验生活百态。什克洛夫斯基强调:“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1]”。在文学创作中使用陌生化技法,能够提升诗歌内涵,拓宽诗歌表现形式,培养读者文学审美能力。海子在文学创作中已经将陌生化技法运用灵活,充分表现出海子精神世界。
一、海子简介
海子原名为查海生,出生在我国安徽省,是我国80年代中期著名的诗人,海子是在进入北京大学校园后开始的诗歌创作,由于海子特殊的精神世界,最终在1989年,海子选择卧轨自杀的方式结束其一生。海子仅仅创作了7年的诗歌,但是却为人们留下大量优美的诗歌,例如《亚洲铜》《夜色》《祖国(或以梦为马)》《春天,十个海子》《黑夜的献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
海子诗歌的创作特点就是能够带领诗歌欣赏者走入海子精神信念中,了解海子所想要表达的永恒情感。海子在诗歌中实际将永恒表现具体化,让人们对于生命本质深度探究,海子诗歌为诗歌欣赏者营造出来一个海子眼中的生命本质情境,让人们能够眺望远方[2]。
海子的诗歌全部都是抒情类文学作品,对于生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了海子所特有的情感,在对海子诗歌欣赏中可以发现,海子诗歌是思想角度分析,海子是一个思想矛盾体,不仅仅能够将世界中的事物具体性表现,还能够将事物浪漫话、写意化。
二、陌生化技法生活反常化
陌生化技法在实际使用中就改变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传统的观念,强化了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人们只要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就能够为陌生化的文学作品所影响,最终于潜意识中冲击人们惯性的思维[3]。
海子诗歌就能够很好说明这一观念的。诗歌是诗人为读者提供的一个艺术氛围,更是诗人眼中的世界。海子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明白陌生化的重要性,因此海子诗歌为人们展示的是海子精神世界,并不是直接告诉人们一些人生道理。在海子的诗歌中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春暖花开的世界,人们在诗歌欣赏中都能够对理想中的世界有一个新认识。在别人眼中未来的生活可能是迷茫的,但是在海子眼中未来却是一个能够创造幸福的远方。在海子诗歌欣赏过程中,迷茫的人们对于未来生活有了新的动力,更加愿意探索生命中的美好,了解生命的真谛。海子诗歌中所描述出的未来生活,在人们眼中是那样熟悉与陌生,帮助人们潜在的理想浮出水面,让人们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4]。
诗歌是这样,生活更是这样。人们都能够对生活有着新鲜的认识,推动人们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就像人们厌倦了传统的诗词后,就有了诗歌。特色是一件产品被人们所熟知的基础,陌生化是人们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特殊性表现形式,也成为了文学创作中的核心技法。
三、海子诗歌中陌生化技巧表现
海子在诗歌创作中,无形的将陌生化巧妙融入其中,让海子诗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陌生化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技法形式,能够让人们对于已经熟悉的事物有着全面的认识,人们对于事物重新感觉到新奇,增加文学作品美感。
(一)异化现实
异化现实在文学作品创作中使用陌生化技法的直接性原因,陌生化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突出性的表现形式。
1.决绝后的坦白
海子在诗歌创作中重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在诗歌中更是将这种想法表现的淋漓尽致。海子在诗歌中将生命本质抽象化的表现,同时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再次带向一个新高度。物质生活对于人们生活影响逐渐增加,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关注物质生活水平,道德伦理已经发生了异化。海子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改变感受深刻,创作出了“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这样的诗歌,表现出海子在尊重每个个体独立物质需求的同时,努力保持自身生活需求,厌恶与其生活在同一个空气中的想法。在人与人不断接触中,人们逐渐忽视对于人性的关注,往往在他人身上找到自身生活的价值,在个体无法确认自身价值时,就会陷入深深的迷茫中[5]。
在海子诗歌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社会生活对于人们的影响,海子批判了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的改变,逐渐忽视自身价值,个体不断异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丰富物质需求的同时,对于人们精神世界也是一种束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身特性。海子的诗歌就能够直观反映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以及海子对于这种变化的无奈。
2.反叛中的保留
海子对于生命本质解剖中,对于人的内心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了解中经常需要直接面对生命中丑陋的一面。海子对于生命本质探讨中,更是无法躲避生命丑陋一面的问题,但是海子厌恶生命中丑陋的一面,同时还承认生命丑陋能够促进人们精神世界的建设,正是人们拥有了生命丑陋的一面,才可以让人们对于自身有着更彻底的认识,才能鞭策人们不断向前、向上。
在海子的诗歌中,对于生命丑陋可以说是最大化的夸张,海子甚至写出了“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这种诗句。丑陋的世界创作出丑陋的文学作品,但是人们在丑陋的社会中,还存在异化性的心理,也是海子诗歌所想要为人们所表现出的、他的精神世界。海子诗歌就是以这种异化的特点所被人们了解,在海子《秋日黄昏》中曾经写道“从此再不提起过去,痛苦或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种诗句,表现出现实生活中每天所需要面对的痛苦或幸福,用更加清醒的头脑生活[6]。
3.沉沦里的依恋
海子诗歌是有大量对于现实生活批判性的诗句,但是主要还是对生命的歌颂,探索生命的真谛。就如海子所说的“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种对于未来生活美好的畅想,这是海子在凡俗生活中对于生活的依恋。这种依恋是海子精神世界中无形的表现,是海子眼中的未来世界。海子更加关注对于人们心灵变化的了解,对诗歌创作中明确自身创作风格,需要诗歌对人们带来的情感。
在海子创作诗歌中,海子也在不断对自身成长进行反省,了解自身想法,进而创作诗歌。海子诗歌可以说是海子精神世界及自我认识的集中体现,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海子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反省中具有反叛精神。文学创作虽然提倡多元化共存,但是最终还是希望文学创作回归到人性中,探索人的价值,了解生命的意义,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海子在自身反省中也曾经出现过迷茫,甚至是自我否定的时刻,例如海子在《九月》中就曾写到“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在对海子诗歌分析中应该了解海子诗歌中的陌生化技法,关注海子关注的对象[7]。
(二)海子诗歌中陌生化表现
在海子诗歌欣赏中,人们经常能够发现海子诗歌的特点,能够有效说明海子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能。海子通过对于生命真谛的探索,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海子眼中生命的真谛,让人们对于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
1.言说策略
任何文学在创作中都是人们语言作用下的成果,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交往重要的工具,基于语言交往的交际关系更加局限,正是由于交际关系的局限让人们对于陌生化有了重新的认识。
海子在诗歌创作中经常通过第三方的言语将海子所想要表现的情感表现出来,例如海子在《麦地与诗人,询问》中就写道“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人们在欣赏海子诗歌中,会在无形中进入海子为人们营造的环境中,用海子的语言表现出海子对于这个世界的不满,对于这个世界的呐喊。言说策略能够缓解人们在诗歌欣赏过程中的语言障碍,让人们对于语言表现形式有着新的认识,丰富人们精神世界[8]。
2.审美观念
海子诗歌中为人们营造出了一个人们所没有想象到的世界,让人们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美感。海子诗歌用文学审美重新审视这个社会,在海子眼中社会应该是平和、安宁的,人们都能够在每天生活中感受生活,对于自身有着重新认识,感受生活中的点滴快乐。人们的精神世界本来就不应该用外界的因素进行约束,应该在精神社会中无拘无束活动。在人们对于社会感觉到迷惘的过程汇总,海子对于这个世界全新认识,将生活中的美好尽情放大,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探索生命的真谛。
3.创作技巧丰富
海子对于生命及自身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后,会选择一种自身认为最适合的情感表现形式,因此海子选择了诗歌,也可以说是诗歌选择了海子。海子在诗歌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技巧,让人们对于海子精神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了解海子诗歌中所想要表现的情感。陌生化技巧丰富了海子诗歌创作途径,让海子诗歌创作更加丰富,也丰富了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触动人们探索生命真谛的想法,同时为人们呈现出不同的海子[9]。
四、结论
本文对于陌生化技法在海子诗歌中进行简单分析,了解海子诗歌创作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特点,了解陌生化技巧在海子诗歌中的表现意义。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A].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56.127.
〔2〕申玮.“玄学诗人”约翰・邓恩诗歌中的“陌生化”技巧[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06):79-81.
〔3〕王红涛,武娜.形式主义批评理论视域下看古诗中“陌生化”技巧的运用――以“诗鬼”李贺为例[J].海外英语,2015,(13):182-183.
〔4〕陈燕.蕴含在混乱表面之下的意蕴和谐――论卡明斯“古怪的印刷体式”诗歌的“陌生化”技巧[J].太原大学学报,2011,(02):61-63.
〔5〕赵志.论穆旦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技巧――以《诗八首》为例[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01):19-20.
〔6〕肖曼琼.“陌生化”: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翻译[J].外语教学,2008,(02):93-96.
篇(7)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诗歌的教学不同于常规的课文教学,其实际教学任务的开展不仅仅需要强化学生对于诗歌中出现的基础知识进行有效的把握,还要提升学生对于诗歌的阅读、品味的能力,进而为学生体味诗歌的意境提供有效的保障。因此,高中诗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要注重教学的方式方法,以有效的措施来不断的推进学生诗歌阅读与品位的能力。随着国家对于高中教育的重视与扶持,大多数高中都完成了多媒体教学工具的配备,而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资源的丰富化,教师备课资源的获取渠道也更加的便捷。因此,在现代化教学的背景下,教师一定要有效的搜集教学资源,进而借助教学资源的帮助,以跟读、阅读、朗诵的形式强化学生对于诗歌意境的体味。
例如在《再别康桥》这首现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可以以正常的备课内容保障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可以借助网络工具来下载相关的配乐诗朗诵以及单独的背景音乐。进而在基础知识教学工作完成后,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为学生播放标准的《再别康桥》朗诵录音,以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跟读感受诗歌的意境。同时,在学生掌握基本感情的表达方法后,教师也可以邀请部分的学生以配乐朗诵的进行来体味整首诗歌,进而再次强化学生对于诗歌情感的把握以及对于诗歌意境的体味,为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效果的发挥提供有力的保障。
2.教学过程中抓住有效的契机,指导学生进行模仿写作,引导学生直观感受诗歌意境
诗歌意境的体会当然不仅仅在于对于诗歌的重复朗读,很多时候,高中课堂上,教师对诗歌的拆借、诗歌含义的解读以及诗歌写作手法的讲解同样能够提升学生对于诗歌整体把握的能力,进而强化学生感受诗歌意境的能力。因此,在诗歌教学的过程中,一线的语文教师应当注重对于诗歌的讲解尤其是诗歌写作手法的教授,进而在教学的过程中,把握相关的契机来让学生进行诗歌的模仿写作,以诗歌的写作以及情感的表达,引导学生直观的感受诗歌美好的意境。
高考结束后,很多学生都会远离家乡去其他城市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而这一美好而又伤感的未来情景就可以作为诗歌的素材来指引学生进行诗歌的创作。在《我爱这土地》这首诗歌的学习过程中,语文教师首先要对诗人艾青表达情感的方式进行讲解,进而在诗歌讲授课程完结后,教师可以以远离家乡这一素材为主题,让学生尝试进行模仿创作。这种形式下,学生对于家乡土地的热爱之情都会被激发出来,同时,在诗歌的模仿过程中,学生也能够更好的对《我爱这土地》这首诗歌进行深入的体会,进而在自己的作品与教材作品的对比下,学生对于诗歌意境的感受更加的深刻,对于应试教育环境下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了更好的渠道与锻炼方式。
3.以诗歌朗诵比赛等形式,强化学生借助诗歌意境提升文化素养的能力
篇(8)
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华清的诗歌写作有知识性的一面,但他对于知识型的诗歌写作似乎并无特殊的爱好。知识性的诗歌写作,通常有一个“弊病”,那就是偏好议论与铺叙,强调逻辑性,严重时则呈现出一种说理性散文的写作倾向。与其他很多诗人的知识性写作不同,华清的诗歌对于知识并不依赖,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及以僻奥为格局从来都不是他对诗歌的追求。即使与知识大为有关的篇什,他也往往能够避重就轻、化繁就简。在《迷津或梦境》这一组诗歌中,知识性最强的当属《从死亡的方向看》和《博尔赫斯或迷宫》。其实,前者的“知识性”不过就是形式上的一点呈现,那就是是诗人起笔化用了多多的一句诗。而除此之外,诗歌的通篇不过都是在借助这一“方向”来“观察世界”和“人间的一切”。应该说,这是一种另类和独到的发现,是一种充满了“奥义”的清醒。所谓思想深刻的批评家的“非同寻常”,此即是一种表现。后者的“知识性”则主要与博尔赫斯及其写作有关,如果剥离掉这些背景知识,我们很容易发现华清此诗侧重的其实乃是对“命运显现”与“照亮黑暗和真理的闪电”的一种可喜的“惊悚”。华清的诗歌总是有它真正要“庇护”的核心所在,尽管这种核心所在有时与所谓的“知识”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交互。
篇(9)
(二)在背诵一定量的诗歌的基础上,具体分析,理解一定量的诗歌 我们采取的是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过程,既先练习、分析一些诗歌,在练习中逐步的认识、了解诗歌的基本常识,以及它的规律。然后归纳出诗歌的一些理论知识,再由这些理论知识去指导诗歌的学习和练习。在具体的理解、分析、判断、积累的前提下,对诗歌进行感悟,对诗歌的分类、意象、典故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为进一步高层鉴赏打下基础。因为如果先讲诗歌的理论知识就会使学生陷入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如同学习语言,孩子一定是先说话,然后慢慢地去理解词汇和句子,进而去理解语法和修辞。
(三)在学习诗歌时积累作品中的意象 引导学生运用“以意逆志”的理论来理解诗歌。要求学生对古诗歌的意象、意境、情感有了真切深入的感悟后,用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的语言、情景对原诗进行再创作,再现诗风词韵,这就要求理解诗歌中的意象的具体意思,如“月”、“长亭”、“短亭”“秋风”“古道”等。“木奴”,果树;“丁香节”,愁思难解、情致缠绵;“长短亭”,表示送别或抒发难舍难别之情:“芳草”,怀念朋友或怀念故国、抒写离别乡思。我们让学生去记一些意象,如以冰雪的晶莹比喻心志的忠贞、品格的高尚;对月思亲――引发离愁别绪,思乡之愁;以折柳表惜别。“柳”,“留”的谐音,折柳有相留之意,等等。
还要重视诗歌中的典故的积累。例如,阅读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要正确理解此诗,就要了解“折柳”这个典故有惜别送行或思乡怀远的意思。
再如,李益《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谴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要想理解本诗就要弄懂“伏波将军马援”,“定远侯班超”,以及“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因此就有必要给学生介绍一些具体的典故,如“王孙”,指高人隐士;“闻笛”表示追念故友缅怀友谊;楼兰:以后诗人就常用“楼兰”代指边境之敌,用“破(斩)楼兰”指建功立业。折腰:“折腰”意为躬身拜揖,后来喻指屈身事人,而诗人常反其义用之。化碧:常用“化碧”形容刚直中正的人为正义事业而蒙冤受屈。东篱:多用“东篱”表现辞官归隐后的田园生活或娴雅的情致。劳歌:本指在劳劳亭送客时唱的歌。“劳歌”后来成为送别歌的代称。柳岸:古人送别有折柳的习俗,后来就用“柳岸”指送别的地方……
(四)在教师的引导下认识诗歌的类型、分类 我们对诗歌进行简单的分类。这是第一步。可以分成英雄赞歌:如李白的《塞下曲》、王昌龄《从军行》;黍蓠悲歌:如姜夔《扬州慢》、刘禹锡《乌衣巷》;田园牧歌:王维《山居秋暝》、孟浩然《过故人庄》;闺怨诗:王昌龄《闺怨》、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思乡羁旅诗:孟浩然《宿建德江》、温庭筠《商山早行》;咏怀咏史诗: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送别感怀诗:柳永《雨霖铃》、王维《渭城曲》等……通过分类学生对比较浅显的诗歌就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有了一个纲,理解起来也就有了方向。写景抒情诗主要把握景和情的关系;借古感怀诗,一般要把握古和今的关系,可以以古喻今,也可以古讽今;托物言志诗主要领悟物和志的关系,借何物显何志,根据不同类型诗歌的特点来学习。抓住了精神实质。也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五)引导学生要知人论世 由于作家的经历、思想、生活习惯和对生活对社会的认识不同。即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处境不同,反映在诗歌里主题、艺术手法也不相同。因此就要引导学生了解作家,从而认识作品。揣摩、了解作者的心境,体会、品味诗人的情感。诗歌为什么具有感染力,就源于它融注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高考诗歌鉴赏经常要考诗人的思想情感,故在平时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在品味字词的过程中去把握思想内容,品味作者情感,所谓“知人论世”是阅读诗歌时一定要注意的。比如了解了和陆游生活的年代、心胸、气魄等方面的不同,也才能明白为什么会说梅花“她在丛中笑”,而陆游却说“寂寞开无主”和“只有香如故”了。当然,一般来说,作家的风格其一生各阶段基本一致,如: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王维的诗中有画,孟浩然的恬静又浑健,苏轼豪放又旷达,弃疾深沉又豪放,柳永伤感又缠绵,陆游流畅又雄放,李清照凄婉多清丽……学生应该认识到,我们通过诗歌的学习可以了解、归纳出作家的这些知识。以后我们遇到这些作者的诗歌可以对号入座地猜测、理解其诗歌。
篇(10)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1-0024-08
如何给李心释的诗歌命名,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他身为语言学教授,曾经出版《语言的语言迷途》等语言学著作;他熟悉解构主义哲学观,在生活观念与诗中均践行,均试图实现自我生命体验的双重在场;也是沉浸语言在虚无深处不断体验生命真谛的“空空和尚”(诗人曾经用过此笔名)。这份艺术简历,构成他进行生命省思的精神背景与艺术前提,远离通过诗歌获得世俗虚名之嫌。倘若没有此相关的精神领域与哲学态度,我们也自然无法考究他的诗歌动力、功力、活力、魅力。
在一部分读者看来,省察他的诗歌或许令许多读者感觉不知所云,间或以晦涩拒之。正如许多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一样,对读者提出较好的专业性、精神性的要求。“马拉美在法国创造了所谓艰深作者的概念。他明确地将必须付出的思想努力引入到艺术中来。正是这样,他提高了对读者的要求,并且他还带着一种真正光荣的令人钦佩的智慧,为自己选择了为数甚少的一群特殊爱好者,这些人一旦领略过他的作品,就再也不能忍受不纯粹、肤浅和毫不设防的诗歌。”[1]202李心释着重于语言的诗歌书写,也同时关顾生命意识与能动性的精神在场。李心释自然站在这个时代的高度上以世界性的眼光写作的,他深知汉语思维自身嵌带的问题及汉语发展的危机感,积极地通过语言不断修复汉语诗歌的信心,不断在形而上学的思索中试图抵达某种艺术可能。
一、在语言深处深究虚无
如果对诗人李心释的语言学的专业背景、延异哲学观、空空的生命意识这种种精神背景稍加考察,我们发现他的诗歌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何谓真正的生命事实的“难题”的思索,而“语言”成为沟通以上三种精神背景的媒介,让他在自我的精神在场与终极性体验中切近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难题”,并展开形而上的思辨、探析。
近年来,他陆续完成了《致敬》、《冬天的苦念头》、《遭遇橡皮树》、《乡村邻居》、《路上的眩晕》、《逛书店晚归》、《灵塔》、《我在这里呆过》、《老茅》、《天空》等作品,他的诗歌取自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的语言,这里面的“致敬”、“苦念头”、“眩晕”却成为后现代心灵投射的支离图像,这个世界不再仅仅由日常支配,而是不断深处挖掘自我的潜意识,诗人更像一个历史学家在虚无之坟寻觅心灵的拓片、零散而寓意深刻的字符,这些组合成从日常导向形而上或者神性的精神语境,诗篇成为一个现实的场域供读者沉思、巡游、审视、辨析自我存在的空间。如他《致敬》中写道:
高原的公路沿线
一匹马静立,低着头
疾驰的车经过它
像一个轻浮的笑话
一匹黑色的马,公路唯一的高度
静止的速度
比所有速度都快
是因为我把眼睛留在了它的身上
作者要致敬的正如面对语言的沉默,因为自我的清醒而促成了致敬的时效、深刻,在生命奔走的匆忙旅途中,静下来想想生活、想想那类融留的沉默的客观生活,保持清醒的意识与态度也成为生命探索的另一种可能路径,“我把眼睛留在了它的身上”,再次强调主体对世界发现的必要性、必然性,如果自我是清晰的、秩序的,那么语言就试图反思、颠覆自我世界的平衡、秩序,唯有不断破除自我的幻象,认识你自己,方可抵达内心的隐秘、诗意与可能。
所有的写作都在写作中完成。在许多诗人看来,诗歌写作的经验就是多写、练笔,在多写中练就、发现某种诗体表意的经验与能力上的提升,不断深化、纯粹,直到形成自我的风格,这成为当代诗歌书写的重要经验。瓦雷里的学生梁宗岱曾有如下一段代表性的论述:“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配的宇宙。”[2]李心释的诗歌,是带着深刻的空观,在语言的通道不断触及、呈现思想的外壳,从他的诗歌更能触碰到的现代的语言意识及哲学观对当代生活的积极影响,更能从诗篇领略其对当下生活认知的启示、意义。“艺术是艰难的,而艺术家在这种艺术活动中经历着不确定……诗歌只是一种练习,但这练习是精神,是精神的纯洁性,是纯净之处――意识,这种可用以交换一切的空无的能力,在那里成了实际的能力,并在严格的范围内包藏着它的各种结合的无限性和它的动作的广阔性。”[3]73世界的认知是难的,这同样成为李心释语言、生命、思想、哲学的综合性的认知前提,他的诗篇展现了这种种语言观、生命观、哲学观、思想观,对读者不断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可能。诗歌成为对现实焦虑、虚无人生的某种积极有效的肯定性的书写,这种书写再次呈现了诗歌作为艺术的重要样式对生活信心的修复与理解的可能。
当代诗歌书写需要体验能力、想象能力,还有自觉的语言、诗体意识,才可能达到诗意、思辨形成较佳的审美、认知效果。头巾、菜刀、把手……成为他脑海深处的语象,不断从日常经验导入形而上的精神遐想与探索之中。他写道:
迎面一个中年妇女
包着头巾,过冬的暗花棉袄
手上动作深入本地
有黑色的血在她身旁循环
这样一直走着,可到黄泉
又一老者
男性是边上的树与房子的性别
干黑的皮肤褶皱
有无数生的厌烦的堆积
日复一日,毫无差别
惟一重大的变化就只剩一个了
曾是那大学教室里的青春
早早结在食物链上
等来的饕餮大餐却不是他自己
(李心释:《冬天里的苦念头》)
梯子不用于我们之间的通达
梯子是扭曲了的生活的精致化
融洽的关系
会像菜刀收集疼痛
菩萨坐在最高层
因为人们不让她有排泄
属泥土的才有心肠
为一只鸡的权利而斗争
我们同拥一枚巨大的青褐色丹药
取名曰天空
加入夕光的糖水
夜夜共享它的苦
(李心释《乡间邻居》)
我说这片土地
犹似说这一张纸
写满后注定要翻过去
翻过去了也许不再有纸
而决无空白
这片土地我呆过
当我被翻过去了
土地还在
我,一个临时钉在地球上的把手
过往的时光将通过我
转动她
(李心释《我在这里呆过》)
他不断捕捉日常的诗意经验通过语言的存在之思,试图理解生命的困惑、虚无,语言因而有了敞开的多义性、丰富性。“敞开,即诗歌。这空间,在那里所有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在那里在两个领域之间有着无限的过渡……诗人当然无法进入其中,诗人进入其中只是为了消亡,在这空间中,诗人只有保持一致才进入裂口的深处,这裂口把诗人变成一张无人理会的嘴,正像它对待聆听寂静的分量的人一样,这就是作品,是作为渊源的作品。”[3]139在语言的本体的质询与探索中,在诗的经验与幻象之间,他的诗歌进行语言/思想的平衡与裂生,生成多种生命、艺术的可能,不断走向澄明之境的存在之思。
法国文艺批评家保罗・瓦莱里在评价马拉美的诗歌时,指出语言(艺术)的不可完成的状态,“艺术的对象逐渐脱离低俗和普遍的幻象,他的品行促使他去从事无形而浩大的工程。这种无情的选择吞噬着他的岁月,完成这个词不再具有意义,因为思想自身是什么也不会完成的。”[1]194不断破除生活的幻象,深入语言的迷津,不断又通过语言呈现艺术与思想的通道,最终为生命意识提供某种精神理路与艺术可能。“它要求思想具有最全面的素质,它永远不会完成,因为严格说来它永远不可能发生,这个工作试图建立一个人的话语,这个人要比任何真实的人在思想上更纯粹、更有力和更深刻,在生活中更激烈,在言语上更高雅和巧妙。这种非凡的话语以支撑它的节奏与和谐为特征,节奏、和谐应当与话语的形成十分紧密甚至神秘地联系起来,使得声音与意义再也不能分离,并且在记忆中无限地相互应和。”[1]181这也自然成了李心释诗歌的写作理念与精神可能的探索动力与前提,在他的诗歌中除了获得一种语言的思辨的知性的审美性的感悟,同时,还获得一种思想认知的震颤感、共鸣意识,可见,他的日常的诗性观察维系了诗歌语言本体的严肃性、终极性的思考魅力,不断抵达诗歌的精神世界。“精神,在审美的意义上,就是指内心的鼓舞生动的原则。但这原则由此鼓动心灵的东西,即它用于这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把内心诸力量合目的地置于焕发状态,亦即置于这样一种自动维持自己、甚至为此而加强着这些力量的游戏之中的东西。”[4]158
当代诗歌书写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本位意识很大程度上传承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中的解构一脉。李心释在生命、哲学的语言意识受惠于传统的佛学空观的潜在意识,他不断否定自我、破除幻象的诗歌写作的精神前提也自然受到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凡是钻研诗歌者就避开了作为确实性的那种存在,遭遇到了诸神的不在场,生活在这种不在场的深处,并为这不在场负责,担当其风险,承受其厚意。钻研诗歌者应当抛开一切偶像,应同一切决裂,应当不把真实作视野,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因为他没有丝毫期望的权利:相反,他应当绝望。钻研诗歌者死,遭遇死亡如深渊。”[3]19他走向了存在主义的存在之思,这一切自然与现代主义以来的“虚无”的探究产生了关联,或者说,这种虚无的精神前提,让他在执着书写与跳出窠臼并行的语言意识中不断深化、强化自我个体的思考与精神性认同。
当代诗歌书写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遮蔽了语言自身的生长态势力与发展可能,他们过度的意象与抒情、过度的形容词、语气词的使用、过度的叙事与口语写作,导致了诗歌愈加偏离诗歌追求的事实、真相。在美国学者奚密看来,哲学取向上的基本差异使现代的“纯诗”观念有别于中国的传统诗学。现代“纯诗”观念不仅导源于同质性读者群的消失,而且甚至在更多程度上导源于公认的整体价值系统的缺席。[5]李心释的诗歌始终坚持语言的可能为前提,不断表现出诗歌必然、本质的诗体意识,使得他的诗歌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精简主义的倾向,这种精简性走向了诗歌的减法、凝练的原则,同时提供了种种自我语言繁殖的能力,重新让诗歌恢复到生命这一立场与维度,驱除繁复的、过度的语词障碍,直达语言的表意现场、诗意生成的肌质与多向性、丰富性的这一精神层面。在澄明的自我与可能面前展开存在之思,精简、凝练的诗歌获得一种语言思辨与知性组合的审美性体悟,不断阅读产生思想认知上的震颤感,日常的诗性观察维系了诗歌本体的严肃性、终极性的思考魅力。他写道:
书店外面,夕照像头颅一样坠落
我出门的惊恐与悬空的文字
有节制地不毁坏日常生活
是胃里的黑暗催我起身
结账的服务员嫣然一笑
依旧如明码标价
一条狗准时来围剿我
是的,我总是被一条而非一条以上的狗
围剿。跑到校门才有安全
因为狗害怕比它大的狗
校门吃进吐出一拨拨人
它消化什么不得而知
今晚的我要消化五本书、黄花菜加五毛饭
(李心释《逛书店晚归》)
国内战争中死去的这些人
与一千年前的和尚共葬一处
想必亡灵自会去渡亡灵
灵魂和石像,对应于
早晨与太阳
回收现世的目光而成石像的光明
今年的梅花节上
一块墓碑无缘无故地裂了
对应于
一角升天了的塔檐
(李心释《灵塔》)
李心释面对当代再现、叙事为主的口语写作话语统领诗坛这一现象,不无警示地提出“隐喻是写给读者的情书”的常识与诗观,可见其清醒的语言意识与诗思指向,让他的诗歌获得了修辞的较佳文本效果,也让读者深入到生命之维的另一种可能观照之中。他写道:
月亮只亮一张熟人的脸
一侧煞白,刚刚经历过我的数落
门前橡皮树葱茏的叶子却以大音量
要求我的生活跪拜
枝干里的神灵
视线被拨得像跳绳
六十年后的我加入,绊倒
再也不能起身
给一次闭目命名为‘夜晚’吧
我明白
那些已逝的同类正在向我转述
别处的生活
(李心释《遭遇橡皮树》)
留意脚,自然就深入土地
凭一片硕大的枯叶
大致能判定站立的纬度
人群永远是细菌一样地分裂
腰带的视线比头上的可怕
只瞄准地图上的一个点
或是在哪里预订了位置
留在脑海里的面孔
仍需一一标上序号
(李心释《路上的眩晕》)
我是九月份来这里的
因为你
一年旋即榨成刚刚
却又匆匆把一生吞下慢慢化解
一个朋友
在语言里已经很老很老了
我用语言的历史
增进对他的感情
把他逼到死角
地图上的一个点
我的笔尖无数次在想象中落下
在他恰好于画架前
把墨抹上
(李心释《老茅》)
在直觉、灵感的牵引下,语言的灵性、神性盎然于笔端,一首首诗篇像精神食粮,让写作者有勇气写下去,也让读者阅读中找回生命的思维与信心,语言与思想形如“基督”,也神似“弟兄”,它又是“诗”,最终三者合一。其实其中的关系正是或此或彼,你我感染,相互扶持,共育诗华。阐释意义走向了体制,阐释的过程也许更切近诗的审美性、文学性。
二、语言:不可能的可能
当代诗歌语言的探索,表现出对汉语自身表述危机与自觉纠偏的文化意识,不断从日常的、经验的话语通过诗性的、文学性的话语的置换、书写去维护汉语自身的纯洁、隐喻的诗性结构。当代社会陷入种种话语的圈套的牢笼,对经验的、日常的、交流的、功能的语言也时刻应该保持警醒意识与辨别态度,“日常话语的机械化、自动化,语词造成虚假的修辞幻象或名实相离,语言总体上工具性、非人化的增强,等等。存在主义者认为这才是语言的危机,拯救之途是把诗与思的本质方式归还给语言,不断进行语言创新。”[6]
当代诗歌的语言的写作,时常滑入了语言的娱戏与一次性的消费行为,仅在语言的外部滑动、迁移,而真正走向文本效果的内部运动、探讨的话语实践,似乎还相差甚远。在李心释看来,有一类艺术作品观念先行,艺术家之创作就是要颠覆已有的或流行的艺术观念。那个被反抗的观念就像民歌手的动作做派一样,已程式化,几近化进艺术界大众中的无意识,令此类艺术越走越窄,缺乏生机。20世纪80年代中的诗歌观念的变迁似乎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反叛意识浓烈,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歌行为。参见李心释博客.http:///blog/static/7425795320130317320291/.他在《隐喻是写给读者的情书》写道:“修辞如果没有了直觉/不过是顾虑重重的代名词/不是废话连篇/却能判别隐喻的好坏/儒者教导不了别人/一个词语繁衍出另一些词语/这的本性谁都会感染”,“隐喻是写给读者的情书”,隐喻自然成为诗歌的常识与语言的本体追求,在直觉、灵感的内力作用下,语言裂变成诗的灵性、神性,“诗歌的话语不再是某个人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没有人在说话,而在说话的并非人,但是好像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语言便显示出它的全部重要性;语言成为本质的东西;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因此,赋予诗人的话语可称为本质的话语。”[3]23语言让读者在阅读中与写作者的情思融合,并在语言的体味中切近生命意识、不断提升艺术思维的高度与难度,也在语言阅读中形成诗意的生命智慧,诗、思、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或此或彼,彼此渗透、交汇、影响、融合,前提是语言,最终又回归语言,语言成为前提、媒介、效果的生成机制与可能。
在诗学与诗歌的传统之间的平衡,给当代诗歌书写提供可能。李心释的诗歌表现出语言本体的回归探索,不断试图识别世界被遮蔽的秘密。在他看来,“在日常观念的世界中我看不到任何人的希望,写诗是为了反抗日常语言,反抗虚无,感受意义的言说,确立真语言。”[7]他在《二手的我》写道:
金黄色的
光线
通过白墙壁
折到被午睡遗弃
的床前
目的是把一个人
变成
二手的我
再嫁祸给冬日
书架像个停车场
一本心仪的车
冲出堤坝
追踪我
诗歌依旧帮助我们破除自我幻象,语言本体的修辞对“二手的我”的堕落、迷津进行驱逐、去蔽,忍受黑夜的孤独、寂寞和语言的纠缠,让自我努力超越于现实之外,但是写完又要落入凡间,从日常经验的“床前”,展开现实自我的精神质询,“冬日”,富有意味,既可能指向诗人当下的生活语境,也可能传送冬日生活之遭遇的联想,于是诗歌经验之外的另一语义生成,至少“嫁祸”已把诗的情绪在字里行间不断进行暗示而铺展。“书架像个停车场”,同样源于日常生活,但又在强指、近似的联想与隐喻中,不断让我们体味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似/非似带给文本的神奇效果,“一本心仪的车”,颠覆了语言的表达秩序,在“本”与“辆”之间把我从经验拉向幻象,在诗意的可能捕捉中,我们寻访诗人自我的可能秘密。“冲出坝外”,完成了诗歌的语言的表现可能,也强化诗歌走向语言本体的“幻想”色彩。诗的语义、情绪的错位、变形,让读者尝试对《二手的我》狠狠阅读、跟踪,从而,让生活的真相的自我慢慢浮现出经验的精神水面。“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序列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序列所造成。”[8]诗歌成为某种话语促成了这一切的转化与生成,从日常的经验空间不断抵达可能性的诗性、诗思凝聚的文学空间。
语言的不可能的可能状态推动了诗/思、诗人/读者之间的联系、相互理解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人都是语言的奴隶,诗人是不安分的奴隶,并随时希望由奴隶变成主人。自觉的语言意识是摆脱语义奴役的第一步。”[9]诗人离不开读者,正如诗歌离不开语言一样,在可能的语言中抵达艺术与思想所启示的生命之维,这就预设了语言不再是日常的交流功能,也非稳定语言结构的政治话语,而是让语言成为一种思维可能,诗歌写作颠覆了、赋予了、强化了、生成了语言的种种可能。“一首诗歌是否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 只能说相对自足,因为即使诗是封闭的,但理解却是个开放的过程,读者面对一首诗歌有两个权力,一是进入诗人创造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去体会其聚合的空间和组合的表现法,去体会语言的结构与张力;二是并不把这首诗读成一个整体即一首完整的诗,只取其中一词一句,把自己被激发的体验填充进去,而后读成的诗其实已是另外的一首诗了,不能归于作者,你也完全可以重写,那是你自己的诗。”[10]可见,诗篇的完成绝非单凭诗人的写作,还需要读者的有效介入,不可能的语言的可能性,让写作者与读者之间找到了对话的意义与可能,语言思维自身嵌带的复义、隐喻等功能,最终深化为语言/生命的某种思维、意识。
三、语言本体写作的当下话语启示
当代诗歌的发展经过朦胧诗对战歌、颂歌的语言置换,经过第三代标以先锋的语言、语感对朦胧诗意象与抒情的语言的替代,经过轰轰隆隆的下半身、垃圾派、废话写作等话语对上半身的语言解构,在李心释看来,“现代汉语诗歌还像个孩子,承认这一点,或许还能看到希望:我们的传统已经纵容了一个孩子的撒野,或许正在等待她的主动自我矫正与回归。”[11]40诗歌还是一个孩子,体现当代诗歌的年幼、稚嫩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语言存在的问题,以及诗体意识的回归、审视、认知、超越方面的缺失影响了语言凝聚的艺术观、生命观的自然形成与深度。
当代诗歌书写一直并未离开语言,但是语言在当代诗歌似乎又是剥离与单一、局限的,李心释的诗歌及观念的实践,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话语启示。
第一,语言的本体意识、可能意识对当代诗歌书写的积极影响。
当下语言状况相对受到来自西方翻译、网络语言、汉语拼音化等的影响,使得当代诗歌书写不自觉地滑入时代的语境中,语言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不是语言在表达,而是人为的声音在表达,语言的自我繁殖能力被限制,束缚了当代诗歌的语言发展与纯粹。“中国大陆新诗创作正出现在这个世界艺术诗歌的新起点时期。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探索,不再重复西方的脚印,在此以前我们总是追赶西方的实验,现在我们应当找回自己诗歌的过去,包括古典诗词、美学,综合西方现代的诗歌的种种尝试,取其可取者,寻求有东方特点的自己的诗学和诗格。”[12]
李心释的诗歌表现出某种难能可贵、独特清醒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判断力,“判断力为了自己独特的运用必须假定这一点为先天原则,即在那些特殊的(经验性的)自然规律中对于人的见地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却在联结它们的多样性为一个本身可能的经验时仍包含有一种我们虽然不可探究、但毕竟可思维的合规律的统一性。”[4]18虽然有人将其放在“第三条道路”等诗派的写作类型中去认识,但他无疑保持了艺术的清醒与思想的独立,因而,他的话语一方面源于当代诗歌书写中吸取的营养,但也不断突出当代诗歌放逐语言、弱化语言认知水平的写作,不断滑入语言的常规与政治的话语圈套之中。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诗界和小说界吸收了现代哲学和语言学中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似乎真的把语言当语言看待,其背后仍然是文化与文学革命的思路……“语言”在80年代初不过是启蒙主义旗帜下的一个工具。之后,第三代诗歌里“反崇高”“反文化”“反英雄”等文化主张扎根在“语言”头上,“诗到语言为止”,“语言”的地位已被提升至不能再高的位置,但它仍然是工具而已。[13]
第二,当代诗歌史的情结编织与诗性建构的重新认知。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指向了诗歌写作的时间、历史的描述与梳理,而相对缺失了诗性、客观性的评价与鉴别。在他看来,“在无法辨别谎言与真理的时候有太多的人保持着沉默,因为说话只徒增混乱。当代诗的疯长完全来自符号说谎的力量。所谓诗人,已是盗用叙述真理的语法来装饰自己的怪物,有太多奇思妙想不是来自头脑而是来自语词的主宰,诗人坚决不当意识形态的奴隶,却把奴颜婢膝献给了语词。诗界曾倡导能指的滑动,而警惕语词的老化、板结,他们借以产生诗意的东西不外是一场歇斯底里的自我献祭的狂欢”[11]38
当代诗歌的批评与研究,远离语言本体意识上的书写,许多作品研究指向写了什么,而诗歌研究者、批评家也局限于诗歌写了什么的一般梳理与常识研究,相对缺少对语言境况的深度剖析。“没有任何‘文学史’(如果仍然要写这样的文学史的话)能够仍然是正当的,如果它像以往一样满足于把各种流派串连在一起而不指出它们彼此之间的鸿沟的话,这种鸿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即写作的语言观。”[14]188在这样的学术体制化、认知理性化的常识牵制下,我们相反远离了诗歌的传统认知与语言意识的觉醒可能。“所谓的文学史资料几乎没有触及创造诗歌的秘密。一切都在艺术家的内心进行,似乎我们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一切事件,只对其中作品有着表面的影响。更重要的东西――缪斯女神的行为本身――与她的经历、生活方式、遭遇以及一切可以在一部传记中披露的事情无关。历史能够观察到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1]33
当代诗歌研究的历史意识应该注意诗歌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差异性,美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所指出诗性的修辞性的历史意识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常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15]1 “伟大的历史经典之所以从来不明确‘解决’某一历史问题,而总是向过去‘敞开’以激发更多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比喻性。正是这个事实允许基本上把历史话语当作阐释,而非解释或描写,而最重要的则是将其当作一种书写,不是为平息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意志,而是刺激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生产更多的话语,更多的书写。”[15]299对当代诗歌史不断深入进行“情节编织”,从语言的差异性、丰富性中找出诗体意识上的经典作品,丰富与完善“当代诗歌史”的历史图景与理论研究。显然,“在古典时期,‘诗学’并不指任何领域,任何特殊情感内容,任何首尾一致性,任何分离的领域,而只是指一种语言技巧的改变,即按照比通常谈话则更富艺术性、因此更具有社会性的规则来改变自我表达方式,换言之,即把一种由于其惯习的显明性本身而被社会化了的言语,投射于来自心灵的内在思想之外。”[14]28
第三,诗歌跨越艺术边界,走向种种思想可能的思考,为当代社会观照自我提供了精神性的话语启示。
强烈的生命意识的灌注、积极的书写态度,有效地让诗歌成为抵达某种审美性、思想性的精神活动的形式之一,同时也回到了主体在生命―艺术异质同构这一文化意识。“在我写作的时候和直到我停止写作为止,我为之心折的不朽思想是一场白日梦。我认为不朽是存在的,但不是像这样的不朽。”[16]通过个体的书写,我们在日常/超验、生活/梦想、现实/艺术的对立中,不断融入、契合、感应、交汇。“写作就把人物的实际言语当成了他的思考场所。”[14]50诗歌提供了最好的艺术形式,实现了现实梦想的生命化指认,不断把人从现实的、物质的、欲望的、世故的经验世界,向超验的、灵性的、精神的、纯粹的现象界过渡。语言的诗艺化、思想化的可能性的探索与书写,成为李心释进入形而上学思考的媒介与基础,“面对世界准备(好)的身体,暴露给世界,承受感觉、情感、痛苦等,也就是说介入世界,交给并参与世界,在同样的情况下,身体可以对世界产生一种合适的反应,从而控制世界,掌握世界,将世界作为一种工具来利用(而不是辨别它),这种工具(按照海德格尔的著名分析)是触手可及的,而且从来都是被照此看待的,被它许可完成的和它指向的任务看透,好象它是透明的一样。”[17]
诗歌的边界不断被打破,最终又回到生命这一最终的企及可能。“训练除了使我们了解、掌握各种写作技巧,最主要功能是使我们知晓诗歌的边界何在。万物皆有边界,何以诗歌独称无限?因此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必须清楚什么是应当抛弃的,什么是应当生发和完善的。但诗歌写作仅凭训练肯定不够,因为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题材上说,诗歌写作都是一种冒险。训练使我们获得冒险的资格,使我们在知晓了写作边界之后跨越边界,使我们的写作不至于僵死或永远停留在学徒期。”[18]诗歌变成书写,从现实切近了精神的在场,而灌注诗里的仍是一个诗人持久以来的参悟与修行的生命理念与终极价值,李心释尝试抵达语言的内核,不断探索一种不可能的可能的存在之思。“作诗并不是在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一种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在思想中,语言才首先达乎语言,也即才首先进入其本质……思想是原诗;它先于一切诗歌,却也先于艺术的诗意因素,因为艺术是在语言之领域的狭窄意义上,一切作诗在其根本处都是运思。思想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19]他不断向现实发出深究生命真实的声音,语言为他提供了走近诗意人生的生活可能,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不断破除幻象,获得精神性、纯粹性的审美视域与生命关怀的融合与统一的可能,实现诗/哲学、诗/灵性等的相互增补、启示。
参考文献
[1]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M].段映虹,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梁宗岱.梁宗岱文集(卷二)[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87.
[3]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M].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8.
[5]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8.
[6]李心释,宋宁刚.对“汉语危机”论的反思[J].广西大学学报,2009(4):108.
[7]李心释.诗观[J].广西文学,2012(11-12):14.
[8]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72.
[9]周伦佑.语言的自觉与诗的自觉[M]//常文昌. 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00.
[10]李心释.索绪尔语言学视野中的诗歌语言分析[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2(5):66.
[11]李心释.当代诗歌的语言策略批判[J].扬子江评论,2009(2).
[12]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8.
[13]李心释.诗歌语言的反抗神话[J].文艺争鸣,2012(10):80.
[14]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5]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序[M]. 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16]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9.
篇(11)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6-0140-01
一、与诗歌相关知识的传授
诗歌教学中的相关知识可以分为有关诗歌的基本常识和诗歌鉴赏的基本知识。有关诗歌的基本常识的内容比较容易界定,学界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如关于中国古代诗诗词曲赋的基本分类,像唐诗、宋词、元曲等。唐诗又可分为古体诗和格律诗,格律诗又分为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又有五、七言之分;宋词有不同的词牌,根据长短又有慢词和小令之分;现代诗歌也有其基本的体例和规范。这些知识,虽然没有必要像大学中文系一样进行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但中学生要学习它,对这些基本常识的了解是绝对必要的。正如方智范先生所言:“了解了一定的格律常识,有利于学生在鉴赏具体作品时,领悟中国古代诗歌在诗歌音律美方面比现代诗歌具有更精密细腻的特殊美感,对作品的意境和情韵的感受可以更深入一步。”
当然,教学中,这些基本常识的学习应该有多种途径,但空对空的传授必定是大忌,因为教学这些知识不是目的。有一位老师这样教《沁园春・长沙》这首时,讲到“沁园春”词的格式,他结合《沁园春・雪》,引导学生了解掌心词的有关知识:
(一)与学生同背《沁园春・雪》,并出示此词全文
问题:仔细分析这两首词,谈一谈它们在结构上有什么相似点?
明确:字数相同,相应位置的结构相似,韵脚相同。
双调,一百十四字。前段十三句,后段十二句。一般呈现出雅驯典重、旷达疏放、豪迈悲壮的风格。
(二)练习:根据有关词的知识,从选项中选出恰当的一项:
沁园春 苏轼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晨霜耿耿;云山离锦,朝露溥溥;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呤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A、月华收练;此事何难
B、月华收练;此事有何难
C、渐月华收练;此事何难
D、渐月华收练;此事有何难
笔者以为,诗歌知识的这种教法是最值得肯定方法之一的,因为它做到了既形象实用又准确易懂。
二、诗歌的诵读
诗歌教学中的诵读慢慢被分析所取代,有的教师居然像分析散文一样一句一句甚至一词一词地落实其中的微言大义,同时也没忘了给诗歌分段,归纳中心思想。这种做法几乎完全消解了诗歌独特的文体特点,它的跳跃性,它的节奏感,它的音乐感,都被大量的意义分析给抹平了,诗歌教学成了应试教学的最大牺牲品。
我们汉字的词汇量十分丰富,单单对文字,就有“读、念、吟、诵、唱、看”等阅读形态。一般的书信文稿是既可以“读”也可以“看”的,也就是说既可以出声,也可以不出声的。而阅读诗歌却不能用“看”来表述,读诗不能无声。柳永的词一写出来就会在坊间传唱,可见词也不宜默读。因此,诗歌不吟诵好比曲成不演唱一样不可思议。
三、诗歌教学的人文熏陶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追求实利的,中华民族始终缺少非功利的形而上的信仰,因此做什么事都得问一问:它有什么用处?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所有目标就是中举做官,书本只是他们入仕的敲门砖。封建王朝灭亡,废科举,兴新学,总该有所改观吧?我们先听听林汉达先生1941年在他的《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中一段话:
假如文字是矿工所用的铁锄,那么学问是用这铁锄所开出来的矿物。自然矿的种类不一,金矿银矿也好,铁矿煤矿也不错。怕是怕工人们什么矿都不采,只在那是费了五年十年的光阴和精神,专在擦亮他们的铁锄。……这种开矿工人要他何用?这种读书人,那是有什么教育?过去的读书人是这样,现在的学生还不仍是这样吗?学生在学校里干什么呢?还不是在他的锄头上做工夫吗?谁叫他这样干的呢?自然是他自己,他的父母和他的教员。一个学生若在作文簿上写了几个别字,或夹了几句不通的字句,国文教员便批评他“不通”,“国文程度够不上”,而他所写的内容如何,却不过问。反之,一个学生如能做诗,且做分平仄押诗韵的旧诗,那末,这管他所说是花呀,月呀,甚至是屁呀,他总是一个有国学根底的好学生。这样的学生不但自己很高兴,便是他的教员,他的家长,也很得意。
目前,“高中语文新课标”已经出台,“人文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在这教育改革的良好背景下,我们应该充分挖掘经典诗歌中审美意蕴和人文魅力,让它化为学生的内在素养,使他们成为灵魂高尚、思想健全的人。
当然,我们反对这样一种做法,即从作品的活生生的内容和形式中概括出理性的、抽象的中心思想或主题思想,再加以模式化的表达。“这种意蕴分析的教条化、图解化倾向,热衷于指向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做法只能是对诗歌本身的损害,对诗歌教学一点好处都没有。从作家主体而言,作品中的意蕴,乃是其思想、意识、情感的综合体。正如黑格尔所言:“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
四、诗歌创作的实践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