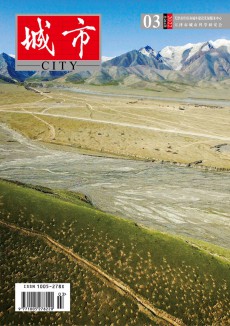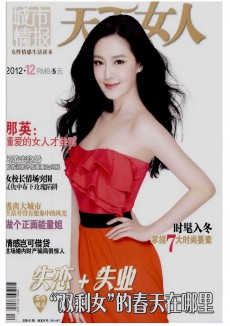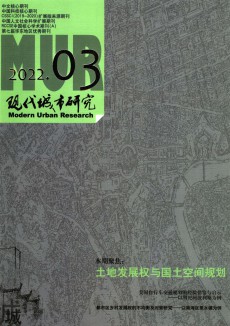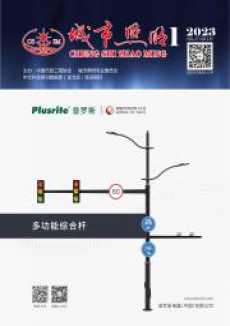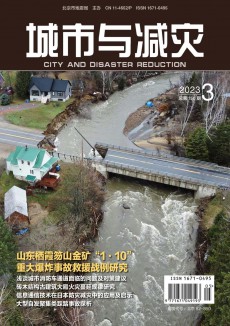城市地理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9 09:20:57
篇(1)
哈维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资本来揭示当代城市的本质。在哈维看来,当代城市的深层本质是资本性,当代城市与城市化是资本维护自身生产、增值的高领域、新工具,当代城市问题的深层本质也就是资本的问题,城市问题不过是资本问题的一种新形式。芒福德则用文化这个范畴来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容器。“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凯文•林奇则立足城市的主体,对城市本质进行揭示,认为活力、感觉、控制、效率、公正等是把握城市本质的重要概念。应该说,针对具体研究目标,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范畴来揭示、定位城市,对把握城市本质,建构作为一般城市理论的城市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理论与城市研究,由于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还没有对其自身的方法论策略进行十分自觉、系统的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研究的深层化。笔者认为,城市理论、城市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与确认。城市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处理对象与概念、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如何从感性的城市现象出发,生成、建构反映城市本质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策略,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法,对确认城市哲学建构的基本方法论,具有示范意义。面对巨大的商品堆积、复杂的资本世界,马克思运用商品—货币—资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资本—消费资本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概念群,对资本社会进行了解码。
正是通过这些紧密相关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知识化、概念化,使资本社会从抽象的感性存在,成为具体的理论存在,实现了资本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飞跃。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理论飞跃,马克思究竟以什么原则和方法为支撑,实现了对作为感性存在的资本社会的符号化、概念化、理论化。笔者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到一般,是马克思对资本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抽象”也就是感性的具体,“一般”也就是理论的具体,抽象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只反映了对象的某一个侧重、某一个特点。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由不同的抽象组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对象多个特点、多个侧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出发,尽可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所有特点、根本特点,并形成反映对象本质的概念与理论的过程。“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发展的场合”。这种方法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也就是从历史出发建构逻辑,并对历史进行逻辑与本质把握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资本论》所运用的这种处理对象与概念关系的方法论策略,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是建构城市哲学的根本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与时期,都会形成反映这个时期与时代的概念与理论。
而社会生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从真实的感性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和概念出发,就成为形成能够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对象与生活的概念与理论的重要基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综合变迁过程,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注重从现实、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其二,直面与解答城市问题,是建构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从问题出发,从资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出发,是马克思《资本论》能够形成其独特概念群的重要方法。对城市哲学而言,真实地面对、切入城市问题,是建构与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与动力。其三,回归城市历史,正确处理城市逻辑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是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面对日益复杂而严重的城市问题,诸多学科的学者已经建构起不同向度与形态的城市知识。梳理、鉴别这些城市知识的合理性、价值与意义,是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面对日益丰富甚至互相对立的城市知识,尤其需要回到城市发展史本身。比如,雅各布斯提出了一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认为,城市在公元前8500年就产生,城市的诞生早于农业文明,正是在城市的推动下,农业等生产方式才得以生产。那么,究竟是农业文明先于城市文明,还是城市先于农业?显然,在概念史这个层面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反思社会实践史,可以发现,雅各布斯在建构起城市观与文明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或者说忽视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雅各布斯所设想的城市,其运行需要有运输工业、存储工具以及文字。但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8500年,轮子运输工具、制陶技术以及文字都还没有出现。这个例子说明,只有回到历史本身,从城市发展史出发,才能解决城市知识层面存在的诸多分歧,才能建构起真正合理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理论。
二、时间与空间:《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与城市哲学
城市哲学的兴起和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叶以来,伴随现代性的复杂化,在福柯、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学者的推动下,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可以从社会实在与社会知识两个层面来认识。从社会实在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现代社会的人文环境、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与文化等的存在形态日益多样,人们日益遭遇同时性存在的文明与文化等的多样性、差异性问题。从社会知识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人们日益关注社会生活的当下性,日益关注同时性存在的多样、差异的文明与文化,甚至把空间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本体性范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空间本体论”等观念和方法。笔者认为,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问题的一面。这种转向反映了当代现代性的重要新特征,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一元性、强制性历史观的反思。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是世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空间性、共时性,可能有利于解释某些阶段性、局部性的现象,但并不能根本性地解释和说明研究对象的深层本质与变迁趋势。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城市哲学研究也遭遇了空间与时间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空间性。在当代语境下,空间性也就是同时并存意义上的多样性。对城市而言,这种多样性、空间性表现在利益、文化、建筑形态、资源条件等方面。那么,这些复杂的关系有无一个相对统一的交汇点,是否存在把握复杂多样性的相对统一的切入点、关节点?这实质上涉及对城市本质与城市秩序的理解,如果城市只是各种要素的杂多性聚集,那么,城市可能也就没有本质与秩序可言。一是如何理解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如何在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中,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性。面对城市化的复杂结果,有的研究者以一种停滞、乡愁甚至倒退式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城市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传统的美好生活;有的研究者以一种激进、技术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人类可以以技术为支撑无限制地向前推进城市化。那么,对城市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时间性与空间性?马克思《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问题的处理,对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厘清当代社会理论的历史观问题,对从方法论层面自觉确认城市哲学的历史观基础具有重要启发。
应该说,马克思深刻地遭遇了其所处时代的空间性问题:资本形态与资本问题的多样性并存。比如:多样堆积的商品,多样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价格等多样形式存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可以说,促使马克思进行理论思考的正是这些复杂的空间性问题。如何把这些空间并存的资本问题揭示清楚,正是《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目标。《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两个层面揭示了资本空间化、多样性的深层本质。其一,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定位。在马克思看来,再复杂的价值关系、资本关系,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具体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管资本是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还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不管资本再生产自己的具体形式与链条多么复杂,最后都是一种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二,对已经深刻空间化、多样化的资本进行历史透视,通过揭示资本自身生成的历史逻辑,呈现其逻辑一贯的深层本质。
《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成经历了物的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货币的产生、资本的产生,再到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等过程,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核心与红线,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在马克思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与历史本质揭示的背后,是马克思独特的历史观策略、方法论策略。其一,马克思强调从已经充分展开、复杂化的现实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思考”,把握其变迁的总体逻辑、总体趋势。“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也为人们研究认识对象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二,马克思注重从历史、现实、未来相统一的视角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变迁逻辑、未来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具有阶段性、暂时性,既不是历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立足社会实践,把握社会规律,创造新的生活。
《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处理,为我们理解城市的本质、建构城市哲学具有重要启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如何理解不断空间化、多样化的城市。虽然城市是一个日益复杂的现象,其重要特征就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化并存,但在深层本质上,城市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创造物。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线索。把握了社会关系的变迁、结构与趋势,也就把握了复杂城市现象的深层特点。城市问题不管多么复杂,其深层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义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合理可持续的城市秩序。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切入点。其二,关于如何理解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普遍社会状态,与意识形态无关。
雅各布斯认为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城市社会,索亚也赞同这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这种城市观其实否认了城市的历史性、时间性,否定了城市发展的可能。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方法论视域中,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该区别社会性与城市性,区别以同质文明为基础的小群落式的空间聚集与以多样异质文明聚集为基础的空间聚集。前者是村落,后者是城镇或城市。而城镇与城市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仍将继续。只有从时间性与空间性相统一的角度,才能深层次地把握城市的具体、历史本质。其三,关于城市哲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自觉。《资本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进行社会与理论研究时,要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具有全局性,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相统一的城市化,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具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现实问题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反思”,把握其历史本质与历史趋势的方法,对深化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世俗与神圣:《资本论》的主体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客观地反映、研究社会生活,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追求客观性,不等于没有价值立场。从知识归属看,价值立场问题是理论与知识的主体性归属问题,即一种社会理论为谁代言的问题;从社会实在看,价值立场问题其实深刻涉及历史本身的主体性问题,即谁是历史与社会的主体这个问题。在当代复杂现代性、“碎化”现代性语境下,历史被分化为不同的具体领域,历史的主体性问题被具体地分化为不同社会领域的主体性问题,比如,谁是经济领域的主体、政治领域的主体、文化领域的主体等。对城市发展而言,追问谁是城市与城市发展的主体,也就是对历史主体的一种具体追问。城市的主体问题又具体化为“城市权”的归属问题,包括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主体归属问题,即谁在城市与城市发展中拥有城市权力、享有城市权利。正如韦伯等所揭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工。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专业化,使人们只能在某个领域内获得发展、获得范围与内容有限的权力与权利。但这种有限的权力与权利,在现实中的配置却往往并不平等。不同领域的权力与权利往往被少数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对“城市权”而言也是如此,城市发展与运行的权力,城市发展的成果及相应权利,往往被少数的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这些精英在城市发展中日益享有神圣的主体地位,而广大的民众作为世俗主体,往往只能成为不受自身左右的城市发展结果的接受者甚至城市发展工具,而不能作为城市发展与运行的主体。精英与世俗的关系,是历史与城市主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虽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进行过研究,以社会学的方法触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虽然福柯、哈维、索亚等对城市权力、城市权利、城市公正等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探索,以政治学、地理学的方式涉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但反思已有的城市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往往相对忽视从主体性及其历史变迁角度进行城市研究,没有对城市主体的神圣与世俗等结构性问题进行专门的历史与逻辑探索,尤其缺乏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研究方法的深层反思、理论自觉。《资本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反思、对世俗主体地位的历史与价值确认,对推动城市哲学主体性研究、价值原则研究的自觉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所面对的现代性是一个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社会。权力与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产业工人则挣扎在生存线上,甚至走向绝对贫困。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论为视域,对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生产劳动的核心主体是工人、普通的劳动者。但在资本现代性的制度语境下,作为财富主体创造者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世俗主体,不仅没有获得应该的权力和权利,反而成为资本无限增值自身的工具。《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行逻辑与运行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方法、策略。反思《资本论》,可以发现,在科学客观逻辑的背后,有一条非常鲜明的主体价值逻辑,就是确认世俗主体、普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可以说,对谁是历史的主体这个问题的追问是《资本论》的真正主题。当然,《资本论》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地指认这个事实,而在于通过详细地研究资本主义诞生、发展、运行的历史与逻辑,具体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具体证明了世俗主体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进行主体性研究、历史主体确认的。让历史过程本身确认历史的主体,用事实本身来揭露事实,是马克思进行主体性研究、主体性确认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正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历史与机理研究,马克思把对苦难者、世俗主体的同情转化或者说升华为对其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确认、价值确认。《资本论》的这种主体性研究进路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特别是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城市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城市主体的自觉反思与确认,当下的城市哲学研究尤其需要拓展从微观、具体出发的主体问题研究思路。城市主体性是历史主体性这个问题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具体化。对历史主体这个问题进行哲学高度、宏观尺度的反思与反省,对把握城市主体性问题具有基础意义。但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的真正深入把握,尤其需要结合具体、微观领域的城市权力、城市权利问题进行。城市是一个由诸多具体领域、环节构成的复杂机体,没有诸多构成环节与领域的合理化,没有诸多微观领域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对整体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从微观出发,从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具体构成出发,具体确认世俗主体的“城市权”,是深化城市主体性研究、推进城市研究走出主体性迷失的一个基础路径。其二,对城市本身进行历史研究,用城市发展史本身的内在逻辑确认城市主体,是厘清城市主体性问题的根本基础。目前的城市史研究往往以城市空间、城市地理、城市形态、城市建筑等为线索进行,而没有以城市主体性问题为线索展开城市发展史研究,更没有对城市主体与城市发展史关系进行深层把握的城市史研究。这导致了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研究的浮躁化与浅层化。城市哲学研究的深层化,离不开对城市权利史、城市权力史的进程反思与逻辑把握,也离不开对生产方式变迁史、社会关系变迁史及城市主体变迁史的具体研究,也离不开对主体性、城市性、社会性、现代性等问题的逻辑与历史把握。城市发展史研究的深化,将“自然”呈现世俗主体在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地位。其三,直面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当代特征,具体探索符合时代条件的解决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制度路径。当代城市现代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现代性,有延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资本现代性是城市现代性的重要特点,马克思对资本关系、阶级关系等的批判性把握,对分析当代城市及其主体性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当下现代性、城市现代性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后福利社会、消费社会、知识社会、虚拟经济与社会等的推进,使城市现代性语境下的社会关系、阶级与阶层关系等表现出高复杂性。这就需要城市与城市哲学研究者不断跟踪、把握当代现代性的新变化、新特征,对城市主体性的变迁趋势进行动态性的研究,探索面向未来的调整城市主体关系、实现世俗主体历史主体性的可行制度、可行策略。
四、智慧与知识:《资本论》的知识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任何一个对象,包括客观性的世界和主观性的理论,都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对理论而言,对象性存在有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理论都最终同实在对象、感性对象有关,都是对世界与实在的一种直接或间接反映,不和真实、感性、外在对象相关联的理论往往是抽象的;二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都以知识群、理论群的方式存在,只有在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共存与对话中,一种理论才能得以生成、发展。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中都需要同时性地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同外在对象的关系问题,二是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城市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城市问题的突现,是城市理论、城市知识产生的根本动因,正是在感性的城市问题的推进下,城市理论、城市哲学才得以产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城市问题的关注,所谓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将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城市理论、城市哲学需要以知识群和理论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种城市研究都不可能以单独或独占的形式存在,正是在同多样形态、范式的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共存、对话与碰撞中,城市研究才得以繁荣、不断发展。这样,对城市哲学而言,如何处理好同已有的多样、多学科城市理论的关系,能否形成与其他城市理论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城市知识群、理论群的良性发展,就成为城市哲学研究能否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城市理论群、城市知识群,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不同向度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不同专业学科的研究者们建构起不同样态的城市理论,比如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二是这些不同向度与范式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仍处于相对离散的状态,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各异。虽然有了一些跨学科的对话,但城市知识仍主要分属于不同的专业学科,往往缺少真正的深层对话,尤其缺少不同城市理论之间的多元对话,甚至没有进行多元对话的机制和平台。三是城市问题本身的复合性、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不同学科城市知识、知识理论的跨界对话,这种对话将为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的可能。城市哲学正是这种对话趋势的一种产物,城市哲学的推进将为不同学科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深层对话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基础甚至一种新的机制。这样,如何探索、确认同多样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进行多元对话的原则和机制,就成为城市哲学建构与发展中需要自觉反思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知识论策略,其处理知识与理论对话问题的原则与方法,对城市哲学处理知识对话、理论对话问题具有重要启发。反思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同已有的相关研究、相关知识、相关理论进行深层和系统的对话,不仅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推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正是在同不同思想的对话与碰撞中,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不断形成、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诸多思想、理论进行了对话,对其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重要著作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与对话中形成、证明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原则与方法。
《资本论》的思想与理论对话,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一种有深度和明确目标的对话,一种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批判性对话。马克思梳理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撰写教科书式的理论概览,不是为了梳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为了在对话中揭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揭示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理解上的可能价值与主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理论对话,是紧紧围绕探索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运行规律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对话,而不是无目的的漫游式对话。其二,是一种有广度、直面问题本身、没有学科边界的哲学性对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诸多流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反思了李嘉图、斯密等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也就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政治学思想批评史。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反思与批评,始终保持着哲学的高度与深度,始终没有游离于对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深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这样,《资本论》又同时是一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著作。哲学性是《资本论》的重要特点,也是《资本论》能够走进当代的重要原因。其三,是一种有智慧的对话,是以探索具体规律、可行的实践策略为目标的对话。揭示资本的剩余价值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灭亡的规律,是马克思同不同范式经济学思想进行对话的重要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服从于更为高远的目标:具体探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建构新世界的可行策略、实践智慧。也就是说,在《资本论》的大尺度思想对话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实践目标,就是为解决资本问题,为建构更合理的新世界、新社会进行原则、路径等探索。这样,马克思《资本论》就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批评史著作,不仅是一部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更是一部以实践智慧为导向的实践哲学著作。智慧性是《资本论》的根本价值所在,是《资本论》具有跨时空意义的根本原因。对城市哲学而言,在知识建构这个层面,《资本论》的独特知识论策略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其一,多学科对话是深化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必要路径。一方面,建构城市哲学是不同形态城市理论深层对话的一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城市哲学的自觉建构,也将为城市理论的多学科对话提供一个更具一般的对话基础与对话平台。
篇(2)
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的探索,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以“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整合中外在城市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学科架构,以满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识需要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为推动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综合研究城市发展上都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为“城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积累。
转贴于 二是以“都市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与升级。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代理性系统为核心,无法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会,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与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理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城市的。当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舆情,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温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学根据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对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业背景下形成的现代理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
篇(3)
《城视时代》从影响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两大关键因素―――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入手,剖析中国当代文化在形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当代中国的现状来看,视觉技术和城市化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视觉技术内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构成,视觉媒介及其观看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而城市化、都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城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因此,在以文化视角重新观看中国文化社会问题获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型理论武器。
《城视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开拓性地将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在一起,命名为“城视文化”[1],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一套文化理论研究方法。那么,曾军为何要把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结合起来呢?作者在文中指出,这两种文化的联姻是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是因为城市作为一种景观,其视觉经验是城市人确认自身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参照,而城市景观的文本化,又是视觉文化关注和解析的符码。这是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的基础;二是新型的视觉媒介技术产生于城市,并形成观看机制,进而弥散至世界各地,而城市不断创造的景观,产生出权力渗透的空间,使城市中的视觉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将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从主体上来看,是因为曾军对中国当代文化状况非常关注,他具有探索新型文化理论方法参与文化建设和指导的强烈精神诉求。
二、“城市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诱发了新型的文化艺术形式,视觉研究成为新宠。目前学术界对“视觉”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视觉”名词化(将其视为人们拥有的视觉感知能力和为满足这一感官需要而生产出的视觉对象),另一种是将“视觉”动词化(将其视为观看的行为)。而曾军认为,传统学术界将视觉文化的本质性规定概括为“视觉性”不如“视觉化”更为恰切,因为“视觉化”拥有更加整合性的视角,能够兼顾我们对“视觉”的名词性和动词性的理解,并能将属于“视觉性”的内涵涵纳其中。在曾军的“视觉化”概念中,最直接的意义是“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其次是在视觉化过程中,影像化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第三是“视觉化”显现出后现代图像的虚拟性,即由于“拟像”的泛滥而形成的视觉危机、表征危机;第四是视觉文化逻辑会形成“视觉性的弥散”。[2]值得一提的是,曾军在剖析文化理论问题时,善于借鉴既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又注意到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与独特性,从独特和不同之处发掘理论的创新点。从“视觉”到“视觉性”再到“视觉化”的理论分析变化这一例,可以管中窥豹。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城市、都市,相应地也产生了“城市文化”和“都市文化”。曾军在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之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与其称之为城市化不如称之为城镇化;在90年代之后都市化的因素才慢慢扩大。除了对城乡发展状态更准确地概括之外,曾军还指出,在城市文化中“农民性”因素一直处于次要位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认为,只有将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结合,才能对中国都市文化产生更合理的作用和影响。
在对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理解的基础上,曾军提出“城视”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球化处境,以及具体的文学创作、文化现象紧密联系起来。[3]原本两个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融合为一种更为普适性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使都市、视觉,文学、艺术,甚至政治都纳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开阔的理论视野、新的研究领域和迥异的思维方式。
三、“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是各自为政的研究类别,它们互为表里,互相结合。曾军通过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形成了“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通过分析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形成了“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其中一方面,“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曾军用代表性的文学、文化案例,剖析视觉文化对地域性城市中文学观看方式的影响,探索新媒体文学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地位和意义,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方式,辨析政治学视域下的视觉文化和观看的政治学内质。曾军认为《长恨歌》是“城市文化加视觉文化”的绝佳文学案例,作者王安忆将上海作为观看的对象,并且是自觉的自我反观式的观看―――上海作家以独特的“上海人”心理、“海派”文化和“鸽子视角”(一种“非典型性漫游”的观看方式)来关照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曾军通过分析“新世纪文学”来解析“新媒体文学”的概念内涵[4]、价值意义以及隐藏的问题,并认为视觉化艺术形式改变了当代文学生态的权力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众影评是新近崛起的视觉文化现象,“过度而狂热的看客”的主体构成,使其评论大多采用观赏式的“观后感”文体,并且大多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坚守,但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纳垢和众声喧哗特点,又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体现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批评;经典艺术的复制品,由于无法保有原作的“灵韵”而置身于尴尬的处境,但在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观看行为本身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学内涵,曾军分析了看与被看(主体的“屈从性”)中存在的观看的意识形态性,其中既有权力的支配关系,又有文化的认同关系。主体的“屈从性”会产生“情境主义的观看”和“自由观看”[5]这两种相反的情境。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无论是关注地域性的城市代表,视觉化艺术形式的产生,还是套就视觉观看对象的处境,观看行为本身的政治内涵,“城市(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参与到其运作机制和内部构成中。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也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曾军通过具体的区域性文化比较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析了都市化过程中全球性与地域性冲突产生的文化矛盾,并进一步分析都市化可能引发的、尚未显现的新型生产方式、美学空间和文化传承问题。在《城视时代》关注的不是无所不包的城市文化,而是视觉化文化艺术中的“城市”:“海派”和“韩流”都经过了由文化他者指认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并自觉进行文化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而这两种以视觉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性城市/国家文化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海派”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逐渐被泛化,消解到均质化的主旋律中,“韩流”却假借官方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运作大获成功,但二者却都存在着身份认同被质疑的问题;《繁花》是阐释视觉化文学艺术形式、城市文学叙述和地方性文学生产运作的绝佳例子。从地域性小众网络平台(上海“弄堂网”)的出身,到获得纯文学期刊、严肃文学界认可的转换,从作者的网络文学和资深传媒编辑身份的切换过程,使《繁花》介于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双重边缘,虽然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但其实原本两相对立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海派”地域性城市文化特征和新媒体的生产传播方式,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城市文化大多关注高楼大厦等“高度美学”相反,曾军从城市的地下文明空间―――地铁中,探索“深度美学”的内涵。地铁空间将城市的集聚性、流行性和陌生感高度浓缩化和夸张化了,曾军认为地铁空间完全可以假借影像等视觉审美因素,改变封闭、狭窄、陌生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富含“深度美学”的城市地下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不仅有发展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其中论者注意到了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主体因素―――市民,他认为对于城市性文化的过分关注、排斥非城市性文化,是文化传承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狭隘之处,因此应当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通过概括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曾军的“城视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城市文化中分析视觉化因素、现象,在视觉文化中关照城市(空间)维度,这是“城视时代”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曾军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
四、“城市文化”的审美现代性
在《城视时代》中,曾军将方方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口是心非”的叙述特点概括为“潜对话”。“潜对话”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人物与人物、人物的内心与外在表现、人物与作者等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或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点和态度,但这种话语、观念的错位和对立,却被一种隐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呈现。在方方的小说中,不仅有“独白/对话”“私人言语/公共言语”“温和言语/激烈言语”“作者/人物”之间的潜对话;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还有“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间的潜对话。这些潜对话不仅有形式的意义,而且是对人物与时代精神状态之间的错位状态的关注,潜对话能够使公开对话的不可能情境呈现出来,并进行内在的消解颠覆。方方用知识分子的隐忍、自省、颠覆的特点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具有代表性;在熊召正的《张居正》中,曾军也将人物的设置和关系看作张居正改革的“元话语”对话关系。并且他认为,政治改革与文化道德无法分割的特点,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非理性色彩;刘震云的创作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其民间诙谐文化开始呈现为更为鲜明的河南式幽默,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拧巴”,因此曾军从“叙述的拧巴”到“话的拧巴”分析了“拧巴式幽默”的文化特征,他认为,这种具有个性色彩和反讽意味的群体性幽默,来源于人与生活、世界的别扭和错位,而河南作家能将其演化成一种迥异的小说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叙述话语,乃至文学观,其中包含着人们在悖反、荒谬和本真理想之间的错位中挣扎、反抗的文化心理体验。最后,曾军从支配性、主导性文化和审美风格上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美学的凝滞”来指认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总体性匮乏,又提出“凝滞性美学”概念来概括当代美学主流的风格所存在的缺陷。
曾军善于从文化、文学案例的某一细微之处或处于遮蔽状态的因素着眼,思索当代文化问题,并且善于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提升,不仅能追溯至美学现代性上,更能将其置诸于社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社会学、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分析,最终又能落实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中。这种论述方式既可以使略显高深、艰涩的理论辨析和独特、陌生的视角,通过灵动、翔实而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和论据,填补恢宏结构架构中的缝隙,使论述真实可感并且富有信服力;另一方面,论者试图建构多元合一的理论体系,使原本看起来独立的单篇文学、文化现象剖析和某一典型性的观点辨析,呈现为一系列关于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的集束型研究成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研究来说,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鉴性的价值和意义。
并且,曾军将在文化中新近凸显出来的视觉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中显现的城市化“文化化”结合,发掘二者内在的联系,创造出一种“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这种文化视域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自足性与普泛性,使文化研究拥有更广泛的视域,更宽广的理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突围发展的一支脉络,也是文艺批评的创新之路。
注释
[1]“城视时代”可以解释为“城视文化”的“时代”,那么“城市文化”就是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视觉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新型文化理论。相应地,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可以称之为“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
[2]参见《城视时代》第一章第三节《“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
篇(4)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白长虹.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8,(2):80-84.
篇(5)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
(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详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图1)。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篇(6)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篇(7)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数字城市(Digital City,DC)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1]。数字城市的提出成为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亮点,随着数字城市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我国数字城市的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 研究方法、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1.1.1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特定主题内容进行定性定量剖析,提示该主题内容的实质,系统、客观地把握其研究动态和趋势[2]。
1.1.2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数据来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一定研究目的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它是在统计学原理的指导下,在长期文献信息统计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
1.2 统计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关键词”为检索项,“数字城市”为检索词,时间跨度选取2006-2011年共6年的数据,即检索条件:关键词=数字城市*全部期刊*年=2006-2011。检索出符合条件的论文共计1704篇,剔除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共获得有效论文1117篇。
2 数字城市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2.1数字城市研究发文量分析
在cnki学术趋势搜索中以数字城市为主题检索,数据整合分析后得到该领域论文数量在1997-2011年的变化趋势,经分析得:
1998-2003年我国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一直呈现增长态势, 2000年国民经济“十五”规划将信息化列为专项之后,论文数量明显增长,2003年达到顶峰;2004-2006年间研究呈现下降趋势且发文量相对平稳,该阶段论文对数字城市发展中的瓶颈及对策进行了分析;2006年之后该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历史高峰。
2.2论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2006-2011年间数字城市领域论文作者进行统计,获得有效论文作者1771位,其中,李琦发表文献9篇,排在第2、3位的分别是邹逸江、黎林峰,这些作者均为数字城市研究领域的积极型研究者,丰富和发展了数字城市理论。
2.3论文期刊分布分析
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揭示了文献信息集中离散分布规律,该规律有助于选择和确定核心期刊。所谓核心期刊,实质刊载与某一学科领域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4]。
载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中《中国建设信息》、《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与《地理空间信息》载文量最多,载文数量189篇,占论文总量的16.92%,《中国建设信息》刊载量连续3年处于领先地位,为研究者快速查找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热点提供参考。
2.4关键词分析
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近6年数字城市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共计1380个,列举出现次数较多词并对相近的词进行归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关键词统计结果表
序号 关键词 出现次数 所占比例 序号 关键词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1 数字城市 48234.93% 6数据库503.62%
2 地理信息系统 17512.68% 7应用302.17%
3 虚拟现实 977.02% 8 地理空间框架 221.59%
4 城市规划 63 4.57% 9 数字化 211.52%
5 信息化 594.28% 10电子政务 201.44%
3 数字城市未来研究热点
3.1智慧城市的研究是数字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
数字城市领域中核心作者李琦认为:数字城市是智能城市的初级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城市也将向智能城市发展。通过一些核心作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数字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智慧城市将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3.2地理空间框架的研究作为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持仍是研究热点
通过对数字城市刊载量较多的期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与地理空间信息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作为数字城市的一部分,为整个数字化城市管理搭建了一个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可以有效的促进地理信息共享应用,数字城市领域的地理空间框架研究仍是未来研究热点。
3.3数字城市的应用研究将日益增多。
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了解到,截止2012年5月23日,全国已有260余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政府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决策,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因此,在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研究方面,建成后如何依托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水平,以及如何使数字城市建设更好的服务民生方面的研究将日益增多。
4 结语
回顾国内近六年来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数字城市研究文献的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研究主题涉及数字城市的理论、支撑技术和应用等多方面,未来也将逐步向较高层次的智慧城市领域研究,更好的促进城市建设,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数字城市信息共享的几个问题[J].《北京测绘》,2007(4):1-5
篇(8)
中图分类号:F294;N9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同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如城镇体系发展不协调、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相同职能类型的城镇重复建设,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滞后,城镇化进程对资源消耗过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严重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要任务是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基石和前提。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间复杂性的探索,作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其“复杂的非线性”空间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系统领域,才真正开始形成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洪流。由于过分追求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用地矛盾及空间利用“破碎化”等问题,城乡关系优化及城乡空间统筹被提上日程。因此,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扩展到了城市—乡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研究重点和突破研究难点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城乡系统空间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进行详尽梳理,以厘清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脉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2 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2.1 国外城市系统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个主要支流倍受关注:一是分形城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异速城市保持研究逻辑同构;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与动力城市及网格-主体城市存在一定渊源;三是分形与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统一于自组织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发展,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兴起,为传统城市网络系统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支撑,从而奠定了复杂网络城市研究流派。
(1)异速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Clark就发现城市人口密度距离衰减的负指数律(Clark定律)[1],此后许多学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纷纷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间满足幂指数关系,即城市扩展存在异速生长现象,系统建立了系列城市异速生长函数,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负幂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积幂指数模型最具影响力,为此Clark模型的负指数律受到广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与异速生长律同构的分形学派。近年,我国一些学者(陈彦光、刘继生)通过数理推导,统一了幂式异速生长关系与负指数人口分布之间的逻辑不兼容,从而将城市系统纳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体系中[10]。
(2)动力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传统静态空间模型(如引力模型、潜力模型、空间扩散模型、距离衰减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释城市自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城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受到广泛重视。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W.Forrester率先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结构变化研究,创立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Urban Dynamics),即构建一系列反馈城市系统要素关联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构造了城市动态学模型,即构建一组展示城市突变的非线性方程[11]。二者开创和引领动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学者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系统开展了城市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可持续发展预测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运用突变论、协同学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如Amsin的城市突变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区域迁移动力学方程[12]。
显然,动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统构成要素的关联反馈为主,缺乏位置、距离等空间要素的考量,无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间的动力演化过程;部分模型尽管开始考量时空变量,但多以宏观尺度为主,缺乏对个体行为和微观结构引致的空间变化分析。这为后来的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如何从宏观到微观、从系统要素关联推演到城市空间演化?也相应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发。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态、结构的模拟与实证研究,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城市统计分析,但最终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随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期全面地对城市及城市系统的内部空间结构展开分形理论和实证研究[14][15],系统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城市内部形态向内逐渐细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渐扩展到城市体系:微观层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运用分形几何学,从建筑审美和城市设计视角,解析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家居环境、建筑外观等建设和设计理念的“最优形态”。中观层次——城市内部分形,研究最为广泛,内容涉及城市边界、景观、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网络结构等方面[16]。宏观层次——城市体系分形,以城市等级规模、空间作用、中心地体系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应用于城市系统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有学者零星运用CA计算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过程[18]。70年代末,Tobler将CA模型引入地理学,创立“细胞地理学”[19],并率先实证模拟了美国底特律城市扩展过程。受其影响,80年代中期美国的 Couclelis和英国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动态模拟领域开展CA理论和实证研究[20][21],引领一些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作了尝试性及至深入性的应用和扩展。90年代以来,随着GIS技术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实现融合,学术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统研究热潮[22],研究内容集中于城市系统形态生长、土地利用、城市景观、位序-规模等领域[23]。
(5)自组织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论、分形理论、人工智能-生命理论、自组织临界论、自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渐趋合流,形成自组织城市研究学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协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组织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网格-主体城市[36]等领域。
(6)复杂网络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织,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转向网络化视角[37],从空间实体流(全球航空流、货运流、城际交通流、城市-区域人口流等)[38]和虚拟流(互联网、信息流、社会网络、通讯网络、技术研发区位和扩散、生产业网络等)两个方面[39],揭示城市系统关联的网络复杂性研究成为热潮。Taylor构建“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过跨国生产企业空间联系实证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组织方式仍为等级或位序的“累积”[40]。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一些学者从城域(城市内部)和城际(城市体系)两大视角,从交通联系(交通网络、交通流)、社会联系(人口迁移)、企业联系(公司交流、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创新扩散(因特网、电话呼叫、技术交流、创新扩散等)等方面,将复杂城市系统抽象为复杂网络,系统分析了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41],如无标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验证,脆弱性或鲁棒性评价及控制,以及动力学演化与传播特征等。
2.2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哲学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鉴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体系,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突变性等复杂性规律[43,44];普遍认为城市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巨系统,表现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突变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无序与有序交互性等复杂性质[45,46]。二是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或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或者创新性建立城市空间演化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和前缘[47,48]。
与国外一样,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计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统研究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两大阵营:城市内部和城市体系,但主要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与国外的多样研究学科背景不同。同时,研究的内容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49]和空间演化[50]复杂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借鉴分形理论、元胞自动机等复杂科学理论,从城市内部景观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网络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分形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体系和元胞城市为代表[51]~[54]。后者侧重运用突变论、系统动力学、灰关联系统、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开展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相变及突变)和动力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定量研究和模拟预测,如动力城市[55]、自组织城市[56]和主体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静态数学模型[58](等级体系标度模型、城市统计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动态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网络动力学-细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组织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拟模型[61,62](多主体模型、遗传算法、虚拟城市模型等)为主,内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城市规划、人口分布和迁移、景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就业和居住、城市体系及等级规模分布等方面。张新生归纳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实现威尔逊模型的扩展[63]。孙战利将主体(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层和动态交通层,构建了城市动态演化模型,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空间变化与属性变化相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并在GIS的支持下,对美国Ann Arbor城动态发展进行了模拟[64]。陈彦光借鉴自组织理论,提出城市系统复杂性检验的三大判据:分形结构、Zipf定律和1/f噪声[65],并系统运用分形理论,实现实空间-相空间-序空间的统一,构建了系列蕴含静态和动态、功能和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拟和预测于一体的分形城市系统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广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空间动力学模型、等级规模模型、自组织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城市和农村孤立起来分析,城乡关系研究薄弱。上世纪末,一些学者纷纷呼吁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认为关系(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及其空间结构(景观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规律研究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发展型面临突出结构性问题和缺陷,城乡之间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联系,表现为“脱臼的经济”(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们才开始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城乡对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乡互动”(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乡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视野和切入点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问题呈日益复杂的态势,解决这种复杂城乡关系失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乡村-城市关联观”(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则从城乡关系网络视角,明确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化模式。
但这种城乡关联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对空间的关注相当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乡经济社会差异(社会问题、健康卫生、政策体制、意识形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产业联系、资源和资本转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乡关系作用的复杂性问题[76],专门而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交错带(边缘区),普遍揭示出其空间结构的动态过渡性、人口社会学特征多元化、经济发展复合型、土地利用多样化等复杂性特征[48],以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Desakota”空间研究为代表[77]。
3.2 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是一个泛合的概念,涉及社会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视角集中于空间区位关系(地理学)、工业-农业关系(经济学)、市民-农民关系(社会学)、斑块-基质关系(生态学)四个层面[78]。地理视角上的城乡研究倍受关注,成为热点,已经形成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论涉及城乡融合论、城乡协调论、城乡一体化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网络化发展论等[79-81];研究区域触及中国和外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区和非密集区、沿海热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82-84];研究时间尺度以建国以来为主,并考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影响[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关联协调模型为主[87,88];研究内容主要从城乡联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乡关联的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协调对策及发展模式等[89-91],总体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不考虑城乡地域空间差异性,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二是研究城乡关系的静态空间分异与组合,而忽视其地理变化过程的自组织性。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使得二者在空间上越来越隔离,同时也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二者的统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城乡空间统筹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幅员辽阔,各类城市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也为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文献回顾与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成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无论是国外的自组织城市(耗散城市、协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细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体城市),还是国内的分形城市、自组织城市、元胞城市、虚拟城市、城市系统动力学、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多是借鉴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论城市”,对城市体系(inter urban)和城市内部(intra urban)空间复杂性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区域的重要载体——乡村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落到被忽略的边缘。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仍处于呼吁和倡导的阶段。
(2)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来看,方法集成综合研究不强。分形理论和CA模拟技术的融合以及在协同论、耗散论和混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虽体现了学术界集成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复杂城乡空间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子系统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论、空间句法或系统动力学的某个单一理论,综合多学科、多理论对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统的空间关联分析不足。而且,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个时间断面进行考察,而对于城乡空间动态变化描述和模拟则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补充。
(3)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今后城乡空间统筹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化:①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研究。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当前,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是由物质、经济、人口迁移、社会、服务供应、政治行政联系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构成的一个动态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研究几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涉足城乡耦合、关联、协调的非线性规律和城乡关系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②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建立了相关模型解释城市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而对于城乡空间演化过程的分叉与选择、混沌与有序、渐变与突变、竞争与协同、集中与分散等作用机制讨论,利用开放性、非线性、不平衡、环境选择等原理对自组织临界性、相变性等过程的逻辑、实证和类比判据将会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对城乡空间生长的模拟将会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范围、规模,解释城市变迁的内在动力,透视城市化的本质,更好预测控制城市的发展;③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研究。以城乡道路网为载体的城乡关联空间的复杂结构正逐渐被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认识,打开地理学研究主页,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探索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④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研究。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对城乡人口空间分布,市场网络分形,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别是信息要素空间传播、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关系等虚拟城乡社会网络,更需填补研究的盲区。
参考文献:
[1] Clark C. 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 [J].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1, 114: 490-496.
[2] Naroll R S,Bertalanffy L. The principle of allometry in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J]. 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1956(1): 76-89.
[3] 房艳刚,刘鸽,刘继生.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05,25(6):754-761.
[4] Smeed RJ. Road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J]. Journal of the Institution of Highway Engineers, 1963(10): 5-30.
[5] Nordbeck S. The Law of Allometric Growth[D]. Ann Arbor: Inter-University Community of Mathematical Geographers Michigan Discussion Paper, 1965: 7.
[6] Nordbeck S. Urban allometric growth[J].Geografiska Annaler,1971(53): 54-67.
[7] Gould S J. Allometry and size in ontogeny and phylogeny[J]. Biological Reviews, 1966(41): 587-640.
[8] Dutton G. Criteria of growth in urban systems [J]. Ekistics, 1973(36): 298-306.
[9] Lo C P, Welch R. Chinese urban population estim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67): 246-253.
[10] 刘继生,陈彦光.城市密度分布与异速生长定律的空间复杂性探讨[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6(4):139-148.
[11] Wilson A.G. 蔡运龙,译.地理学与环境-系统分析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 张新生.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研究及其应用[D].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7.
[13] Mandelbrot B B. Fraetals: Form, Chance, and Dimension [M].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7.
[14] Batty M. Fractals-geometry between dimensions[J]. New Seientist,1985,106(1450): 31-35.
[15] Batty M, Longley P A. Fractal Cities: a Geometry of Form and Function[M]. London: Academic Press,1994.
[16] Batty M. Fractals: new ways of looking at cities[J]. Nature,1995, 377: 574.
[17] Arlinghaus S L. Fractals take a central place[J]. Geografiska Annaler,1985,67B: 83-88.
[18] 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1968(2): 375-390.
[19]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1968(2): 375-390.
[20] Couelelis H.Of mice and men: what rodent populations can teach us about complex spatial dynamics[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A,1988(20): 99-109.
[21] Batty M, Longley P A. The morphology of ubran land use[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B,1986(15): 461-488.
[22] White R, Engelen G. Urban systems dynamics and cellular automata: fractal structures between order and chaos[J]. Chaos, Solitons&Fractals,1994,4(4): 563-583.
[23] Clarke K C, Gaydos L J. Loose-coupling a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and GIS: long-term urban growth prediction for San-Francisco and Washington, Baltimo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30): 1857-1872.
[24] Allen P?M, Sanglier M. Urban evolu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81(13): 167-183.
[25] Portugali J. Self-organizing cities[J]. Futures,1997(29): 131-138.
[26] Allen P M. Cities and Regions as Self-Organizing Systems: Models of Complexity[M].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 1997.
[27] Prigogine I, Allen PM. The challenge of complexity[A]. Schieve W.C. andAllen P.M. Self-Organization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s: Applications in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3-39.
[28] Haken H.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3rd edition)[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3.
[29] Haken H. A synergetic approach to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cities and settlement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1995, 22(1): 35-46.
[30] Dendrinos D S. The Dynamics of Cities: Ecological Determinism, Dualism and Chao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1] Zanette D, Manrubia S. Role of intermittency in urban development: a model of large-scale city formation[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97, 79(3): 523-526.
[32] Portugali J.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City[M].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0.
[33] Webster C., and Wu F. Coarse, spatial pricing and self-organizing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01, 38(11): 2037-2054.
[34] Bura S, Guérin-Pace F, Mathian H, Pumain D, Sanders L. Multi-agent systems and the dynamics of a settlement system[J]. Geographical Analysis,1996(28): 161-178.
[35] Benenson, I. Multi-agent simulations of residential dynamics in the city[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1998, 22(1): 25-42.
[36] Haken H, Portugali J. The face of the city is its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23): 385-408.
[37]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8] Jiang B, Claramunt 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the model generalization of an urban street network[J]. Geoinformatica, 2004, 8(2): 157-171.
[39] Townsend A M.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10): 1698-1717.
[40] Taylor P J. Derudder B,Witlox paring airline passenger destinations with global service connectivities:a worldwide empirical study of 214 cities[J]. Urban Geography, 2007, 28(3): 232-248.
[41] Batty M. Faster or complex? A calculus for urban connectivity(editorial)[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 2004(31): 803-804.
[42] 周干峙.城市及其区域——一个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城市规划,2002,26(2):7-9.
[43] 盛强.城市迷宫——空间、过程与城市复杂系统[J].世界建筑,2005(11):92-95.
[44] 范诚.理解策略——以库哈斯的视角看当代城市的物质形态突变[J].建筑学报,2004(3):21-24.
[45] 周一星,陈彦光.城市与城市地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1,41.
[46] 吴晓军,薛惠锋.城市系统研究中的复杂性理论与应用[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3-4.
[47] 王铮,邓悦,宋秀坤,等.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1,20(4):331-340.
[48] 薛领,杨开忠.复杂科学与区域空间演化模拟研究[J].地理研究,2002,21(1):79-88.
[49] 陈彦光,罗静.郑州市分形结构的动力相似分析——关于城市人口、土地和产值分维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01,21(4):389-393.
[50] 黄泽民.我国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过程分析——克鲁格曼模型借鉴与泉州地区城市演化例证[J].经济研究,2005 (1):85-94.
[51] 徐建华,梅安新,吴健平.20世纪下半叶上海城市景观镶嵌结构演变的数量特征与分形结构模型研究[J].生态科学,2002,21(2):131-137.
[52] 陈彦光,刘继生.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形态的定量描述:从信息熵到分数维[J].地理研究,2001,20(2):146-152.
[53] 刘继生,陈彦光.长春地区城镇体系时空关联的异速生长分析(1949-1988)[J].人文地理,2000,15(3):6-12.
[54] 冷炳荣,杨永春,李英杰,等.中国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空间特征及其复杂性分析[J].地理学报,2011,66(2):199-211.
[55] 王晓琴.基于空间动力学的城市用地扩张策略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56] 张勇强.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研究——以深圳市为例[D].南京:东南大学学位论文,2003.
[57] 孙建平.Agent的城市交通区域协调控制及优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58] 陈彦光,刘继生.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空间互相关和功率谱分析——引力模型的理论证明、函数推广及应用实例[J].地理研究,2002,21(6):742-752.
[59] 董益书.基于GIS的城市动力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
[60] 黎夏,叶嘉安.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城市发展密度模拟[J].地理科学,2006,26(2):165-172.
[61] 薛领,杨开忠.城市演化的多主体(multi-agent)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12):1-9.
[62] 刘妙龙,陈鹏.基于细胞自动机与多主体系统理论的城市模拟原型模型[J].地理科学,2006,26(3):292-298.
[63] 张新生.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研究及应用[D].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7.
[64] 孙战利.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地理时空动态模拟研究[D].北京:中科院博士学位论文,1999.
[65] 刘继生,陈彦光.城市、分形与空间复杂性探索[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4,1(3):62-69.
[66] 陈彦光.分形城市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67] Bathelt H., Glucker. Toward a relation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2): 117-144.
[68] Yasusada Murata.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68): 1-34.
[69] Dixon, D. 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A].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Developing Area Research Group, 1987.
[70] Scarlett T. Epstein, Jezeph David. Development-there is another way: a rural-urban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paradigm[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8): 1443-1454.
[71] Potter Robert B. and Unwin Tim. Urban-rural interaction: physical for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J]. Cities, 1995, 12(1): 67-73.
[72] Oucho John. Enhancing positive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some experienc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C].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detail.asp?articleID=219, 2004.
[73] Cooke, P., Morgan, K. The network paradigm: new departures in corporate in corporat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Society and Space, 1993(11): 543-564.
[74] Murdoch Jonathan. Networks: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16): 407-419.
[75] OECD.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C]. Paris: OECD, 1996.
[76] 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73):17-24.
[77] Ginsburg, N., Koppel, B., and McGee, T.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47-70.
[78] 马远军,张小林,李凤全,等.我国城乡关系研究动向及其地理视角[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22(3):78-84.
[79] 王振亮.城乡空间融合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城乡空间关系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0] 许学强,等.中国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81] 曾菊新.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2] 李泉.中外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与启示——兼论西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J].开发研究,2006 (5):56-60.
[83] 余斌,曾菊新,罗静.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空间创新研究[J].地理科学,2007,27(3):296-303.
[84] 胡国良,张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关联发展综合评价—以新疆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0):4774-4778.
[85] 张立艳.建国以来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86] 刘玉.信息时代城乡互动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3 (1):33-36.
[87] 曾磊,雷军,鲁奇.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21(6):763-770.
[88] 张竟竟,陈正江,杨德刚.城乡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2):5-11.
[89] 奚建武.城乡关系变迁的新动力——基于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视角的分析[J].城市问题,2009(6):49-53.
[90] 汪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城乡政策及城乡关系的演变研究[D].合肥: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91] 楚材,陈雯,顾人和,等.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协调对策[J].城市规划,1997,21(5):38-40.
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篇(9)
一、学术界研究概况
1.有关学习型城市理论方面的研究
对于学习型城市理论的研究集中在阐述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学习型城市理论根源、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必然性等方面。
关于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国内并没有达成一致。叶忠海(2011)就学习型城市的内涵与价值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学习型城市以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为生存背景和发展空间,以学习和教育为最本质职能,以社会化的终身学习和教育体系为基础,能保障和满足城市市民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有效地促进城市人全面发展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开放、创新和发展的和谐城市。苑大勇(2004)从全球经济变革的转型时期出发,认为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在全球变迁的特殊时期努力学习更新自己的城市。而学习型城市由哪些部分组成?许学国,山鸣(2003)则认为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以及学习型政府是学习型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于学习型城市的理论根源问题,奚洁人(2003)认为其发端于终身学习、 终身教育理念的形成和企业界学习型组织管理理念的确立。郑金波(2003)从我国学习型城市的实践起源出发指出我国学习型城市源于我国学习型组织的浪潮,上海成立“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随后又在北京、济南、南京、昆明等地成立了研究分所,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一些大城市受其影响先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口号。学习型城市是时展的产物,它的提出,有其客观必然性。叶忠海(2011)认为学习型城市的提出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需。
2.有关学习型城市专题探讨方面的研究
有关学习型城市专题探讨方面的研究主要结合图书馆、远程教育以及社区等各类场馆、组织机构分析他们应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
白淑春(2008)认为城市图书馆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组成分,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必不可少的元素。为城市营造了一个公平文明的环境,在促进城市的和谐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余海(2010)指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服务职能、环境优势决定了图书馆在创建学习型城市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高明(2004)也认为图书馆要主动介入学习型城市的创建中,自我加压,在自身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徐皓(2013)以上海开放大学为例,从上海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定位出发,把上海开放大学定位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蒋红(2012)也认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是上海开放大学的基本功能 ,而实现二者并举的关键在于衔接 。
社区是人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在城市中处于最基础的组成元素,是城市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托和落脚点,陈雅丽(2003)认为学习型社区有利于社会稳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有关学习型城市经验总结方面的研究
20世纪末以来,我国已有近百个市(地)级以上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标并进行了实践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可喜的成绩,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就全国而言,学习型城市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认识不到位、任务不明确、职责不清晰等问题。
袁雯(2012)介绍了上海建构终身教育体系的实践与成果,包括建立多元化的终身教育基础平台,为市民创造丰富的终身学习机会;举行丰富多彩群众文化活动;构建终身教育信息化平台,便捷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制定《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形成法律依据等。徐文龙(2001)提出上海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对策,在总体目标下,需要分类设计,依据不同的年龄、从业和学习要求分别确定学习目标。
孙善学,张翠竹对北京学习型城市创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著作《北京学习型城市案例分析》精选了6各区县、9个街道、7个乡镇共22个创建工作突出的地区、社区或单位的典型案例,反映北京市以地域和社区为创建单位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思路和方法,陈建林(2003)在分析重庆的基本情况,提出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基本思路。
4.有关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
叶忠海(2013)认为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科学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特色性原则、现实性原则以及简明性原则,将学习型城市一级指标评定。周素萍(2014)在综述国内外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观点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级指标为资源指标、科技指标、经费指标、文化指标、信息指标、交流指标、人口素质、绩效指标;二级指标为学校、 师资、图书、报纸、档案、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机构、科技人员、科技活动、教育经费、科技经费、文化机构、从业人数、群众文化活动、信息化、媒体、网站、网络教育、国际交流、国内交流、高等教育普及率、平均学习年限、学习时间、出版图书、课题、论文的二级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学习型城市的研究络绎不绝。关于学习型城市,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剖析与解读。
就理论研究方面来看,主要是针对学习型城市的内涵、构成要素、理论基础、以及构建学习型城市的价值意义。很少有涉及学习型城市提出的实践背景,从理论和实践整体上把握学习型城市的理论基础,对这一方面的梳理更是屈指可数。
其次,就构建学习型城市经验来看,大部分城市结合自身实际城市特点,借助国外及国内成功经验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上迈出了崭新步伐。但是文章只是在一个或两个方面系统阐释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就目前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城市的衡量指标没有明确的说明。学习型城市开展的如何?取得那些实效?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这些问题应该成为研究的中心。
再次,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大部分学者只是从评价的原则,或是从某一城市的实际出发制定评价的标准,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较少,不具有整体性与宏观性。
最后,关于学习型城市的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大多采用文献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但是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从理论与实践上整体进行把握,全面进行分析,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并不多。
参考文献
篇(10)
一、国外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兴起源于城市旅游的快速发展,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普遍出现制造业长期衰退、高失业率现象,在创新城市经济的过程中,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型产业因其良好的产业特性和符合消费时代需求的巨大发展潜力推动了城市中心区的复兴,在1990年代快速成长为一个显著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对城市旅游研究的关注主要来源于现实: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解决旅游者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对历史城市旅游的需求所带来的到访率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很多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城市将城市旅游作为城市复兴战略的政策。
城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研究。供给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市场和形象研究。城市旅游产品研究,包括城市吸引物研究、城市文化旅游研究、城市遗产旅游以及城市事件旅游。城市旅游影响研究,包括经济影响研究、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环境影响研究、居民影响研究,以及其他因素对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管理与规划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管理研究、城市旅游规划研究、城市旅游的空间结构研究等。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困难地区”的旅游、城市旅游统计的标准化和城市景观评估的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界对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学科体系建设等主要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探讨,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根据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现状,选取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热点问题为线索,理清其主要的理论观点,梳理和勾勒出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学术前沿态势。
2000年和2001年的旅游研究侧重于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行业发展现状、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研究,这与当时全国许多省(区、市)几乎都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将旅游业列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或列为当地优先扶持发展的产业现状有关。2002年和2003年在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旅游规划创新、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有了深入地研究,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有趋热的表现。2004年和2005年的旅游研究朝着实证和规范的方向发展,旅游研究的视角更为宽泛,研究主题的趋热点不明显,各个层面的研究趋于平衡。生态旅游、民俗旅游、会展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的概念和开发思路更为明确。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和更多参与。
近年来对城市旅游产品的开发,开始触及温泉旅游、影视旅游、俱乐部旅游等休闲娱乐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城市旅游的研究对旅游经济、旅游规划理论和实践、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及发展模式的一般理论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重视。对旅游经济和曾经对旅游业产业地位、产业政策、旅游发展阶段、旅游市场化发展与政府行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等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的研究落在更有现实和发展意义的遗产旅游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上。
中国旅游城市国际化、世界化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城市旅游的研究落定了座标,明确了方向,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业内人士及专家学者对中国旅游城市如何登上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舞台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分析对比,理论著述以及相关战略对策,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更为积极的抗争因素,有力激励了中国旅游城市创建的市场。
由于城市旅游的基本概念存在着诸多外延,无明确一致的定义,又无成功的旅游城市发展经验以供借鉴和推广,导致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使现实的城市旅游经济行为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和背景,难以形成“真正的”城市旅游学的系统理论。另外,我国对旅游城市的研究视角过多集中在对旅游客体的评价和开发上,缺乏以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对旅游主体在文化、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对于国际旅游前沿问题,缺乏将需求导向型与技术导向型有机结合的理论平台;目前国内旅游研究尚未真正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旅游、赌博与旅游等与中国社会伦理文化发生冲突的敏感性问题,但这是理论界在研究旅游与现代性之间关系不可忽视的现象,城市旅游所追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理性需求刺激与理性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这是我国研究城市旅游活动国际化、市场化必须正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篇(11)
2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界尤其是城市地理研究中强调“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或“关系转向”。这些因素在解释城市化中虽然不可能完全替代经济因素,但其对重新解释经济因素对城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在城市化中起重要的作用,海外学者在解释中国的城市化时大都强调要有政治经济的观点[4,5,6]。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力图使其概念化,有些理论与概念的提炼在国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
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建国后,中国工业发展与城镇化是不相协调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资本主义的消费地和寄生地,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决心要实现城市由消费地向生产地的转变。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上限制了城市化,背离了城市化过程。ma和hansen在题为“现代中国城市发展”一书中对这一现象概括为“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事实就是“减少城市化成本,来扩大工业化的发展”[7]。ma认为中国以农民和农村为根据地,反对修正主义,其意识中存在反城市化的倾向,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概念(antiurbanism and counterurbanization)[8]。
这一概念提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控制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的真正动机是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考虑,还是从城市管理和国防考虑[9,10]。虽然仅是一家之言,但平均主义及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及方针的确有较大的影响[11,12]。lin将其概括为“有限城市化下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limited urbanization)[13]。zhou和ma,针对时期城市“人口过剩”,城市人口超过城市经济发展的现象,概括出“表象城市化”的概念(spurious urbanization)[14]。ma和wei认为,指导中国发展考虑的是均衡、 国防和经济三大原则[15]。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乡村人口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但这些人口进入工厂并未进入城市,出现离土不离乡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并不多见。这一现象被称为隐性城市化(hidden urbanization)。传统的经济决定与城乡分割的城市化分析方法也受到了挑战。围绕着mcgee的desakota概念,有关学者进行了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分析[16]。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有两条: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以前,以计划经济和以城市作为增长极的发展路径;另一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自发产生的,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化。第一条发展路径是至上而下的发展路径,与第二条发展路径相对应,ma及其他学者[17] 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揭示了随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遍布全国的城镇在中国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一条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仍存在争论,但在主流地理学界,强调制度、私有化、地方化的大背景下,他代表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者的声音,以及与主流地理界的争辩。
随着外资流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一步加速[18],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外向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 及外向驱动工业化(externally driven)及城市发展的概念与理论[20]。也提出了“二元城市化”的概念,认为一方面存在政府引导下的针对非农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存在农业人口自发的城市化[21]。国际化及外资促进了苏南经济转型,传统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被外资企业及外向型经济所替代[22]。 3 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多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全球化使资本、人口、技术、信息等要素跨国流动加剧,形成了许多跨国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空间结构重组。全球化突破了传统国界的限制,使得中外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对城市与区域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城市发展受制于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社会空间结构受全球化的影响明显。全球化在不同层次的表现被认为是重塑城市的要素之一[23]。全球化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集中于作为全球化战略的全球资本和产业的重组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全球市场力的运作与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城市地理研究跨越空间限制,成为一个新的学派,其强调从全球经济重组到跨国资本的流动性和建立全球城市网络及城市空间的变化。
外资是全球范围内城市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2003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一般的公司区位选择不同,外资区位具有一些独特性,如对地区环境较为敏感,尤其是政府政策及中国的转型经济。leung 指出中国外资分布不均衡主要是由于现存的亲缘关系的不平衡[24]。eng和lin进一步指出新建立和已建立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接近市场,也有利于处理与地方的关系[20]。hsing强调台湾生产厂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文化亲近的重要性。共同的文化因素在最初区域全球化阶段尤为重要,如香港资本向珠江三角洲流动,台湾资本向福建的厦门和漳州流动都是明显的例证[25]。但是,随着地区全球化的深化及各种形式、水平的竞争的发展,这种文化联系对外资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 市场和公司的作用加强。 如在2000—2001年,大量的台湾资本由珠江三角洲、福建流向长江三角洲[6]。
海外学者也对中国大都市内外资的投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大都市区的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在城内遵循经济合理性,可以从经济和政策方面进行解释[26]。除传统的如靠近铁路、集聚因素、劳动市场外,靠近高速公路、高档宾馆外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区位选择促进了城市的转型,加速了城市多中心发展格局的形成。开发区的政策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影响重大[27]。
全球化的生产加速了世界城市的发展,城市区域成为迅速成长的新的经济和空间现象。这些城市区域是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节点,在货物、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方面起枢纽作用,以其大小和经济实力对各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城市区域肯定会重塑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模式[6]。在近二十年来,外资的大量流入,使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投资的密集区,促进了城市区域的成长,被称为崛起中的国际城市区域[28]。虽然对国际城市区域尚未有一个标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城市区域的潜力和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化城市区域的研究集中于上海一长江三角洲[22,26],香港一珠江三角洲[16,29]及京津地区[30,31]。wei对苏南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苏南模式并向西方学术界深刻地阐明了地方政府及地理环境对国际化的决定性影响[5];对杭州的研究揭示了转型和国际化交互作用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及转型[22]。此外,通过分析京津地区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及挑战,阐明了制度及地理区位条件在国际城市崛起中的重要性[31]。
全球化对城市社会空间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转型结合,使得中国的城市空间更趋复杂化。这种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城市社会分层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下岗工人,另一方面涌现出私营企业者,外资白领等,其收入差距巨大,出现城市社会的分层与极化。从上海房地产价格空间差异入手,发现住房商品化使得上海在解放前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复活,城市商业发展,住房私有化都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32]。②全球化加剧了中国沿海与内地的差距[33],使得大批劳动力涌向沿海,沿海城市在享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城市社会问题[34,35]。③全球化也促进中国乡村人口向大城市迁移。事实就是乡村人口迁移选择以本土关系为纽带的路径[36],这种被概念化就是“地方的力量”(power of place)。 ④由于城市内部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及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沿海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设立总部和分部,服务业的逐步开放及集聚化的要求,我国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的建设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30]。
历史上全球性的贸易、人口流动等是全球化的重要背景,对全球化起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华人移居海外,形成了强大的华人集团,ma和他的同事把海外华人群体(chinese diaspora)作为一个包含地点的系统。这个空间动力系统由源于同一地点的人群所组成,包含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构成及分布[37]。这一理论与概念,在与西方主流理论的争辩中,增加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声音,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对恢复了海外华人的祖国情结,在构建全球部落和民族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38]。一个全球华人“资本主义”的帝国,从美国曼哈顿到硅谷,从香港到台北,再到珠江三角洲东莞的村庄,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4 体制改革与城市转型
最近中国城市研究集中于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下的城市过程和机制转型[6,39]。中国体制改革是渐进性的、实验性。不是简单的拷贝西方资本主义,但希望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6,27]。转型时期,海外学者很少用资本主义描述中国的经济性质,但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剧,资本主义的色彩似乎越来越浓[40]。影响中国城市转型的体制因素较多,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财政和行政分权、政企分离等方面。许多人认为政治经济因素对城市转型的影响最为关键[6,23]。wei提出从中国体制改革的三大过程,即地方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及地方、政府及海外投资者三大主体进行剖析,来研究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机制[33]。研究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及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世界各国罕见的,并从分权,市场化,国际化及空间结构重组来分析导致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因素,弥补了主流理论对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国际化及其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研究的不足[23]。wu认为,城市转型是一种城市过程,不仅指土地开发和住房商品化的具体过程,而是根本性的政治经济过程[41]。
体制改革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城市的政府与管制行为,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对转型经济,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在组织经济中的作用都有一些新观点[33,40,4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管理体制行为趋于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地方拥有更多的财政自,住房商品化,土地租赁市场的建设,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也靠市场力量推动。私有化现象相当明显[43]。地区组织和政府、城市地区、街道办及居委会等具备更多的管理职能,这反映了政府意欲创造一个可管理的社会,以对付诸如社会救济、下岗工人再就业、流动人口等问题。政府分权和服务职能的市场化,引发了中国城市向企业家城市的努力。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中国城市逐步由生产地向企业家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转变,其结果使城市之间及城市区城间竞争加剧,这种“地点营销”(place promotion)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41]。
的确,中国的城市转型创造了新的城市空间,这些新空间,从国营百货店租赁柜台到城市写字楼、摩天大楼、高新开发区、科技园,到外国零售店、购物中心及购物综合区、乡间别墅、大学城、开发区、金融街和商业中心,构成了新的城市景观和城市空间。这些空间包括如下几类:一是城市社会空间,二是城市消费空间,三是城市边缘空间,四是城市全球空间[41]。
城市社会空间:由于从福利分房向住房商品化转变,引起城市生活和产业的深刻变化[44,45]。原有依附于单位福利分房,使工作地与住处在一起的情况在减少,大量商品房建成。城市社会差异从房价空间差异可明显反映出来,均质的社会均衡被打破,出现了富人区和穷人区的隔离。这种社会空间的分异受以下几种因素制约:历史发展的差异,住房供给形式,全球化的程度,城乡的体制及文化历史。
城市消费空间:近年来,城市消费由改革开放初的货摊式走向超市、购物中心、步行街,现在郊区购物广场也相当时兴。根据不同档次住宅,周围形成不同档次的消费空间。城市消费及服务业国际化趋向明显。许多城市根据文化传统及国际影响、品牌等建造光怪陆离的消费空间以提升城市形象,作为城市现象展示区。伴随零售业的改革及对外开放,零售业向多元化发展,家庭、私营、外资及股份制企业构成城市的新的商业网络,形成了新的城市消费空间[46]。
边缘空间:边缘空间是有种族和族源等原因产生,是城市隔离及城市体制所引起的。由于在土地和住房市场的排斥,乡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不得不选择在城市边缘居住,把城市村庄作为居住地,形成“城中村”[36]。
全球化空间:由于外资大量投入而产生的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金融贸易区等。国内主要城市争相发展中央商务区(cbd),提升国际化,争取成为国际资本向服务业投资的集中地。一些国际盛会如2008北京奥林匹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创造更多的全球化空间。
5 城市地理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近20多年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但面对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变化如此巨大的城市。检讨目前的研究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许多研究仍沿着传统的研究路径,重经验研究,忽视理论概括和模型建立,与主流地理研究相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②详实的、可靠的数据分析及野外考察不足,使得分析较为肤浅;③政治经济体制对城市及其转型有重要影响,但分析性论文仍然偏少;④与主流地理学界的交流仍待加强;⑤现代地理技术与方法如gis在城市地理的应用仍然有限。
目前,中国城市地理发展面临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艰巨任务。应该看到,完成这个任务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①中国在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不断开放并与西方接轨,中国提升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并不断有新的内容,中国城市发展、结构、转型的速度与尺度是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这为中国城市地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条件;②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学生在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在理论上相对训练有素,方法上与西方接轨,这些海外学子成为中国与西方联系的重要纽带,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广泛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为城市地理的理论与方法更新提供了人才和知识支持;③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界有关组织的支持下,80年代以来,中国统计机构越来越多的统计信息,有助于经验性的研究及理论提升与概念化;④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个挑战,但也提供了机遇。西方较为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扩散,为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掌握先进的研究技术与方法,提供了机遇。
中国城市地理的理论应如何建立?近年来,我们已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学派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在没有形成我们的理论与概念的情况下,借鉴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必然的。但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经历几十年前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理论适合于中国,如果现存的西方理论不理想,是否还有重建理论和概念的可行途径?如果现存的理论应用不是十分理想,是否还有理论借鉴,这些理论是否可用于理论重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