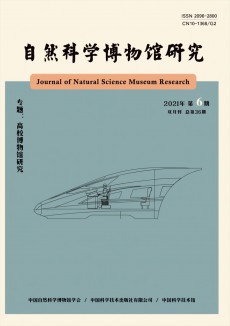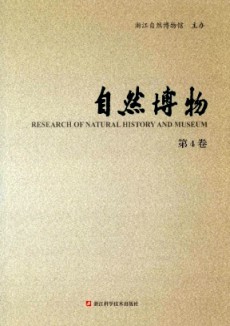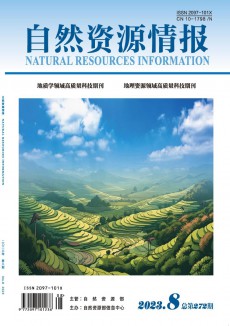自然保护的概念大全11篇
时间:2024-02-28 14:43:19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1)
本文拟对欧盟指令、英国及德国法中的消费者概念进行比较,并分析涉及有关消费者概念的判例,对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概念提出笔者的想法,厘清消费者保护的主体范围,以便在市场交易中更准确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欧盟指令中的消费者概念
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通过条约、规章以及指令的形式,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其中,指令的作用尤为明显。在欧盟指令中,基本不存在对消费者概念的统一定义。虽然立法者根据不同的情境和保护目的,在欧盟指令中对消费者的概念进行设计,但在不同的欧盟指令中,却包含了极为相似的消费者概念。
在欧共体《上门销售指令》和《消费者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指令》中,消费者被定义为:“以......为目的的行为,而该目的不能够归属于营利的或职业的活动的自然人”。
在欧盟《远程销售指令》以及《消费者商品销售指令》中有着极类似的定义:“以……为目的的行为,而该目的不能够归属于营利的或职业的活动的任何自然人”。
而在欧盟《电子商务指令》中,消费者的定义有了些微的改变:“为一些目的的行为,而该目的不能够归属于营利的、商业的或职业的活动的任何自然人”。
从上述指令对消费者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其中的些微区别与发展:
其一,在《上门销售指令》中,“目的”作为名词用的是单数形式,而在其他指令中却用的是复数;
其二,与其他指令相比,在《电子商务指令》中,不仅仅规定了消费者的行为是非营利的、非职业的,而且还应是非商业的活动;这些指令均用否定地形式界定了消费者的行为范畴。虽然在《电子商务指令》中,在“非营利的”与“非职业的”之外,又增加了“非商业的”活动限定,但这样的区别没有实质意义。此外,指令中“目的”的单复数区别,是基于合同标的物既可供私人使用和又可供业务使用,即“两用(dual-use)”目的的考虑。譬如购买汽车或笔记本电脑,既可用于私人生活也可作为业务经营使用。时至今日,尽管欧洲法院没有特别针对上述法令,对消费者概念中有关“两用”问题的解释做出决定,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欧洲法院的判例,推断出其发展的趋势:原则上对消费者的概念作限制解释。
欧洲法院认为,“在‘两用’目的的情况下,并非要当职业性的使用目的占主导地位时,才不适用消费者保护条例。由上述判例可见,在“两用”合同中,只有当职业性的使用目的占次要地位时,才适用于上述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令。
我们在欧盟现行合同法原则(Acquis Principles)中也能找到同样的观点:“为一些主要目的的行为,而该目的在其企业性的活动之外的任何自然人。”
在上述欧盟指令以及现行法原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共同的规则:
1.消费者的概念应局限为自然人;
2.参考交易的目的;
3.将营利和职业性的目的排除在外;
4.判断交易活动是否归属为营利和职业性的目的。
如上文所言,从欧洲法院历年来的判例来看,对消费者概念作限制解释。因此,创业者或合伙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如Benincasa 诉 Dentalkit Srl一案中,原告作为创业者,虽仍为自然人,但却以未来的商业性活动为目,因此不属于消费者。欧洲法院认为:“在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消费者的特性时,消费者的概念需作限制解释,它取决于具体合同中,当事人的身份与其目标及本质之间的关系,而非根据其主观身份来确定,作为缔结合同的原告,以从事非当前的,而是未来的职业或营利的活动为目的,不能被视作消费者。”
相较德国民法,欧洲法院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调整范围作更为严格的规定。通过这些判例中欧洲法院对消费者概念的限制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在欧盟指令中的消费者概念是相对独立的。
二、英国法中的消费者概念
在英国法中,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消费者概念:
1.“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出现在1977年的《英国不公平合同条款法》,在1979年修订的《1893年英国货物买卖法》 的第61条第(1)款和第(5a)款中,同样沿用了前者的消费者概念;
2.“欧化”的消费者概念则来源于按相关欧盟指令转化为英国的国内法。
(一)“传统”的英国消费者概念
在《英国不公平合同条款法》中,通过对消费者合同的定义引导出“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其中第25条第1款规定:“合同中的一方(消费者)既非在业务过程中交易(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也没有令人以为其在业务过程中交易,”及在本法第15条第2款(a)项提及的合同中,“货物以通常的方式供应给私人使用或消费;”
此外,在该法第12条第1款中规定:“在符合以下情况下,立约的一方与立约的另一方交易时,即属‘以消费者身份交易’
(a)他并非“在业务过程中(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订立该合约,亦没有令人以为他在业务过程中立约的表现;
(b)另一方是在业务过程中订立该合约;及
(c)如合约受售卖货品的法律……,根据该合约或依据该合约移转的货品,属于通常供应作私人使用或消费用途的类型。”
在英国法中,很早就已产生了“角色特性”的消费者概念,由于在市场交易中经营者往往拥有更多关于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并通过营销与格式合同等手段使得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通常扮演着弱势角色。英国法同样将消费者的交易目的纳入关注的重点。消费者购买商品以满足其通常的私人消费需求,而非经营者通过交易以满足其经营业务的需求。此外,拍卖和公开招标也被严格地排除在消费者活动之外。
作为英国“传统”的消费者概念,《英国不公平合同条款法》与《英国货物买卖法》并没有从根本上将消费者限制为自然人。除此之外,“传统”的英国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合同中的举证责任,在欧盟法和德国法中均未有如此细节化的规定。
(二)“欧化”的英国消费者概念
“欧化”的消费者概念则几乎逐字逐句地来源于每个欧盟指令。譬如,英国为了将欧共体1993年颁布的《关于消费者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的指令》2转化为国内法,于1994年颁布了《英国消费者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规章》,其中对消费者概念作了这样的说明:“消费者意指,以营利、业务或职业为目的之外活动的任何自然人”。
此外,《英国远程销售消费者保护规章》中包含了相同的消费者概念,虽然在第3条第1项中,仅列举了“业务”,但在之前对“业务”的定义中,已清楚地做了解释:“业务即包括营利或职业”。《英国远程销售消费者保护规章》中对消费者概念的定义,同样严格遵循欧盟《关于远程合同中消费者保护的指令》中的规定,与《英国消费者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规章》中的消费者概念并无二致。《英国电子商务指令》中的第2条第1项对消费者做了几乎相同的定义。《1987年英国消费者保护(非营业场所订立合同取消)规章》中,对消费者概念被定义为:“被认作在以业务为目的之外活动的,除法人以外的人”。与其他规章相比,这里对消费者概念的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它同样指明了“业务”,并在先前就对“业务”作了相同的定义:即包括“营利或职业”。因此,消费者的概念范围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
通过由欧盟指令转化为英国国内法,即所谓“欧化”的消费者概念,将英国“传统”的消费者概念限定为自然人。与英国“传统”的消费者概念一样,“欧化”的消费者概念同样将业务性的行为目的排除在外(“outside his business”)。然而,在“欧化”的消费者概念中,并没有对有关“表见经营者”、举证责任的划分做出规定。
(三)英国法中的“两用”问题
在英国法的判例中,所购商品用于私人和业务的“两用”交易,常常成为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论往往集中于关于“在业务过程中(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这一特征上。根据以往一些判例来看,如London Borough of Havering诉 Stevenson案 ,如果有关交易即便不是买方的主要业务,但只要是“构成该业务不可或缺的部分(integral part of the business)”,该交易就应被视作“在业务过程中”的行为,即当事人符合经营者的特性,因此不能归属于消费者概念的范畴。该案的争议在于:被告经营的是汽车租赁业务,而变卖其业务用车是否应被视为“在商业或业务过程中(in the course of a trade or business)”所从事的行为?该案的Lord Parker首席法官认为,租车业务中的部分日常业务便是购置和调配车辆;在此事实基础上,出售车辆和对车辆信息的描述乃是构成租车业务“不可或缺的部分(integral part of the business)”。
为判断交易行为是否“在业务过程中”,英国法引入了“偶然性(incidental)”的概念,即通过交易的规律或偶然性的程度,来判断该交易是否属于“在业务过程中”。譬如,变卖旧的工厂设备,通常情况下不应将这种“偶然性的(sporadic)”交易视作“在业务过程中”订立的合约。同样,公司“在业务过程中”订立的购车合约,应基于其业务性质的需要,譬如一家经营着杂货店的公司购买了一辆货运车;商业银行为其高级行政人员购买轿车;地质勘探公司为其业务经理购买越野车等。在R&B Customs Brokers公司诉 United Dominions Trust公司一案中,上诉法院法官Dillon认为,“在认为一项交易作为构成业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前,该项交易必须要体现其规律性。如果该交易不是规律性的,企业购买商品也可以像自然人一样受到消费者法律的保护。”
然而与以往判例不同,在之后Stevenson诉Rogers一案中,英国上诉法院则采用了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解释“在业务活动过程中”这一术语。在本案的波特大法官(Potter LJ)看来,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14条第2款应按其字面做扩大解释。由于该案扩大了对“在业务活动中”这一概念的解释,以至于在主业之外的交易是否属于“在业务活动中”这样的问题,没有明晰的答案。同样,在使用“欧化的”消费者概念中,“两用”交易的问题无依可循。即便如此,通过上述判例我们仍旧可以看出现今英国法庭对此类案件的判决趋势,即消费者保护往往被优先考虑。
通过对英国法中消费者概念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法不依赖于欧盟指令中的规定,在《英国不公平合同条款法》与《英国货物买卖法》中已发展出独立自主的消费者概念。英国法自有的消费者概念与由欧盟指令转化为英国国内法而来的消费者概念,即“传统”与“欧化”的消费者概念一起组成了现今英国的消费者概念,因此至今英国法中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消费者概念。
三、德国法中的消费者概念
在德国消费者保护法的开端,德国法中却仍没有出现关于消费者的概念。因此,1894年的《德国分期付款买卖法》中通过将“商业登记簿上的登记的商人”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从而界定实际需要保护的消费者。
同英国一样,德国立法者为了将欧盟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指令转化为国内法,制定了众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因此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这种高度复杂的消费者保护体系造成了各法律规范之间在价值和逻辑方面的冲突,以及法律适用方面的不便32。为了使这些规范构成逻辑和价值融通的一体,便于法律适用,自2000年德国债法改革始,在德国民法典中消费者的概念被统一地定义为:“既非以其营利活动为目的,也非以其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而缔结法律行为的任何自然人。”正是通过德国的债法改革,让德国立法者得以将欧盟指令中对消费者概念的不同定义进行统一并转化到德国民法典中:民法典开篇第一章的总则中规定消费者一体化的概念。
与英国传统消费者概念不同,德国民法典以否定的方式界定了消费者概念。根据这样的定义,消费者首先被限制为自然人,因此法人被排除在消费者概念之外。此外,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如在创业阶段着手筹备其营利活动的创业者(Existenzgründer)或独立的自由职业者虽然仍为自然人,但原则上已不能被看作为消费者。
德国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条对消费者的定义,“对于创业者的一些法律行为,如租赁办公室、签订连锁加盟合约、购买自由执业诊所的股份,均被看作为经营行为。对于这样一种处在准备阶段,即将成为营利性的或自由职业的活动,没有理由适用消费者保护的相关规定。”
德国民法典对消费者概念的定义中,使用的是“缔结法律行为(abgeschlossene Rechtsgesch?ft)”,而非英国法中的“订立合约(contract deals)”一词,这使得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在订立合约之前便可适用。譬如,经营者在缔约前应履行的信息披露的义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消费者概念在德国民法典和欧盟指令中并无二致。
德国民法典中仅仅将“独立的职业活动”排除在外,而非在欧盟指令中涵盖了所有的职业活动。譬如,公司职员购买工作服,根据德国民法即可界定为消费者,而根据欧盟的规定则极有可能被界定为经营者。由此可以看出,与欧盟指令相比,德国民法对消费者的概念定义地更为宽泛。譬如,以民事合伙形式管理自己财产的情况时,民事合伙也被原则上视为消费者。
通过这些判例我们不难看出,与欧盟法中的消费者概念相比,德国法院更倾向于一种对消费者概念更为宽松的解释。
在德国的“两用(dual-use)”情形中,关于消费者特性的归属,时至今日仍存在激烈的争议。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或所谓的自雇人士的出现,譬如,其所购买的汽车往往既用于个人私务使用,同时也供其职业活动支配。德国部分学者认为,在此类问题中总应优先考虑消费者保护。而就近年的判例所显示的趋势来看,判断消费者的特性更多是取决于标的物私人使用和业务使用的主次地位。
对难以判定交易标的物的使用目的时,德国最高法院认为,“若自然人的行为被归属为经营者的活动,仅当该自然人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通过其行为明确地、毫无疑问地将此表示出来”,由此可见德国最高法院更倾向于作有利于消费者的推论。
四、结论
在欧洲仍未有一个统一的消费者概念,就连在欧盟指令中也没有对消费者概念作一体化的规定。时至今日,在英国存有两类消费者概念:“传统”与“欧化”的消费者概念,它们之间主要以是否涵盖法人来区分。“欧化”的消费者概念是通过欧盟指令转化为英国国内法形成的,但英国法院在对消费者概念的解释中更多地选择较为宽松的适用范围来保护消费者。德国民法典参考欧盟指令中的规定,在民法典中将消费者概念作了一体化的定义。与英国法院长期以来显现的趋势 即在争议情形下作对消费者有利的判决相比,德国法院虽未走得更远,但也经常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倾向消费者保护的一面。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070-02
一、比较法视野下的金融消费者概念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规定各有特色,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所采取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在法律层面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作了明确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国家,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1999)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个人、家庭成员因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体。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将受保护的金融消费者界定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人”。
(二)英国
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首次采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贸易、商业、职业目的之外接受金融服务的任何自然人。①
(三)日本
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规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的保护对象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只要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者,都在该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日本于2006年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该法在明确“金融消费者”定义的基础上,将家庭理财纳入生活消费中,同时,将金融商品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投资类商品,并且明确规定金融从业者要参照投资者的知识、经验、财产状况以及交易目的等因素履行说明义务,以达到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
(四)台湾
2011年6月中国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该法第3条还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总体而言,上述国家和地区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都体现了对弱势一方的保护,强调扩大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合理性
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合理性进行探析,即探讨金融消费者成为独立法律概念的价值所在。各国和地区将金融消费者作为独立的法律概念进行界定,主要是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在金融发展大背景下,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逐渐从对有形商品的消费,转向对无形商品的消费,而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这种无形商品的销售具有很强的信息化特征,加之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的多样化、复杂化特点,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在掌握信息的地位、能力、条件等方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消费者在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的弱势地位,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迫切地需要法律制度的保护。在弱者保护理念强化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不断得到更多人们的认可和关注,将弱者保护理念扩展至金融消费领域逐渐成为法律的取向所在,金融消费者——这一新的法律名词就此应运而生。另外,金融消费者成为独立法律概念,也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的需要。
三、中国“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法律界定
从中国现行立法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明确界定消费者的概念,当然也无金融消费者的明确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中国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基本法律,但却无法对“金融消费”这一类特殊的消费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中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一)中国有关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立法实践及理论争议
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在中国金融立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一词,银监会已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作为“金融消费者”。保监会也将投保者视作“保险消费者”。证监部门并未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而是认为证券投资者具有投资性,称为“投资人”较为合适,在实务界,证券行业也并不认可“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作为法学上的概念,学界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未达成一致。较为典型的观点有: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可定义为: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魏琼、赖元超,2011)。另有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享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社会成员(郭丹,200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是指:不具备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一般性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黎金荣,2012)。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争议,分歧主要有: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的范围是否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以专业知识为界限来划定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即是否把具备专业知识者排除在金融消费者范围之外。上述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涉及以下难点:一是金融消费属不属于生活消费;二是将金融领域消费者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的初衷何在。
笔者认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其初衷和主要目的便在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及地位悬殊的状态,从而保护弱者。而随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发展,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越来越突出,迫切地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况且,金融消费已成为消费者生活消费行为不可缺少的部分,成为消费者的一种重要消费活动,理应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消费行为。
(二)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
笔者赞同魏琼等人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即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其特征如下:第一,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为自然人。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在于“个人消费”,而非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
金融消费者不同于金融投资者。投资者是证券法中的重要概念,中国主流学术观点不主张将投资者归于“金融消费者”概念,因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不是为了生活消费。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金融消费者的立法来看,其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范围一般都较宽,且金融消费者一般都限定于个人或者为了个人目的。从中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金融消费者是金融领域的消费者,其消费目的也在于“个人消费”,而不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
参考文献:
[1] 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J].西部论坛,2012,(4).
[2] 魏琼,赖元超.论中国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其特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7).
[3] 钱玉文,刘永宝.消费者概念的法律解析——兼论中国《消法》第2条的修改[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2).
[4] 郭丹.金融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3)
环境刑法中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是损害这种法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环境刑法中,法益的规定性对于污染概念的成立有着直接的意义。
在反对环境犯罪的斗争中,人们首先认识的是环境破坏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以人类为中心来确定“环境”的范围而形成的“人类环境”(注:“人类环境”这个概念是1972年联合国大会人类环境会议时提出来的,指的是以人类为中心和主体的外部世界,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人工改造过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体。转引自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的概念,大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在反对环境犯罪中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的性质。在这个时期之前,主要地是由于工业化的程度比较低,人类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合理地”向大自然索取。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改变从而最终给人类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德国在1971年由各方面专家提出的刑法修改建议稿中,“环境保护”的概念也不过是局限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免受环境的危害”这样的认识上。(注:关于德国环境刑法发展的概况,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0年代以来,由于人为原因对环境的破坏,包括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而引起的环境问题,例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物种灭绝、生态平衡失调等,尤其是通过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形式对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日益受到重视。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这些污染环境的后果对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威胁,更是震撼了全世界。在这种对环境意义的新认识中,德国刑法学界开始考虑将保护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作为自己保护的社会利益。
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和主体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生态环境的概念与人类环境的概念对环境刑法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人类是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并且,只要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没有直接侵害人类自身的生命和健康,就不会有刑事责任问题。根据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犯罪将以环境是否受到对其不利的侵害为标准,并且,刑事责任的产生不需要以对人类的损害为必要条件。(注:有关的分析,参见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危害环境罪的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在根据“人类环境”的识识而确立的环境犯罪概念里,自然环境在实质上并没有成为刑法所要保护的一个自在的和独立的对象。在这种条件下,自然环境受到刑法的保护,其实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到损害为条件和限度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或者该种侵害是在人类社会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因此,在以“人类环境”作为法益的环境刑法中,污染必须达到给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地步,才能在刑法上被承认,也就是说,才能作为犯罪处理。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4)
原真性是世界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由于被运用于多个语境和层面,原真性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概念”(Golomb 1995)。的确,原真性概念在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都在相互传播与使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不断为原真性提出新问题,再加上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使得原真性概念理解越发困难。
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原真性概念在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两个甚至多个学科领域之间交替出现,关注视角的不同导致对原真性概念理解差异使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本已经矛盾重重的管理部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理清原真性概念在两个领域间的不同演变路径及其理解差异十分必要。本研究拟从authenticity的中英文词义人手,分析该词两种不同学科语境的词义与概念演变并进行分析比较。
一、“Authenticity”的起源及其中文译法
一般认为,“Authenticity”来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在宗教占统治力量的中世纪,“Authenticity”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程度(阮仪三、林林,2003)。“authenticity”的英文词义表示“真正”(trile)、“真实”(real)、“原作”(original)、“诚实”(honest)、“神圣”(sacred)(Lowenthal,1994)。
“Authenticity”引入文化遗产领域始于《威尼斯》(1964),在汉语中能与“authenticity”相对应的术语是用于鉴定文物的“真品”一词中的“真”,但仅针对可移动文物而言。根据英文辞典中对“authenticity”的“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以及《奈良文献》中的相关理解,曹娟(2005)、徐嵩龄(2005:105)认为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更能准确反映英文原词的含义。但此前,张松(2001)、阮仪三、林林(2003)在讨论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时就已经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同是文物背景的学者也有将其译为“真实性”(张成渝、谢凝高,2003;张成渝,2004),国家部分机关的相关正式文件也译为“真实性”。
“Authenticity”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源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inauthenticity)的认识。美国历史学家Boorstin(1964)将托马斯库克组织的大众团队旅游称为“伪事件”(pseudo-event),是一种“失真”(inauthenticity)。与之相反,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1976、1989)则认为旅游者生活在现代化、异化(Mienated)的社会中,真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旅游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找“authenticity”。社会学研究者王宁(1999)在将MacCannell的“Authenticity”概念介绍到中文语境中时,将其译为“本真”。但在哲学研究领域,早在1991年就有人将“authenticity”译为“本真性”(杜维明,1991:49)。
其实,“真实性”一词早在中文语境中存在,只不过是多用于传播学、哲学、语言学等领域。从可查文献来看,“真实性”早期含义主要是针对“真”与“实”,“假”与“虚”而言,如纳扎罗夫(1953)关于电影纪录片真实与否的讨论,杜岫石(1959)、金岳霖(1959)关于真实与正确的哲学讨论等等。或许缘于语言习惯,后来旅游界常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吴忠才,2002;于岚,2003;吴晓隽,2004;钟国庆,2005;田美蓉、保继刚,2005;陈勇,2005;王晓跷等,2006)。
综上,“Authenticity”的中文译法各有背景,但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原真性”与“本真性”的词义基本相似,“原”指“原生的”,“本”指“本来的”,只不过目前社会学界、民族学界通常译为“本真性”(最近也有译为“原真性”,如马晓京(2006),而文化遗产保护界常用“原真性”,与之相比,旅游界常用的“真实性”更强调旅游者的体验,但由于“真实”失去了“authenticity”中“原初的”、“本来的”含义,与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相背,根据英文翻译的“信”、“达”、“雅”原则,译为“原真性”应该更符合原意。
二、遗产保护法规与文献中原真性概念的演变
根据曹娟(2005)、徐嵩龄(2005)的研究,原真性概念大致经过以下几部国际法规文献的发展与完善:
《威尼斯》。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了“第2届国际历史古迹的建筑师与技师大会”,通过了《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简称《威尼斯》),《》首次明确提出“使它们(历史古迹)能以充分完备的原真性传承下去”,《威尼斯》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最早的状态”(theunderlying state)而且要保护“所有时期的正当贡献”(the valid contributions of all periods),“不能改变布局和装饰”,“要保护古迹周围环境”,等等,充分表达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概念内涵,即“最初的状态”与“当时的环境”。
《奈良文献》。1994年11月,日本文部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罗马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组织召开“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的原真性”国际专家会议并形成《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简称《奈良文献》)。《奈良文献》第13款指出,“想要多方位地评价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其先决条件是认识和理解遗产产生之初及其随后形成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意义和信息来源。原真性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质、利用与作用、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有关‘原真性’详实信息的获得和利用,需要充分地了解一项具体文化遗产独特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层面的价值。”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保持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包含着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成了某项遗产”。
《巴拉》。在国际遗产界对原真性概念一系列探讨中,澳大利亚的《巴拉》(The Burra Charter)是一部对原真性概念也有重要影响的法规,它针对原真性原则提出遗产保护方式可以包括维护、保存、恢复、重建、兼容性利用、利用、适应性改变、展示等多种方式,接纳了“重建”等符合亚洲文化遗产特征的遗产原真性保护方式。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1999,2002,2005)将遗产价值认证直接与遗产的原真性联系起来,并明确指出遗产申报必须经受“原真性检验”(testof authenticity):“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property)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原真性标准”;每项被确认的项目都应“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原真性的检验”。自此以后原真性概念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概念,受到世界各国遗产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明确提出,文物古迹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现存实物必须是历史上遗留的原状,并规定原状是指实施保护工程以前的状态和历史上经过修缮、改建、重建后留存的有价值的状态,以及能够体现重要历史因素的残毁状态;局部坍塌、掩埋、变形、错置、支撑,但仍保留原构件和原有结构形制,经过修整后恢复的状态;文物古迹价值中所包涵的原有环境状态。并提出了具体的鉴别、修复、保护工程的技术要素。所有这些理念都充分考虑了中国特色的古迹与文物保护要求。
当然,迄今各国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仍有差异,关于它的发展与完善仍在不断的进行中。总的看来,近几十年国际遗产保护的法规与文献中关于遗产价值识别或遗产保护观念的变化基本上反映了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过程:从纯不可移动物质遗产到可移动物质遗产,从物质遗产本身到物质遗产的非物质元素,从遗产价值标准的欧洲化到遗产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从遗产保存到遗产保护与利用多种方式并存,并开始关注遗产与人的关系,关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见表1)。
三、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演变
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来源于哲学领域的人类存在主义研究,但借用自早期博物馆研究(Trilling,1972),随着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将原真性概念延伸到旅游研究领域,它很快变成一个热门话题。但随着原真性概念的广泛运用,其内涵的不明确性与使用局限性日益暴露。批评家质疑它的可用性与正确性,支持者用它来解释旅游现象,成为旅游研究领域批评、改进与再批评的热点问题。Wang(1999)将原真性概念分为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几个类型:
客观主义的原真性(objeetive authenticity)。对原真性的客观主义方法研究以Boorstin(1964)和MacCannell(1973,1976)为代表,二人把原真性当作旅游客体内固有的一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在看待旅游者追求这种原真性的能力和动机方面,两人的观点截然相反。Boorstin(1964)认为游客既没有获得原真性的能力,也没有追求原真性的愿望,而MacCannell(1973)则认为游客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虚伪,他们出游目的就是追求原真性。在客观主义的原真性概念中,不管是Boorstin所批评的“伪事件”(pseudo-event)还是MacCannell所提出的“舞台化的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其衡量标准都是基于博物馆情境下的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判断。他们的这一主张招致了多种质疑和批评,其主要批评在于原真性在现实中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专家、学者所判断的不真实或“舞台化”对旅游者而言则有可能是真实的(Wang,1999)。
建构主义的原真性(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Wang(1999)将建构主义的原真性概念概括为:(1)绝对客观的、静态的起源或“原物/原作品”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一种“原物/原作品”意义上的绝对真实(E.Bruner 1994);(2)真实或不真实是一种人们看待、解释事物的主观结果;因此对于真实的体验是多元(pluralistic)的而非单一的;(3)对于旅游目的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来说,原真性是旅游客源输出地的游客基于其期望甚至刻板印象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所贴上的一种标签。在效果上,旅游者确实在寻找原真性,但他们寻找的不是客观的原真性,而是社会建构的原真性。旅游目的或其他事物作为原真性被体验不是因为他们是原物或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标志或原真性的象征被认识到(Culler,1981);(4)曾经是不真实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了一个“突现的真实”过程后会被重新定义为真实(Cohen,1988)。由此可见,建构主义者寻求的原真性不再是Boorstin和MacCannell所指的客观的原真性,而是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的原真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Wang,1999)。
后现代主义的原真性(Postmodernism Authenticity)。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在对旅游客体和旅游主体的认识上,代表着一种比建构主义原真性更激进的观点,他们完全不把“不真实”(Inauthenticity)当一回事(Wang,1999)。他们的核心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1)“真”、“假”其实没有严格边界,“真真假假”其实经常相互替代。Eco(1986)用美国迪斯尼乐园的例子来说明真假的界限,他完全解构了原制品与复制品、符号与现实等之间的界限,抹杀了“真”与“伪”的界限,进而也解构了原真性的概念。(2)现代技术可以使“假”变得比“真”还真,“假作真时假亦真”。Baudrillard(1983)用柏拉图的“虚像”(simulacra)来解释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虚像的发展经历了“伪造(counterfeit)一复制(copy)一仿真(simulation)”的过程,而现在的世界正是一个“仿真”构成的世界,它允许没有“原作品”,没有“起源”,仿真(simulation)和虚像(simulacrum)变得如此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已达到了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的境界。“表演的原真性”可以替代原物,因而也可以起到保护脆弱的旅游文化(Cohen,1995)。
存在主义的原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并非源于旅游研究领域,它主要与人类存在的意义、幸福的意义、人对自己的意义等话题有关(Carol J,Steiner and Yvette Reisinger,2006)。其早期含义是“人在某一时期对自己的真实”(Berger,1973)。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王宁 (1999)将游客的原真性体验分为个体内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与个体之间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两个维度,并认为既使旅游客体是假的,但游客会在旅游活动的激发下放松自己找到个体内部的原真或者个体之间的原真体验。当处于存在的原真状态时,人们感觉自己比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更加真实、自由,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发现旅游客体是原真的,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能够参加非同寻常的活动。
此外,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在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同时,持批评观点的学者仍然认为这种原真性在强调旅游者追求原真自我的同时忽视了东道主社会(李旭东、张金岭,2005)。美国学者Wang Yu(2007)也指出客体的原真性与存在的原真性(与自我相关的原真性)之间并非毫无联系;而且,通过某种机制这两种类型的原真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她认为原真性有三个层次――客体、自我(主体)和家。她认为除了客体层面的原真性和自我(存在)的原真性之外,与家相联系的原真性(home-related authenticity)亦是理解旅游者追求原真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游客旅游是为了逃离熟悉的环境,却又不断“在他乡寻找故乡”,在“陌生中寻找熟悉”,Wang Yu将这种原真性理解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其核心思想包括:(1)事先对“他者”的想象――这种原真性主要是与客体相关的,而且受大众传媒、旅游文献、旅游指南等影响;(2)旅游者本能地寻找“家的感觉”,在陌生中寻找熟悉,在他乡中寻找故乡。(3)东道主根据旅游者的需要创造和提供符合旅游者需要的原真性的旅游产品。Wang Yu提出的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的概念事实上是一种客体(东道主社会)和主体(旅游者)共同建构的原真性。这个概念强调了客体和主体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它解释了建构的、舞台化的遗产文化何以被旅游者所接受。wang Yu超越了对“原真性”概念的二元理解。但与此同时,定制化的原真性的问题在于当这种二元对立消除后,东道主社会是否可以提供每个个体旅游者认同的原真性遗产文化以及如何提供。这种定制化的原真性必然是多元的,而最终的结果可能就如wang Yu自己丽江案例研究所说:在旅游地“旅游者可能随处发现也可能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本真的纳西文化’”。
总的看来,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虽然最初源于博物馆研究领域、哲学研究领域,但在旅游研究中却是从关注旅游者动机与旅游者体验开始,这也就奠定了其概念后面的演变过程,即基本上是站在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真”与“假”,尽管客观主义原真性更强调客体本身的“真”与“假”,但这种“真”与“假”也只旅游者辨别能力范围内的真假,建构主原真性则开始认为旅游者所关注的客体“真”“假”是被社会建出来的,其本质仍是从旅游者角度来判断的“真”与“假”,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原真性概念,可以不作考虑。存在主义原真性完全从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自身开始分析“真”与“假”的感受,实际上是将原真性概念的视从主体对客体的关注与判断转向了主体对自身的关注。“现实存在主义”的原真性提出的“定制性原真性概念”又重新将原真性理解拉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但却不是将客体放在一个被动的“判断”与“鉴定”“真假”的位置,而是认为客体是根据主体的需要而主动建构的一种“真”的场景(见表2)。
当然,西方旅游研究中对于“原真性”概念争论只是一种理解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的一种视角,原真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本身就说明了“原真性”并不是一个“静止、客观、固定的标准”或“某种产品或吸引物的固有属性”,它往往是主观的、建构的以及不断发展和被创造的,对原真性概念的分析将有助于研究旅游地管理、文化商品等多个热点问题。
四、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路径与理解差异比较
首先,从学科背景看来,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是以考古学、博物馆学为基础,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是以社会学为基础,学科背景不同,其最初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研究更多地关注遗产保护的标准与实施技术细则,而旅游社会学者则关注旅游社会现象的解释。
其次,从研究与争论焦点来看,遗产保护界因国际文化差异及遗产特性的不同对原真性标准理解不同而产生争议,争论原真性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个公认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而旅游研究领域则从解释旅游社会现象,增强旅游者体验、管理旅游地的角度来讨论原真性的概念,但由于旅游产品类型不同、旅游场景不同等旅游形式多样化的特征而形成对旅游体验的多角度解释,其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旅游现象。
第三,从发展过程来看,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经历了从强调物质遗产的本身到强调物质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元素,从强调物质遗产的现状到强调物质遗产的时空演变过程,从物质之间的关系到强调物质与人关系的过程。与之相对应,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从分析旅游主体对客体的“真假”辨别到讨论旅游客体“真”与“假”的构建模式,再到完全从旅游主体的“真”、“假”体验态度,然后发展到旅游客体与主动的互动构建模式。二者都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但其演进动力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界的演变动力是世界各国遗产保护界的实践,推动世界公认的、适用于多种类型的遗产保护的标准,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演变动力却在于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的旅游现象,对旅游活动与旅游地管理提出改进意见。
第四,从发展趋势来看,遗产保护界将原真性概念不断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扩展到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并且这一概念在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不断地推进世界各国的各类遗产保护与保存。旅游研究领域也将原真性概念从主体关注不断向客体及主客体互动关注不断推进,使原真性概念的内涵边界不断放大(见表3),值得一提的是,原真性概念在在旅游研究领域出现之初就没有局限在文化遗产范围,而是以旅游者体验为中心延伸到任何其他旅游客体对象进行讨论,并且已经在业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如近年来旅游业界以“真山真水”为宣传口号的旅游“寻真”运动日益盛行,这一现象说明旅游经营者与旅游需求者都已经开始关注旅游活动中“真”与“假”的问题。
五、原真性概念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的理解逻辑框架
如前所述,遗产界关注物质但日益向非物质元素聚焦,旅游界关注现象但日益转向互动分析。鉴于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基于两者互动之间的研究,原真性概念有必要充分吸引各自的优点,在研究中予以全面考虑(见图1):
关于客体原真性理解。根据遗产保护界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在徐嵩龄(2005)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将原真性的理解要素分解为遗产的地点、位置,形态、法式,形式(指非物质艺术的表现形式)、器物,材料、材质,环境,技艺,功能,精神、情感,原住民社区(生活方式、艺术传人),相关事件、人物与地方,时序变化等12个方面。在旅游研究中,于客体本身的“真”与“假”辨别的复杂性,以及旅游主体“真”与“假”的辨别能力限制,因而也只能从游客体验的角度来分析客体“真”与“假”对旅游体验的效果,为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提供依据。
关于旅游主体的原真性理解。遗产保护界基本上只关注客体本身,认为遗产本身一定是可以用一个绝对标准对真与假进行衡量,但旅游研究中却将旅游主体即游客自身是否有“真”与“假”的体验作为关注的焦点。不过从长远来看,游客对客体原真性认知能力的提高也受客体原真性标准的普及程度有关,因此遗产旅游研究中主体的原真性体验与满意度的关系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应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主体的原真性体验。
关于旅游介体对原真性的影响。由于时间、空间以及旅游者知识能力等原因,旅游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不是直接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旅游介体的影响,这些介体包括宣传媒介、旅游服务机构等,他们对旅游客体的宣传、介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认识。因而媒介对客体的构建方式与传播途径,以及媒介对主体即旅游者对客体的认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都是旅游原真性概念需要分析讨论的问题。因此遗产保护界在研究客体的固有标准时也要注意对这些标准信息的传播与普及,保证遗产原真性在媒介中建构的准确性。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5)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法学界已有很多关于法益的讨论。现将既有讨论的几个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在法益的涵义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将法益界定为权利之外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或类似表述。[1]个别异见认为,任何权利均可称权益、法益,但权利外无权益、法益;主张权利以外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违反法理。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权利、法益、一般利益三者并列讨论,认为法益是介于权利与一般利益之间的一个概念。[2]有一些学者还区分了广义法益与狭义法益,狭义法益仅于权利之外存在,广义法益则将权利也包括在内。[3]总之,既有研究基本上系将法益定位于权利之外的一个法律保护对象。
第二,在法益的词源问题上,许多学者谈到,该概念系来自于德国。[4]其中有的学者直接指明了原词,“‘法益’(Rechtsgut)一词,由德国学者首创,日本学者从德文首译。” “法益一词是由德文das Rechtsgut翻译而来。”
第三,在法益概念的功能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界定一个独立的法益概念,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其提供民法上或更具体地说是侵权法上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与权利相比,是一种弱保护。[5]
在既有民法“法益”研究的资料来源上,最常被引用的有以下两部分资料:其一,刑法学者关于法益的著述,主要为张明楷教授的专著《法益初论》[6]和台北大学高志明2003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刑法法益概念学说史初探”;其二,民国时期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关于“法益”的一些论述。常被引用的有史尚宽[7]、曾世雄[8]、芮沐[9]、洪逊欣[10]等。
从资料来源角度看,我国目前的民法法益研究至少有以下两个不足。其一,刑法法益理论或可用于参照,但若直接拿来做民法法益研究的根基,恐怕不妥当。比如,刑法基于其公法性,不可能仅将其保护对象指向单个个人,必然会产生诸如“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或“个人法益”、“超个人法益”这样的分类,这就会与以单个私人为思考原点的民法产生不可弥合的间离。其二,台湾学者对法益的论述,多系只言片语,仅系在体系阐述时顺便提及法益,而未及深入。且我们也存在脱离体系背景的误解。[11]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虽然我们一方面指出了“法益”概念源于德国,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几乎没有利用德国民法学中关于“法益”研究的资料;以致我们对“法益”概念在其原生的德国民法体系中的涵义、功能、理论争议、实践发展所知甚微。
这里隐藏着一个方法论问题。当我们从域外引入一个概念,并试图为我所用时,这种比较法上的借鉴何以可能?又何以有效?其前提恐怕是应当首先厘清下述问题:该概念在其发生地是何涵义?它原本被设计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又有何发展?它在实践与判例中的应用如何?理论上又有何争论与流变?有了这一系列清晰的认识,我们才有条件进一步思考:我国是否有同样的问题?该概念又是否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概念是否及怎样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从而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发生体系矛盾?如果未进行以上思考,仅仅是说“这个概念来自某国”,然后就依翻译之后的字面涵义来解释之,并以其为手段来解决自己设想的问题,建构自己设想的体系,这就难称之为一种法律借鉴,也难称为一种比较法研究。此时,说不说“该概念来自某国”都是一样的,对论证与结论均无影响。说了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陈述时的辅陈或导入,或一种“此事古已有之”的隐喻,从而减少他人对概念本身的质疑;但概念的内涵、外延、功能及一切,其实都是自己赋予的。这样的研究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研究结果会格外“多彩”,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其实是在各自发挥想象力。[12]
本文的学术企图,首先不在于在法理学层面上对法益进行一般的探讨,因为这样的探讨至少要弥合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之间的鸿沟,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结论会过于一般,从而缺乏实践意义。其次也不在于在整体民法层面、如权利理论上对法益进行探讨。从前引法益的既有讨论中可以看出,即使是民法层面的法益研究,实际上也是将侵权法作为一个主要的假想适用领域,从法益保护相对于权利而言是一种弱保护即可看出这一点。很显然,合同法上的保护是不区分权利与利益的;由于合意过程可以维持当事人的预期,合同的相对性可以限制请求权人范围,所以纯粹经济损失在合同法上是无疑问地可以得到赔偿的。换言之,利益在合同法上获得的根本不是弱保护。只有在侵权法领域,由于利益保护往往比权利保护需要更强的要件,如存在保护性法规、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这时才谈得到一种对利益的弱保护。事实上,但凡得出较之权利,“法益”只能获得弱保护的结论时,研究者就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到侵权法领域了。总之,最能发挥“法益”研究之意义的民法领域,乃是侵权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学术企图,在于结合“法益”概念的原产地——德国法,以及区分“法益”概念最有意义的民法领域——侵权法这两个要素,探讨德国侵权法上“法益”概念的发生与发展、法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理论上的纷争及实践应用,当我们真正廓清“法益”在德国侵权法中扮演过和扮演着什么角色后,再来考虑该概念对我们有什么可能的意义。
二、法益是什么——当代德国学者的观点
综合德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法益指且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
拉伦茨、卡纳里斯谈到前述保护对象时认为,虽然它们象所有权一样也具有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但它们却并非支配权,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与主体相对的、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可供归属于主体——如同物可归属于所有权人;因此,它们通常不被称为权利,而是被称为法益。”[13]多伊奇、阿伦兹认为:“我们将那些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存利益称为法益,它们尽管具有绝对性,也即可以对抗一切他人而受保护,但并未成为一项绝对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原则上不得转让。”[14]梅迪库斯、劳伦茨认为:“生命、身体、健康与自由不能作为主观权利来理解。只有当人们能够将主体(权利主体)与客体(权利客体)区分开来时,人们才能说这是一项权利:在第823条第1款随后规定的所有权中,所有权人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即其适例。但生命、身体等却并非如此:它们是与人无法分离的人的特性。”[15]有的学者则不加解释,直接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列举的保护对象分为两类进行讨论,或分别称之为“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权利”(所有权、其他权利),[16]或分别称之为“法益”和“绝对权”。[17]
第二,法益指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所有受保护的对象。
也即,这种观点认为,法益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和其他权利”。
费肯杰、海内曼称:“第823条第1款列举如下绝对受保护的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和其他权利”。[18]《艾尔曼民法典评论》将第823条第1款项下所有保护对象统称为“法益”,并称该款为一个“法益导向”的条款。[19]有的著述对第823条第1款下的诸保护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再讨论,而是直接在“法益”或“法益侵害”标题下将所有客体列出。如《帕兰特民法典评论》在“受特殊保护的法益之侵害”项下列举了所有六项保护对象。[20]福克斯则将“法益侵害”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请求权的一个构成要件,并将六项保护对象都包括在内。[21]
综上,暂且作以下两点分析:
其一,可以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不是指权利以外的利益。恰恰相反,“法益”是权利(我们所谓的)之内的一个概念。如果采第一种观点,“法益”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种传统的具体人格权,而在此之外的其他人格权(如名誉权)不包括在内,一切财产权和身份权更不包括在内。这是一个比我们所说的权利要小得多的概念。如果采第二种观点,“法益”的范围较为宽广。由于此时它包括了“其他权利”,而“其他权利”中现在包括了限制物权、知识产权、专属性亲属权等,因此可以认为这时的“法益”有了较广泛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内容。但它仍然不能等同于权利,因为债权是不包括在“法益”范围内的。[22]因此,第二种观点下的“法益”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绝对权”概念,或者称之为“侵权法上的权利”。但无论怎样,德国民法上的“法益”,只能在权利范围之内且比权利小。前文所引我国目前研究中的,所谓狭义上的、在权利之外存在的法益,或广义上的、包括一切权利利益在内的法益,都不是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概念。
其二,德国民法上的“法益”究竟是指什么?是权利(或绝对权),还是“生存利益”(Lebensgüter)?是仅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内容,还是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六项内容?这一点还须继续考证。在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争议?这仅仅是一个无谓的概念之争,还是蕴含了深刻的历史、立法、理论和实践背景?
前引德国学者所提到一个将狭义“法益”区分出来的形式理由,即这些“生存利益”与主体无法分离,也无法转让。这一点固然无法否认,但我们也能想到,毕竟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是一个侵权法的基本规定,该条所做的区分应当有侵权法上的意义才对。而“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在受侵害时的保护问题上,与所有权等实无区别。不能转让及难以价值化,仅导致这些“生存利益”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而在归责上,“生存利益”与所有权是毫无区别的。可见,所谓“生存利益”与主体无法分离、无法转让的理由,是极其形式化的,这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玄机,否则何劳拉伦茨、卡纳里斯、梅迪库斯、多伊奇、艾瑟这些大家去做这种无甚意义的区分?
三、法益概念的初始涵义、功能与实践
众所周知,德国侵权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是法国侵权法的一个反动。基于避免侵权责任泛滥,并适当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思想,德国侵权法对侵权赔偿请求权进行了限制。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并不明确保护对象,而德国侵权法限制侵权赔偿可能性的手段之一,就是从利益的广大范围中,挑选出若干典型、成熟的领域给予保护。而且,“这些领域由不同层级组成,即从一般利益到特殊法益再到绝对权利,逐次攀升。”[23]这里我们看到了法益与绝对权利的区分,这一区分也正是民法典立法者的态度。“帝国议会民法典咨询委员会主席恩内克鲁斯(Enneccerus)留给我们如下观念,那四种不属于主观权利的生存利益,应当与主观权利区别对待。”[24]
保护对象的区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对象的分级。“从一般利益到特殊法益再到绝对权利,逐次攀升。”这说明,在德国民法典立法时,绝对权利是高于法益的。法益与权利究竟有何不同?多伊奇认为:“权利与法益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可以从以下三个标准来考虑:客体、可转让性、数量是否固定或者说是否能够开放地补充。”[25]法益系与人身密不可分的人格利益,所有权与其他权利仅涉及可与人身分离的财产利益,故前两项区别——客体与可转让性容易理解,要害在于第三项区别。“生存利益已被完全列举;判决不可再创造新的第823条第1款上的法益。”[26]“财产利益理论上可以开放地补充,无论在责任法自身领域,还是通过其它法律领域的新发展,财产利益的开放补充恐怕都是可能的。与之相反,人身利益的数量却并非无穷。”[27]第823条第1款上的法益的数量和内容,已被德国民法典立法者固定下来,并且不允许司法实践再进行创造性的发展;这就是当时立法者的态度。而在这四项法益之外的其他人身利益怎么办?回答是可以通过保护性法规结合第823条第2款进行保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名誉。第823条的前身之——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条第1款中,被列举的保护对象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所有权或其他权利”。[28]而“名誉”这个保护对象后来被删除了,原因就在于刑法典上关于侮辱、诽谤罪的规定(《德国刑法典》第185条以下)可以视为保护性法规,结合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之法规”侵权类型,即可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若一个对名誉的损害行为未构成侮辱、诽谤罪的,立法者则认为民法典没有必要提供超出刑法典的保护程度。[29]
可见,德国民法典立法时,人们的普通认识是财产利益的重要性大于人格利益。因此,与所有权类似的绝对权被认为可以经司法继续扩张,而代表人格利益的法益则被认为已为立法完全固化了。这就是所谓保护对象分层级的一个表现。
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绝对权是有弹性、可发展的,然而在技术上、或者说在形式上依靠什么来保障其发展的可能性呢?这就是立法者创设“其他权利”这个开放性概念的用心。“其他权利”即意味着,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性质上与所有权类似的新型财产利益,司法可以将其纳入到“其他权利”中,从而使其获得过错责任的保护。
接下来便到了问题的核心。法益与权利(绝对权)都受过错责任的保护,保护要件和法律效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必须存在于同一个条款,任何一个都不能被打入第823条第2款或第826条的“另册”。但是,当我们在同一条款中列举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这六项保护对象时,我们会发现,如果不加任何限定,“其他权利”的扩张功能是能够作用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之上的!如果这四项法益与所有权没有区别,则“其他权利”能够吸纳与所有权类似的其他财产利益,也就同样能够吸纳与四项法益类似的其他人格利益,而这一点,恰恰是立法者所不愿看到和力图避免的。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与“所有权、其他权利”是有区别的,是两个不同范畴。“其他权利”只能在本范畴内发挥弹性,但它不能跨越界线,到另一个不同领域中去发挥扩张功能。这两个范畴分别是什么?“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叫做“法益”,“所有权、其他权利”叫做“权利”(或主观权利、绝对权利)。正如前引诸多学者反复强调的,法益不是主观权利。至于为什么不是主观权利?理由大家可以另行总结或创造(如可转让性的不同、主体不能以其自身为客体等),但结论是已定的。
多伊奇对这个故事有一个精辟的总括:“立法者明确命名了法益,因为立法者不想把法益归入主观私权利。一方面的考虑是要把生存利益完全列举,且不得再补充;另一方面是考虑须对一切类似于所有权的绝对主观权利提供全面保护。”[30]
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的判决,忠实地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图。1903年出版的《帝国法院判例集第51卷》中,记录了一个原告起诉要求保护名誉和职业自由的判决。该判决所列的第一个争点,就是“名誉和职业自由是否属于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若以现在的眼光看,至少名誉已经属于“一般人格权”,而“一般人格权”又属于“其他权利”之一种,因此可以获得第823条第1款过错责任之保护。但上世纪初的法官并不这么看。“本案中适用第823条第1款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二审法院意图知晓,能否将名誉、甚至一切人身和绝对权利,都归入无论故意过失致损均能引发赔偿责任的‘其他权利’范围内。有人亦认为,主体对其劳动力及个人能力的自由且不受干扰的利用,无疑也属于‘其他权利’。但是,‘其他权利’这个概念不能如此宽泛地扩张解释。只要还不能从第823条第1款中推断出其他涵义,‘其他权利’就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理解为主观权利。……第823条第1款首先明确列举了如下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无论从现法典中,还是从第823条第1款的发生史中,都无法支持以下观点:即,这些法益已被承认为真正的权利,它们只是权利的一些具体例子……”[31]可以理解,前已述及,民法典第一草案与法典正式文本在第823条第1款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民法典把“名誉”排除于过错责任保护之外。如果司法判决于法典生效仅3年后,就把名誉归入“其他权利”,从而将其纳入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范围,这显然是直接违反了立法者原意。综上,本案中,名誉与对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支配显然不属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法益,同时也不属于与所有权类似的财产权利,故也不能归入“其他权利”。因此,法院的结论是,本案中的名誉与职业自由不受第823条第1款之保护。
四、法益涵义、功能与实践的发展
(一)二战之后的发展
二战之后,德国侵权法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来自于基本法。德国基本法的修改,把人的尊严与人格价值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实践中对人格利益高涨的保护需求,和基本法上人格尊严对部门法的价值渗透的双重作用下,德国侵权法中的人格利益保护有了巨大的发展。于是,以限制人格利益保护为己任的“法益”概念,无可避免地落伍了。它若还要存在,便不能再坚持以往的涵义和功能。
与侵权法上人格保护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以及第2条第2款:“人人均有生命与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个人自由不可侵犯。以上权利只能根据法律进行限制。”
以上基本法条款对侵权法上人格法益保护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第823条第1款中的法益直接转化为主观绝对权利。“此处所述的生命与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及自由权是基本权利,也即主观公权利。根据宪法第1条第3款,基本法约束的首要对象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审判权。基本权利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进入私法发生作用,并得创设私人权利和义务(‘第三人效力’)仍有若干争议。但由于在既有案例中,第823条第1款给予生命、健康和自由的保护,已与生命、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及自由权的宪法保护相重合,因此,对生命等的主观私权利与对生命等权利的宪法保护相一致的体系构成,也就显而易见了。”[32]基本法上的生命、身体、自由权是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价值体系渗透于私法之中,使得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的生命、身体、自由不再仅为低于绝对权的法益,而是直接成为主观权利。
这一立场亦体现在判例中。《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判例集第58卷》记载了如下案例。该案中,由于被告过失导致车祸,致使原告怀有的6个月的胎儿脑部受到损害,该婴儿出生后逐渐患上瘫痪症,原告遂基于孩子的健康损害要求赔偿。与本文主旨相关的是,该判决中出现了对“第823条意义上的对胎儿健康的主观权利的损害”[33]的表述。在这里,“健康”这一“法益”已经被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直接称之为“主观权利”了。
第二,法益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被“一般人格权”所吸纳,进入了“其他权利”范畴。四项法益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如名誉、隐私等,在德国民法典上本无独立的保护依据。但在战后人的尊严与人格价值至高无上的大潮影响之下,诸多其他人格利益也有了强烈的受保护的社会需求。司法为了因应这一点,遂在基本法的价值指导下,缔造了“一般人格权”概念,并将其归为“其他权利”的一种。由此,各种人格利益的保护就不再要求“保护性法规”或“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而只需满足过错责任构成要件即可。[34]
至此,法益与权利的区分便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在基本法与判例的影响下,法益已经被视为权利。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法益与权利区分的目的,乃是要把过错责任的保护范围人为地区分为两个领域,然后使“其他权利”仅在财产领域发挥扩张功能,从而杜绝新的人格权产生。但是,当各种人格利益经“一般人格权”的通道,已经成为“其他权利”的一类时,“其他权利”非但不再是人格权扩张的防火墙,反而成了人格权扩张的推进器。当杜绝人格权扩张这一目的不存在时,为达这一目的的手段——法益与权利的区分——也就不再必要了。因此,现在德国民法学界对法益能否作为权利对待的一般态度是:“虽然在可转让性、保护强度、法律所定义的保护范围、构成要件的形式上仍能看到部分区别,但这些都不能够论证对法益的区别对待。”[35]
综之,“法益与主观权利之间的区分已经被宪法所弥合。”[36]
基于以上认识,回头再看德国学者在法益问题上的“差别观念”。事实上,德国学者并不存在两种观点。应当认为,他们对于法益概念的来龙去脉都是了然的。只是有的学者,如拉伦茨、梅迪库斯,还愿意再作一些解释,提及一些过去的故事。于是,他们先说法益是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在法史上当然是正确的;然后再给出一些诸如主体不可以其自身为客体、法益的不可转让性等形式化理由,这个也无可厚非;最后,他们一般会再指出,“然而这种区分在侵权法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在此无须继续深究。”[37]“在依据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侵权保护方面,法益与绝对权(如所有权)已无区别。”[38]这是现实的态度。
而有的学者,可能认为既然法益与绝对权的区分已经不再有意义,则根本就不必再多做解释,于是他们直接把“法益”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保护对象的统称(如费肯杰、海内曼),或把“法益侵害”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请求权的统一构成要件(如福克斯)。无现实意义之事不必多提,这种态度也无可指摘。
(二)债法改革后德国民法典中的“法益”
2002年债法改革后的德国民法典中,首次使用了“法益”概念,使该概念终于从一个法解释用语,变成了法典正式用语。在债总部分新增的第241条第2款(保护义务)及第311条第2款(缔约过失)中,立法者将“权利、法益、利益”并列规定,三者同为债之保护义务和缔约过失的保护对象。在解释上,“在前合同之债中,当事人即已负有不侵害他人的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权利(如所有权)的义务。……此外,当事人须顾及另一方的其他利益(尤其是概括财产,也包括决定的自由)。”[39]
可见,德国立法上仍沿续了民法典初创时的思想,即“法益”(四种具体人格权)、“权利”(主要是绝对性财产权)、“利益”(主要是纯粹财产利益)三者的概念区分。而且在表述排序上,仍然是权利第一、法益第二、利益第三。相较于法解释,德国立法还是显得比较保守;也不禁令人感慨历史惯性的强大。对此本文再做三点说明。
1.很显然,即使是在这种传统区分下,法益与利益仍然是截然不同的。
2.虽然在第241条第2款、第311条第2款上,权利与法益被区分为两个概念,但两者的保护程度是一样的。债法总论中如此,侵权法中更是如此。
3.当下德国民法中,债法总论立法上“权利、法益、利益”三者的区分表述,与侵权法上普遍存在的“法益”与“权利”(绝对权)混用的情况同时并存。前引诸多混用这两个概念的学者,其著述几乎都发表于2002年之后,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立法上的用词而修改自己侵权法著作中的表达。其实可以想见,侵权法中“法益”与“权利”的混用几乎可以说是必须的,因为若非如此,就无法解释为何与“法益”同质的一般人格利益能成为一项权利(一般人格权属于“其它权利”)。
为何德国债法改革仍然使用了“权利、法益、利益”并列的表述?本文认为,可能立法者意图在“债的保护义务”和“缔约过失”两项制度中,明确保护对象的全面性,于是把立法史上出现过的“权利”、“法益”、“利益”三个保护对象全部列出,以求周延,避免人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可能产生的误解。比如,如果只列“权利、利益”,可能人们会误认为,是否以上制度不保护那几种具体人格权?如果只列“法益、利益”,可能人们会误认为,是否以上制度不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等等。
但仍须指出的是,“法益”概念的出现,是以限制人格利益的保护为目的的。在人格利益扩大化、至上化的今天,是否仍有必要在仅指几项具体人格权意义上维持一个“法益”概念,不无疑问。
五、我国民法是否有必要设立“法益”概念
德国法上的“法益”,传统含义及当下债法总则中含义,是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具体人格权。而在侵权法领域中,德国学者一般将“法益”与侵权法上的权利视为同义;人们既可以说法益即是权利,也可以说受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保护的都是法益。[40]总之,德国民法上的“法益”,在权利(我们所谓的)之内,而非在权利之外。
若认为源自德国民法的“法益”(Rechtsgut)概念,系指权利以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这一定是个误解。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不背德国法史的包袱,自主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法益”概念。那么,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究竟有无必要设立一个在权利之外存在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法益”概念呢?
须注意,我们不能因为语言的模糊性,遮蔽了我们的思维。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指“应当”受法律保护,还是指“可以”受法律保护?
如果是指“应当”受法律保护,则须指出,一项利益是不是应当受法律保护,不是这个概念本身决定的,而是利益是否能够充分相关保护规范的构成要件(在权利利益区分的保护体系下,指保护性法规、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的要件;在权益不区分的保护体系下,则在满足过错责任要件之后还须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所决定的。一项利益在没有被保护规范的要件检验之前或法官未做出利益衡量决定之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项“法益”;而检验通过或法官决定保护之后,也已不需要我们再跑来宣称,该利益是一项“法益”了。换言之,所谓“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法益”,是一个对利益决定保护与否的判断结果,而不是用来判断是否保护的前提,该概念本身不可能有这项功能。从逻辑上说,权利和利益都在判断是否保护的起点上(即使是权利受侵害,也要经过过错、因果关系等要件检验),而这里所谓“法益”却在判断保护的终点上。权利和利益的涵义都是可得保护的对象;而这里“法益”的涵义却是已被保护的对象。把权利、利益与这样的“法益”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同一类事物,是有逻辑问题的。而且更根本的,一个处于司法判断终点上的概念,是不能为个案中处于判断起点上的法官提供帮助的,也即,这样的概念缺乏规范功能。
如果法益是指“可以”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个概念与“利益”是同一的。因为“利益”一样也是“可以”受法律保护、也“可以”不受法律保护。这样的“法益”概念,没有提供比“利益”更多的规范功能。
如前文引述,有学者将“权利”、“法益”、“一般利益”三个概念并列讨论,此时“法益”与“一般利益”之间的区别在于,“法益”是可以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里的“法益”其实就是“利益”,而一个确定不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概念,根本就不在民法的视野范围内,因为没有必要。这样的三个概念区分,实质上是把“利益”改名为“法益”,再从法外领域拉来一个概念凑成的。
如前文引述,既有讨论中还存在“广义法益”与“狭义法益”区分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广义法益”是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括权利在内),“狭义法益”则指权利以外的受法律保护之利益。这样包括权利在内的“广义法益”概念,其实只是一个权利与利益的统称,在侵权法上称为“保护对象”(Schutzobjekte)。这里的“狭义法益”,其实就是利益。
也有学者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区分“广义法益”和“狭义法益”,“广义法益”包括法律已经规定和应当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狭义法益”指法律已经规定予以保护的一切利益。这里的“狭义法益”相当于前述侵权法上的“保护对象”。而这里的“广义法益”,目的是为了增加一个“应当规定而未规定”的内容;其实,传统民法中的“利益”本来就是开放性的,实践中完全可能出现新型的、现行法未规定的利益,法官此时予以评价地保护(所谓“法律续造”),学说对判例进行整理,在该利益典型化、成熟化后,期待立法的解决。把将来可能出现的保护对象包含在内,本来就是“利益”概念的正常运作方式。
前文引述的诸位台湾学者关于“法益”的论述,各有其表述的具体语境。史尚宽与芮沐先生显然是在“保护他人的法规”意义上,说明此类规范间接地使个人受有利益(法益)。而“保护他人的法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2款)的功能,依通说为保护纯粹经济损失,[41]这是利益的一种典型形态。洪逊欣先生强调的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中,也存在依法律的反射作用而享有利益的情况,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表述为,依法律反射作用享有的利益就是法益。A中含有B,不能推出B=A。其实从文字上也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洪逊欣先生所说的“法益”,就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利益同义。曾世雄先生将权利、法益、自由资源三概念并称,实际上类似于前引有的大陆学者的权利、法益、一般利益的分类。这里的自由资源的特点是,“放任自生自灭者,在法律上不被承认合法,然亦不认之为违法”,其实是一种法外现象。而他所列举的法益种类,大多为典型的利益类型。综之,以上台湾学者使用的“法益”概念,是指利益或利益的一种具体形态。这些台湾学者并无在与利益对立的意义上创造出一个“法益”概念的意图。
综上所述,以德国民法中的“法益”的传统含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来定义的“法益”概念,在我国(包括台湾地区)从未出现过。[42]我国学界对民法“法益”的理论与实践演变,事实上相当陌生,既有研究其实多是在进行自我建构。而这种自我建构出来的“法益”概念,在本文看来并非必要,因为“利益”本身就包含了“可能受法律保护,也可能不受法律保护”的含义,“(可能)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就是“利益”,不是另外一个新事物。以“(可能)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来定义的一个所谓“法益”概念,并不比“利益”具有更多的内涵,当然也没有提供新的规范机能和解释机能。不产生新机能的概念替换,徒增烦扰,且增加了误解的可能与对外交流的困难,没有必要。
侵权法保护对象上,谈权利与利益就足够了。
结语
最后想要再次强调的,还是借鉴的方法问题。当我们借鉴域外概念、理论、制度之时,恐怕还是应当首先透彻了解该概念、理论、制度在其原生体系中的目的、涵义、发展与实践应用之后,再考虑本土存在哪些问题可望利用它来解决。若未经透彻了解这一基础工作,仅根据概念翻译之后的中文表面涵义进行阐发,域外法律资源其实并未得到利用,被利用的只是自己的直觉和逻辑,这不是一种借鉴,也难称妥当。
当然,本文绝非杜绝创新。相反,本文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地域和人民,当然应当有自己的法体系和法文化。只是作为一个法律后发国家,借鉴恐怕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前述观念,可望使我们在借鉴时少一点弯路,多一点成效。
注释:
[1]参见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民事法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郑春玉:“论民法法益的存在及其价值”,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曹险峰:“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白飞鹏、李红:“私法原则、规则的二元结构与法益的侵权法保护”,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张驰、韩强:“民事权利类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1年第12期。参见李锡鹤,“侵权行为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外法益概念质疑”,载《东方法学》2011年第2期。
[2]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参见孙维飞:“弹性的法学移植——以侵权行为法学中法益学说之发展为个案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也有学者以应然性和实然性为标准,区分广义与狭义法益。参见刘芝祥:“法益概念辨识”,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参见李岩:《民事法益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9-10页。孙维飞:“弹性的法学移植——以侵权行为法学中法益学说之发展为个案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张驰、韩强:“民事权利类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1年第12期。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参见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民事法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曹险峰:“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参见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6]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7页。该部分为作者运用日文资料,对德国刑法学中法益概念及理论发展史的一个详细介绍。
[7]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8]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法益者,法律上主体得享有经法律消极承认之特定生活资源。”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9]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权利与法益,二者重要区别,端在主张权之存在与否,权利被侵,主体本身即有向任何方面行使其保障意志之可能。而法律所规定不可侵犯之利益,与其谓为个人之权利,毋宁谓为一般的法益;此处个人即无从直接提出主张。”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0]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法律所保护之利益(法益),未必尽为权利之内容,即其中仍有仅依法律之反射作用而得享有之利益”。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11]举一个典型例子。前引史尚宽先生的表述,“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为既有法益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材料之一。这是史先生在论述侵权行为的“被侵害客体”中的一句话(确切地说,是半句话)。其全句为,“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在违背良俗之侵害,为个人之一切利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史先生是在论述德式或我国台湾地区式的“三个小概括条款”(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法规、违背善良风俗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侵权法结构中,三个概括条款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这里“法益”概念的使用,只是为了说明在“违反保护法规”这一类型中,受侵害的客体为法益,而不是为了概括地说明“什么是法益”,更不是在给“法益”下定义。若仅将史先生这半句话摘出作为依据,或进一步“浓缩”为“史尚宽认为,法益乃法律间接保护之个人利益”,(如前引熊谞龙文,注(19);张开泽文,注(3)甚或更进一步升华为法益定义上的“间接保护说”,(如前引关永红、陈磊甲文,注(3);原文作“简介保护说”,不通,似应为文字错误)徒增误解,未见其可。“违反保护性法规系间接侵害了法益”与“法益乃法律间接保护之个人利益”两句话之间,含义差异之大不啻天渊。
[12]以上概念借鉴和比较法研究上的方法论的类似思考,请参见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13]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S. 374(1994).
[14]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5.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 2009, Rn. 231.
[15]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Ⅱ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 Rn. 1270.
[16]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2,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2,8.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0,S. 151ff.
[17]Brox/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1, § 45, Rn. 2ff.
[18]Fikentscher/Heinemann, Schuldrecht, 10. Aufl.,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2006, Rn. 1557.
[19]Erman/Schiemann, 13. Aufl., Aschendorff Rechtsverlag, Kln 2011, § 823, Rn. 1.与第823条第1款“法益导向”(rechtsgutsorientiert)相对应的概念是同条第2款的“行为导向”(verhaltensorientiert)。
[20]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71.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2, § 823, Rn. 2.
[21]Maximilian Fuchs, Deliktsrecht, 7. Aufl., S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2009, S. 10ff.
[22]Vgl. Münchener Kommentar/Wagner, 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9, § 823, Rn. 142ff.
[23]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1976,S. 13.
[24]Erwin 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2.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1996, Rn. 57.
[25]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S. 17)1976,
[26]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S. 15)1976.
[27]Erwin Deutsch , Haftungsrecht , Carl Heymanns Verlag , Kln/Berlin/Bonn/München(S. 17)1976.
[28]Zusammenstellung der gutachtlichen Äuerungen zu dem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Band Ⅱ.,Äuerungen zum Recht der Schuldverhltnisse, Otto Zeller, Osnabrück 1967. S. 397
[29]Maximilian Fuchs, Deliktsrecht, 7. Aufl., S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2009, S. 36f.
[30]Erwin 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2.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Rn. 58(1996).
[31]RGZ 51, S. 369ff.
[32]Staudinger/Schäfer,12.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86., § 823, Rn. 9.
[33]BGHZ 58. S. 55
[34]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491f.
[35]Staudinger/Hager, 13.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99, § 823, Rn. A14.
[36]Staudinger/Schäfer, 12.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86. § 823, Rn. 9.
[37]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374.
[38]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Ⅱ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 Rn. 1270.
[39]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4. Aufl., C. H. Beck, München 2010, § 25, Rn. 12f.
[40]既然法益与侵权法上的权利已经相等,那么为什么多数德国学者仍习惯于将第823条第1款上的保护对象统称为“法益”,而不是统称为“权利”呢?笔者的理解是,如果统称为权利,由于权利中包括了相对权,因此在字面上总让人有将债权纳入过错责任保护范围的感觉。而“法益”概念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不涉及相对权,因此使用这个概念时,德国学者就无须再对它进行限定了。
[41]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431f;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42]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民法起步较晚,发展起来之时,人格权观念与理论已经甚嚣尘上,并被我们视为当然地继受。于是,我们没有背“人格利益不能直接成为权利”这个思想上的历史包袱。 参考文献
[1]刘芝祥:“法益概念辨识”,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6)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法学界已有很多关于法益的讨论。现将既有讨论的几个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在法益的涵义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将法益界定为权利之外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或类似表述。[1]个别异见认为,任何权利均可称权益、法益,但权利外无权益、法益;主张权利以外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违反法理。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权利、法益、一般利益三者并列讨论,认为法益是介于权利与一般利益之间的一个概念。[2]有一些学者还区分了广义法益与狭义法益,狭义法益仅于权利之外存在,广义法益则将权利也包括在内。[3]总之,既有研究基本上系将法益定位于权利之外的一个法律保护对象。
第二,在法益的词源问题上,许多学者谈到,该概念系来自于德国。[4]其中有的学者直接指明了原词,“‘法益’(rechtsgut)一词,由德国学者首创,日本学者从德文首译。” “法益一词是由德文das rechtsgut翻译而来。”
第三,在法益概念的功能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界定一个独立的法益概念,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其提供民法上或更具体地说是侵权法上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与权利相比,是一种弱保护。[5]
在既有民法“法益”研究的资料来源上,最常被引用的有以下两部分资料:其一,刑法学者关于法益的著述,主要为张明楷教授的专著《法益初论》[6]和台北大学高志明2003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刑法法益概念学说史初探”;其二,民国时期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关于“法益”的一些论述。常被引用的有史尚宽[7]、曾世雄[8]、芮沐[9]、洪逊欣[10]等。
从资料来源角度看,我国目前的民法法益研究至少有以下两个不足。其一,刑法法益理论或可用于参照,但若直接拿来做民法法益研究的根基,恐怕不妥当。比如,刑法基于其公法性,不可能仅将其保护对象指向单个个人,必然会产生诸如“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或“个人法益”、“超个人法益”这样的分类,这就会与以单个私人为思考原点的民法产生不可弥合的间离。其二,台湾学者对法益的论述,多系只言片语,仅系在体系阐述时顺便提及法益,而未及深入。且我们也存在脱离体系背景的误解。[11]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虽然我们一方面指出了“法益”概念源于德国,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几乎没有利用德国民法学中关于“法益”研究的资料;以致我们对“法益”概念在其原生的德国民法体系中的涵义、功能、理论争议、实践发展所知甚微。
这里隐藏着一个方法论问题。当我们从域外引入一个概念,并试图为我所用时,这种比较法上的借鉴何以可能?又何以有效?其前提恐怕是应当首先厘清下述问题:该概念在其发生地是何涵义?它原本被设计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又有何发展?它在实践与判例中的应用如何?理论上又有何争论与流变?有了这一系列清晰的认识,我们才有条件进一步思考:我国是否有同样的问题?该概念又是否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概念是否及怎样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从而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发生体系矛盾?如果未进行以上思考,仅仅是说“这个概念来自某国”,然后就依翻译之后的字面涵义来解释之,并以其为手段来解决自己设想的问题,建构自己设想的体系,这就难称之为一种法律借鉴,也难称为一种比较法研究。此时,说不说“该概念来自某国”都是一样的,对论证与结论均无影响。说了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陈述时的辅陈或导入,或一种“此事古已有之”的隐喻,从而减少他人对概念本身的质疑;但概念的内涵、外延、功能及一切,其实都是自己赋予的。这样的研究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研究结果会格外“多彩”,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其实是在各自发挥想象力。[12]
本文的学术企图,首先不在于在法理学层面上对法益进行一般的探讨,因为这样的探讨至少要弥合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之间的鸿沟,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结论会过于一般,从而缺乏实践意义。其次也不在于在整体民法层面、如权利理论上对法益进行探讨。从前引法益的既有讨论中可以看出,即使是民法层面的法益研究,实际上也是将侵权法作为一个主要的假想适用领域,从法益保护相对于权利而言是一种弱保护即可看出这一点。很显然,合同法上的保护是不区分权利与利益的;由于合意过程可以维持当事人的预期,合同的相对性可以限制请求权人范围,所以纯粹经济损失在合同法上是无疑问地可以得到赔偿的。换言之,利益在合同法上获得的根本不是弱保护。只有在侵权法领域,由于利益保护往往比权利保护需要更强的要件,如存在保护性法规、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这时才谈得到一种对利益的弱保护。事实上,但凡得出较之权利,“法益”只能获得弱保护的结论时,研究者就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到侵权法领域了。总之,最能发挥“法益”研究之意义的民法领域,乃是侵权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学术企图,在于结合“法益”概念的原产地——德国法,以及区分“法益”概念最有意义的民法领域——侵权法这两个要素,探讨德国侵权法上“法益”概念的发生与发展、法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理论上的纷争及实践应用,当我们真正廓清“法益”在德国侵权法中扮演过和扮演着什么角色后,再来考虑该概念对我们有什么可能的意义。
二、法益是什么——当代德国学者的观点
综合德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法益指且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
拉伦茨、卡纳里斯谈到前述保护对象时认为,虽然它们象所有权一样也具有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但它们却并非支配权,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与主体相对的、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可供归属于主体——如同物可归属于所有权人;因此,它们通常不被称为权利,而是被称为法益。”[13]多伊奇、阿伦兹认为:“我们将那些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存利益称为法益,它们尽管具有绝对性,也即可以对抗一切他人而受保护,但并未成为一项绝对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原则上不得转让。”[14]梅迪库斯、劳伦茨认为:“生命、身体、健康与自由不能作为主观权利来理解。只有当人们能够将主体(权利主体)与客体(权利客体)区分开来时,人们才能说这是一项权利:在第823条第1款随后规定的所有权中,所有权人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即其适例。但生命、身体等却并非如此:它们是与人无法分离的人的特性。”[15]有的学者则不加解释,直接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列举的保护对象分为两类进行讨论,或分别称之为“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权利”(所有权、其他权利),[16]或分别称之为“法益”和“绝对权”。[17]
第二,法益指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所有受保护的对象。
也即,这种观点认为,法益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和其他权利”。
费肯杰、海内曼称:“第823条第1款列举如下绝对受保护的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和其他权利”。[18]《艾尔曼民法典评论》将第823条第1款项下所有保护对象统称为“法益”,并称该款为一个“法益导向”的条款。[19]有的著述对第823条第1款下的诸保护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再讨论,而是直接在“法益”或“法益侵害”标题下将所有客体列出。如《帕兰特民法典评论》在“受特殊保护的法益之侵害”项下列举了所有六项保护对象。[20]福克斯则将“法益侵害”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请求权的一个构成要件,并将六项保护对象都包括在内。[21]
综上,暂且作以下两点分析:
其一,可以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不是指权利以外的利益。恰恰相反,“法益”是权利(我们所谓的)之内的一个概念。如果采第一种观点,“法益”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种传统的具体人格权,而在此之外的其他人格权(如名誉权)不包括在内,一切财产权和身份权更不包括在内。这是一个比我们所说的权利要小得多的概念。如果采第二种观点,“法益”的范围较为宽广。由于此时它包括了“其他权利”,而“其他权利”中现在包括了限制物权、知识产权、专属性亲属权等,因此可以认为这时的“法益”有了较广泛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内容。但它仍然不能等同于权利,因为债权是不包括在“法益”范围内的。[22]因此,第二种观点下的“法益”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绝对权”概念,或者称之为“侵权法上的权利”。但无论怎样,德国民法上的“法益”,只能在权利范围之内且比权利小。前文所引我国目前研究中的,所谓狭义上的、在权利之外存在的法益,或广义上的、包括一切权利利益在内的法益,都不是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概念。
其二,德国民法上的“法益”究竟是指什么?是权利(或绝对权),还是“生存利益”(lebensgüter)?是仅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内容,还是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六项内容?这一点还须继续考证。在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争议?这仅仅是一个无谓的概念之争,还是蕴含了深刻的历史、立法、理论和实践背景?
前引德国学者所提到一个将狭义“法益”区分出来的形式理由,即这些“生存利益”与主体无法分离,也无法转让。这一点固然无法否认,但我们也能想到,毕竟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是一个侵权法的基本规定,该条所做的区分应当有侵权法上的意义才对。而“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在受侵害时的保护问题上,与所有权等实无区别。不能转让及难以价值化,仅导致这些“生存利益”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而在归责上,“生存利益”与所有权是毫无区别的。可见,所谓“生存利益”与主体无法分离、无法转让的理由,是极其形式化的,这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玄机,否则何劳拉伦茨、卡纳里斯、梅迪库斯、多伊奇、艾瑟这些大家去做这种无甚意义的区分?
三、法益概念的初始涵义、功能与实践
众所周知,德国侵权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是法国侵权法的一个反动。基于避免侵权责任泛滥,并适当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思想,德国侵权法对侵权赔偿请求权进行了限制。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并不明确保护对象,而德国侵权法限制侵权赔偿可能性的手段之一,就是从利益的广大范围中,挑选出若干典型、成熟的领域给予保护。而且,“这些领域由不同层级组成,即从一般利益到特殊法益再到绝对权利,逐次攀升。”[23]这里我们看到了法益与绝对权利的区分,这一区分也正是民法典立法者的态度。“帝国议会民法典咨询委员会主席恩内克鲁斯(enneccerus)留给我们如下观念,那四种不属于主观权利的生存利益,应当与主观权利区别对待。”[24]
保护对象的区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对象的分级。“从一般利益到特殊法益再到绝对权利,逐次攀升。”这说明,在德国民法典立法时,绝对权利是高于法益的。法益与权利究竟有何不同?多伊奇认为:“权利与法益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可以从以下三个标准来考虑:客体、可转让性、数量是否固定或者说是否能够开放地补充。”[25]法益系与人身密不可分的人格利益,所有权与其他权利仅涉及可与人身分离的财产利益,故前两项区别——客体与可转让性容易理解,要害在于第三项区别。“生存利益已被完全列举;判决不可再创造新的第823条第1款上的法益。”[26]“财产利益理论上可以开放地补充,无论在责任法自身领域,还是通过其它法律领域的新发展,财产利益的开放补充恐怕都是可能的。与之相反,人身利益的数量却并非无穷。”[27]第823条第1款上的法益的数量和内容,已被德国民法典立法者固定下来,并且不允许司法实践再进行创造性的发展;这就是当时立法者的态度。而在这四项法益之外的其他人身利益怎么办?回答是可以通过保护性法规结合第823条第2款进行保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名誉。第823条的前身之——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条第1款中,被列举的保护对象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所有权或其他权利”。[28]而“名誉”这个保护对象后来被删除了,原因就在于刑法典上关于侮辱、诽谤罪的规定(《德国刑法典》第185条以下)可以视为保护性法规,结合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之法规”侵权类型,即可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若一个对名誉的损害行为未构成侮辱、诽谤罪的,立法者则认为民法典没有必要提供超出刑法典的保护程度。[29]
可见,德国民法典立法时,人们的普通认识是财产利益的重要性大于人格利益。因此,与所有权类似的绝对权被认为可以经司法继续扩张,而代表人格利益的法益则被认为已为立法完全固化了。这就是所谓保护对象分层级的一个表现。
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绝对权是有弹性、可发展的,然而在技术上、或者说在形式上依靠什么来保障其发展的可能性呢?这就是立法者创设“其他权利”这个开放性概念的用心。“其他权利”即意味着,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性质上与所有权类似的新型财产利益,司法可以将其纳入到“其他权利”中,从而使其获得过错责任的保护。
接下来便到了问题的核心。法益与权利(绝对权)都受过错责任的保护,保护要件和法律效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必须存在于同一个条款,任何一个都不能被打入第823条第2款或第826条的“另册”。但是,当我们在同一条款中列举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这六项保护对象时,我们会发现,如果不加任何限定,“其他权利”的扩张功能是能够作用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之上的!如果这四项法益与所有权没有区别,则“其他权利”能够吸纳与所有权类似的其他财产利益,也就同样能够吸纳与四项法益类似的其他人格利益,而这一点,恰恰是立法者所不愿看到和力图避免的。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与“所有权、其他权利”是有区别的,是两个不同范畴。“其他权利”只能在本范畴内发挥弹性,但它不能跨越界线,到另一个不同领域中去发挥扩张功能。这两个范畴分别是什么?“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叫做“法益”,“所有权、其他权利”叫做“权利”(或主观权利、绝对权利)。正如前引诸多学者反复强调的,法益不是主观权利。至于为什么不是主观权利?理由大家可以另行总结或创造(如可转让性的不同、主体不能以其自身为客体等),但结论是已定的。
多伊奇对这个故事有一个精辟的总括:“立法者明确命名了法益,因为立法者不想把法益归入主观私权利。一方面的考虑是要把生存利益完全列举,且不得再补充;另一方面是考虑须对一切类似于所有权的绝对主观权利提供全面保护。”[30]
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的判决,忠实地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图。1903年出版的《帝国法院判例集第51卷》中,记录了一个原告起诉要求保护名誉和职业自由的判决。该判决所列的第一个争点,就是“名誉和职业自由是否属于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若以现在的眼光看,至少名誉已经属于“一般人格权”,而“一般人格权”又属于“其他权利”之一种,因此可以获得第823条第1款过错责任之保护。但上世纪初的法官并不这么看。“本案中适用第823条第1款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二审法院意图知晓,能否将名誉、甚至一切人身和绝对权利,都归入无论故意过失致损均能引发赔偿责任的‘其他权利’范围内。有人亦认为,主体对其劳动力及个人能力的自由且不受干扰的利用,无疑也属于‘其他权利’。但是,‘其他权利’这个概念不能如此宽泛地扩张解释。只要还不能从第823条第1款中推断出其他涵义,‘其他权利’就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理解为主观权利。……第823条第1款首先明确列举了如下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无论从现法典中,还是从第823条第1款的发生史中,都无法支持以下观点:即,这些法益已被承认为真正的权利,它们只是权利的一些具体例子……”[31]可以理解,前已述及,民法典第一草案与法典正式文本在第823条第1款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民法典把“名誉”排除于过错责任保护之外。如果司法判决于法典生效仅3年后,就把名誉归入“其他权利”,从而将其纳入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范围,这显然是直接违反了立法者原意。综上,本案中,名誉与对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支配显然不属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法益,同时也不属于与所有权类似的财产权利,故也不能归入“其他权利”。因此,法院的结论是,本案中的名誉与职业自由不受第823条第1款之保护。
四、法益涵义、功能与实践的发展
(一)二战之后的发展
二战之后,德国侵权法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来自于基本法。德国基本法的修改,把人的尊严与人格价值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实践中对人格利益高涨的保护需求,和基本法上人格尊严对部门法的价值渗透的双重作用下,德国侵权法中的人格利益保护有了巨大的发展。于是,以限制人格利益保护为己任的“法益”概念,无可避免地落伍了。它若还要存在,便不能再坚持以往的涵义和功能。
与侵权法上人格保护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以及第2条第2款:“人人均有生命与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个人自由不可侵犯。以上权利只能根据法律进行限制。”
以上基本法条款对侵权法上人格法益保护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第823条第1款中的法益直接转化为主观绝对权利。“此处所述的生命与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及自由权是基本权利,也即主观公权利。根据宪法第1条第3款,基本法约束的首要对象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审判权。基本权利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进入私法发生作用,并得创设私人权利和义务(‘第三人效力’)仍有若干争议。但由于在既有案例中,第823条第1款给予生命、健康和自由的保护,已与生命、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及自由权的宪法保护相重合,因此,对生命等的主观私权利与对生命等权利的宪法保护相一致的体系构成,也就显而易见了。”[32]基本法上的生命、身体、自由权是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价值体系渗透于私法之中,使得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的生命、身体、自由不再仅为低于绝对权的法益,而是直接成为主观权利。
这一立场亦体现在判例中。《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判例集第58卷》记载了如下案例。该案中,由于被告过失导致车祸,致使原告怀有的6个月的胎儿脑部受到损害,该婴儿出生后逐渐患上瘫痪症,原告遂基于孩子的健康损害要求赔偿。与本文主旨相关的是,该判决中出现了对“第823条意义上的对胎儿健康的主观权利的损害”[33]的表述。在这里,“健康”这一“法益”已经被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直接称之为“主观权利”了。
第二,法益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被“一般人格权”所吸纳,进入了“其他权利”范畴。四项法益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如名誉、隐私等,在德国民法典上本无独立的保护依据。但在战后人的尊严与人格价值至高无上的大潮影响之下,诸多其他人格利益也有了强烈的受保护的社会需求。司法为了因应这一点,遂在基本法的价值指导下,缔造了“一般人格权”概念,并将其归为“其他权利”的一种。由此,各种人格利益的保护就不再要求“保护性法规”或“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而只需满足过错责任构成要件即可。[34]
至此,法益与权利的区分便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在基本法与判例的影响下,法益已经被视为权利。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法益与权利区分的目的,乃是要把过错责任的保护范围人为地区分为两个领域,然后使“其他权利”仅在财产领域发挥扩张功能,从而杜绝新的人格权产生。但是,当各种人格利益经“一般人格权”的通道,已经成为“其他权利”的一类时,“其他权利”非但不再是人格权扩张的防火墙,反而成了人格权扩张的推进器。当杜绝人格权扩张这一目的不存在时,为达这一目的的手段——法益与权利的区分——也就不再必要了。因此,现在德国民法学界对法益能否作为权利对待的一般态度是:“虽然在可转让性、保护强度、法律所定义的保护范围、构成要件的形式上仍能看到部分区别,但这些都不能够论证对法益的区别对待。”[35]
综之,“法益与主观权利之间的区分已经被宪法所弥合。”[36]
基于以上认识,回头再看德国学者在法益问题上的“差别观念”。事实上,德国学者并不存在两种观点。应当认为,他们对于法益概念的来龙去脉都是了然的。只是有的学者,如拉伦茨、梅迪库斯,还愿意再作一些解释,提及一些过去的故事。于是,他们先说法益是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在法史上当然是正确的;然后再给出一些诸如主体不可以其自身为客体、法益的不可转让性等形式化理由,这个也无可厚非;最后,他们一般会再指出,“然而这种区分在侵权法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在此无须继续深究。”[37]“在依据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侵权保护方面,法益与绝对权(如所有权)已无区别。”[38]这是现实的态度。
而有的学者,可能认为既然法益与绝对权的区分已经不再有意义,则根本就不必再多做解释,于是他们直接把“法益”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保护对象的统称(如费肯杰、海内曼),或把“法益侵害”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请求权的统一构成要件(如福克斯)。无现实意义之事不必多提,这种态度也无可指摘。
(二)债法改革后德国民法典中的“法益”
2002年债法改革后的德国民法典中,首次使用了“法益”概念,使该概念终于从一个法解释用语,变成了法典正式用语。在债总部分新增的第241条第2款(保护义务)及第311条第2款(缔约过失)中,立法者将“权利、法益、利益”并列规定,三者同为债之保护义务和缔约过失的保护对象。在解释上,“在前合同之债中,当事人即已负有不侵害他人的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权利(如所有权)的义务。……此外,当事人须顾及另一方的其他利益(尤其是概括财产,也包括决定的自由)。”[39]
可见,德国立法上仍沿续了民法典初创时的思想,即“法益”(四种具体人格权)、“权利”(主要是绝对性财产权)、“利益”(主要是纯粹财产利益)三者的概念区分。而且在表述排序上,仍然是权利第一、法益第二、利益第三。相较于法解释,德国立法还是显得比较保守;也不禁令人感慨历史惯性的强大。对此本文再做三点说明。
1.很显然,即使是在这种传统区分下,法益与利益仍然是截然不同的。
2.虽然在第241条第2款、第311条第2款上,权利与法益被区分为两个概念,但两者的保护程度是一样的。债法总论中如此,侵权法中更是如此。
3.当下德国民法中,债法总论立法上“权利、法益、利益”三者的区分表述,与侵权法上普遍存在的“法益”与“权利”(绝对权)混用的情况同时并存。前引诸多混用这两个概念的学者,其著述几乎都发表于2002年之后,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立法上的用词而修改自己侵权法著作中的表达。其实可以想见,侵权法中“法益”与“权利”的混用几乎可以说是必须的,因为若非如此,就无法解释为何与“法益”同质的一般人格利益能成为一项权利(一般人格权属于“其它权利”)。
为何德国债法改革仍然使用了“权利、法益、利益”并列的表述?本文认为,可能立法者意图在“债的保护义务”和“缔约过失”两项制度中,明确保护对象的全面性,于是把立法史上出现过的“权利”、“法益”、“利益”三个保护对象全部列出,以求周延,避免人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可能产生的误解。比如,如果只列“权利、利益”,可能人们会误认为,是否以上制度不保护那几种具体人格权?如果只列“法益、利益”,可能人们会误认为,是否以上制度不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等等。
但仍须指出的是,“法益”概念的出现,是以限制人格利益的保护为目的的。在人格利益扩大化、至上化的今天,是否仍有必要在仅指几项具体人格权意义上维持一个“法益”概念,不无疑问。
五、我国民法是否有必要设立“法益”概念
德国法上的“法益”,传统含义及当下债法总则中含义,是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具体人格权。而在侵权法领域中,德国学者一般将“法益”与侵权法上的权利视为同义;人们既可以说法益即是权利,也可以说受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保护的都是法益。[40]总之,德国民法上的“法益”,在权利(我们所谓的)之内,而非在权利之外。
若认为源自德国民法的“法益”(rechtsgut)概念,系指权利以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这一定是个误解。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不背德国法史的包袱,自主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法益”概念。那么,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究竟有无必要设立一个在权利之外存在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法益”概念呢?
须注意,我们不能因为语言的模糊性,遮蔽了我们的思维。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指“应当”受法律保护,还是指“可以”受法律保护?
如果是指“应当”受法律保护,则须指出,一项利益是不是应当受法律保护,不是这个概念本身决定的,而是利益是否能够充分相关保护规范的构成要件(在权利利益区分的保护体系下,指保护性法规、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的要件;在权益不区分的保护体系下,则在满足过错责任要件之后还须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所决定的。一项利益在没有被保护规范的要件检验之前或法官未做出利益衡量决定之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项“法益”;而检验通过或法官决定保护之后,也已不需要我们再跑来宣称,该利益是一项“法益”了。换言之,所谓“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法益”,是一个对利益决定保护与否的判断结果,而不是用来判断是否保护的前提,该概念本身不可能有这项功能。从逻辑上说,权利和利益都在判断是否保护的起点上(即使是权利受侵害,也要经过过错、因果关系等要件检验),而这里所谓“法益”却在判断保护的终点上。权利和利益的涵义都是可得保护的对象;而这里“法益”的涵义却是已被保护的对象。把权利、利益与这样的“法益”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同一类事物,是有逻辑问题的。而且更根本的,一个处于司法判断终点上的概念,是不能为个案中处于判断起点上的法官提供帮助的,也即,这样的概念缺乏规范功能。
如果法益是指“可以”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个概念与“利益”是同一的。因为“利益”一样也是“可以”受法律保护、也“可以”不受法律保护。这样的“法益”概念,没有提供比“利益”更多的规范功能。
如前文引述,有学者将“权利”、“法益”、“一般利益”三个概念并列讨论,此时“法益”与“一般利益”之间的区别在于,“法益”是可以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里的“法益”其实就是“利益”,而一个确定不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概念,根本就不在民法的视野范围内,因为没有必要。这样的三个概念区分,实质上是把“利益”改名为“法益”,再从法外领域拉来一个概念凑成的。
如前文引述,既有讨论中还存在“广义法益”与“狭义法益”区分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广义法益”是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括权利在内),“狭义法益”则指权利以外的受法律保护之利益。这样包括权利在内的“广义法益”概念,其实只是一个权利与利益的统称,在侵权法上称为“保护对象”(schutzobjekte)。这里的“狭义法益”,其实就是利益。
也有学者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区分“广义法益”和“狭义法益”,“广义法益”包括法律已经规定和应当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狭义法益”指法律已经规定予以保护的一切利益。这里的“狭义法益”相当于前述侵权法上的“保护对象”。而这里的“广义法益”,目的是为了增加一个“应当规定而未规定”的内容;其实,传统民法中的“利益”本来就是开放性的,实践中完全可能出现新型的、现行法未规定的利益,法官此时予以评价地保护(所谓“法律续造”),学说对判例进行整理,在该利益典型化、成熟化后,期待立法的解决。把将来可能出现的保护对象包含在内,本来就是“利益”概念的正常运作方式。
前文引述的诸位台湾学者关于“法益”的论述,各有其表述的具体语境。史尚宽与芮沐先生显然是在“保护他人的法规”意义上,说明此类规范间接地使个人受有利益(法益)。而“保护他人的法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2款)的功能,依通说为保护纯粹经济损失,[41]这是利益的一种典型形态。洪逊欣先生强调的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中,也存在依法律的反射作用而享有利益的情况,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表述为,依法律反射作用享有的利益就是法益。a中含有b,不能推出b=a。其实从文字上也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洪逊欣先生所说的“法益”,就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利益同义。曾世雄先生将权利、法益、自由资源三概念并称,实际上类似于前引有的大陆学者的权利、法益、一般利益的分类。这里的自由资源的特点是,“放任自生自灭者,在法律上不被承认合法,然亦不认之为违法”,其实是一种法外现象。而他所列举的法益种类,大多为典型的利益类型。综之,以上台湾学者使用的“法益”概念,是指利益或利益的一种具体形态。这些台湾学者并无在与利益对立的意义上创造出一个“法益”概念的意图。
综上所述,以德国民法中的“法益”的传统含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来定义的“法益”概念,在我国(包括台湾地区)从未出现过。[42]我国学界对民法“法益”的理论与实践演变,事实上相当陌生,既有研究其实多是在进行自我建构。而这种自我建构出来的“法益”概念,在本文看来并非必要,因为“利益”本身就包含了“可能受法律保护,也可能不受法律保护”的含义,“(可能)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就是“利益”,不是另外一个新事物。以“(可能)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来定义的一个所谓“法益”概念,并不比“利益”具有更多的内涵,当然也没有提供新的规范机能和解释机能。不产生新机能的概念替换,徒增烦扰,且增加了误解的可能与对外交流的困难,没有必要。
侵权法保护对象上,谈权利与利益就足够了。
结语
最后想要再次强调的,还是借鉴的方法问题。当我们借鉴域外概念、理论、制度之时,恐怕还是应当首先透彻了解该概念、理论、制度在其原生体系中的目的、涵义、发展与实践应用之后,再考虑本土存在哪些问题可望利用它来解决。若未经透彻了解这一基础工作,仅根据概念翻译之后的中文表面涵义进行阐发,域外法律资源其实并未得到利用,被利用的只是自己的直觉和逻辑,这不是一种借鉴,也难称妥当。
当然,本文绝非杜绝创新。相反,本文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地域和人民,当然应当有自己的法体系和法文化。只是作为一个法律后发国家,借鉴恐怕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前述观念,可望使我们在借鉴时少一点弯路,多一点成效。
注释:
[1]参见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民事法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郑春玉:“论民法法益的存在及其价值”,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曹险峰:“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白飞鹏、李红:“私法原则、规则的二元结构与法益的侵权法保护”,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张驰、韩强:“民事权利类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1年第12期。参见李锡鹤,“侵权行为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外法益概念质疑”,载《东方法学》2011年第2期。
[2]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参见孙维飞:“弹性的法学移植——以侵权行为法学中法益学说之发展为个案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也有学者以应然性和实然性为标准,区分广义与狭义法益。参见刘芝祥:“法益概念辨识”,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参见李岩:《民事法益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9-10页。孙维飞:“弹性的法学移植——以侵权行为法学中法益学说之发展为个案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张驰、韩强:“民事权利类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1年第12期。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参见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民事法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曹险峰:“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参见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6]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7页。该部分为作者运用日文资料,对德国刑法学中法益概念及理论发展史的一个详细介绍。
[7]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8]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法益者,法律上主体得享有经法律消极承认之特定生活资源。”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9]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权利与法益,二者重要区别,端在主张权之存在与否,权利被侵,主体本身即有向任何方面行使其保障意志之可能。而法律所规定不可侵犯之利益,与其谓为个人之权利,毋宁谓为一般的法益;此处个人即无从直接提出主张。”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0]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法律所保护之利益(法益),未必尽为权利之内容,即其中仍有仅依法律之反射作用而得享有之利益”。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11]举一个典型例子。前引史尚宽先生的表述,“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为既有法益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材料之一。这是史先生在论述侵权行为的“被侵害客体”中的一句话(确切地说,是半句话)。其全句为,“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在违背良俗之侵害,为个人之一切利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史先生是在论述德式或我国台湾地区式的“三个小概括条款”(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法规、违背善良风俗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侵权法结构中,三个概括条款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这里“法益”概念的使用,只是为了说明在“违反保护法规”这一类型中,受侵害的客体为法益,而不是为了概括地说明“什么是法益”,更不是在给“法益”下定义。若仅将史先生这半句话摘出作为依据,或进一步“浓缩”为“史尚宽认为,法益乃法律间接保护之个人利益”,(如前引熊谞龙文,注(19);张开泽文,注(3)甚或更进一步升华为法益定义上的“间接保护说”,(如前引关永红、陈磊甲文,注(3);原文作“简介保护说”,不通,似应为文字错误)徒增误解,未见其可。“违反保护性法规系间接侵害了法益”与“法益乃法律间接保护之个人利益”两句话之间,含义差异之大不啻天渊。
[12]以上概念借鉴和比较法研究上的方法论的类似思考,请参见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13]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s. 374(1994).
[14]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5.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 2009, rn. 231.
[15]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ⅱ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 rn. 1270.
[16]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2,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2,8.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0,s. 151ff.
[17]brox/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1, § 45, rn. 2ff.
[18]fikentscher/heinemann, schuldrecht, 10. aufl.,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2006, rn. 1557.
[19]erman/schiemann, 13. aufl., aschendorff rechtsverlag, kln 2011, § 823, rn. 1.与第823条第1款“法益导向”(rechtsgutsorientiert)相对应的概念是同条第2款的“行为导向”(verhaltensorientiert)。
[20]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71.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2, § 823, rn. 2.
[21]maximilian fuchs, deliktsrecht, 7. aufl., s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2009, s. 10ff.
[22]vgl. münchener kommentar/wagner, 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9, § 823, rn. 142ff.
[23]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1976,s. 13.
[24]erwin 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2.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1996, rn. 57.
[25]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s. 17)1976,
[26]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s. 15)1976.
[27]erwin deutsch , haftungsrecht , carl heymanns verlag , kln/berlin/bonn/münchen(s. 17)1976.
[28]zusammenstellung der gutachtlichen äuerungen zu dem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band ⅱ.,äuerungen zum recht der schuldverhltnisse, otto zeller, osnabrück 1967. s. 397
[29]maximilian fuchs, deliktsrecht, 7. aufl., s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2009, s. 36f.
[30]erwin 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2.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rn. 58(1996).
[31]rgz 51, s. 369ff.
[32]staudinger/schäfer,12.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86., § 823, rn. 9.
[33]bghz 58. s. 55
[34]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491f.
[35]staudinger/hager, 13.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99, § 823, rn. a14.
[36]staudinger/schäfer, 12.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86. § 823, rn. 9.
[37]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374.
[38]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ⅱ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 rn. 1270.
[39]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4. aufl., c. h. beck, münchen 2010, § 25, rn. 12f.
[40]既然法益与侵权法上的权利已经相等,那么为什么多数德国学者仍习惯于将第823条第1款上的保护对象统称为“法益”,而不是统称为“权利”呢?笔者的理解是,如果统称为权利,由于权利中包括了相对权,因此在字面上总让人有将债权纳入过错责任保护范围的感觉。而“法益”概念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不涉及相对权,因此使用这个概念时,德国学者就无须再对它进行限定了。
[41]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431f;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42]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民法起步较晚,发展起来之时,人格权观念与理论已经甚嚣尘上,并被我们视为当然地继受。于是,我们没有背“人格利益不能直接成为权利”这个思想上的历史包袱。 【参考文献】
[1]刘芝祥:“法益概念辨识”,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7)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7-0054-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为了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维护社会的稳定,美国近两年先后通过了一系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如《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法案》(CFPA法案)、《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等,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滥用的损害,监管金融系统性风险。我国的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但是,我国仍有必要借鉴美国的这些做法,通过立法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要通过立法来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特别的保护,必须先在理论上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其与一般消费者特权相比较,金融消费者所享有的应加以特殊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这些理论问题,虽已经成为我国相关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相关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本文将结合已有成果,进一步探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为逐步达成理论共识奠定必要的基础。
一、我国传统消费者概念的局限及修正办法
从逻辑上看,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目前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已经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在不修改该法的情况下,其是否已经足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无法涵括金融消费者这个新概念,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与一般消费者的权益相比,也存在其特殊性,因而,必须理顺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在概念上的逻辑关系。
(一)我国传统消费者概念的局限
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而获得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所谓生活消费是基于人的自然需求而产生的保持人类生存和延续的社会活动。在传统金融法上,通常不采用“消费者”的概念,而是用“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概念,并且投资者与消费者存在着明显差别,投资者不能称为“消费者”。因此,从传统的意义上看,并不存在所谓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以上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将消费限定在生活消费之内而影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缺陷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笔者以为,该传统概念存在如下局限性:
首先,将消费仅仅局限于生活消费,使消费者的外延过于狭小,不能涵括现实生活中全部的消费者。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消费者处于买方的地位,买方只有基于个人的自然需求、为了保持人类生存和延续而购买某商品,才能具有消费者的身份,享有消费者(区别于其他买方)的特殊权益。显然,这种定义不能涵括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例如,某工厂为了办公而购买空调,其员工因空调的质量问题而遭受人身伤害,该员工是否具有消费者的地位?按目前的定义,该员工很难被称为消费者,但是,凭什么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呢?
其次,将消费仅仅局限于生活消费,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多样化,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已经越来越不具有可操作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人类基本的自然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的需求已经不断地多样化,所谓的生活已经不再局限在物质性的生活,而是包含了更多的精神性生活,因而人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精神性的需求。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工作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爱好,成为满足精神性需求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从某种意义是看,精神性需求并非基于人的自然需求而产生,其也非为保持人类生存和延续所必需。在人类需求多样化的今天,人类不仅已经难以分清其某个具体的需求到底是基于个人自然的需求还是非自然的需求,而且进行这种区分也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某公司管理人员购买经营类书籍,谁能断言其满足的只是个人的自然需求?某人狂爱炒股,其在留足生活所需的全部费用后,将全部剩余资金投入股市,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人生乐趣,谁又能说他的这种投资行为不是一种生活消费?
(二)对传统消费者概念的修正
由于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存在着局限,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立法对消费者的界定采用了更为宽泛的办法,如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所谓“消费者”(Con-sumer),是指为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而取得和使用贷款、购买动产、不动产和各类服务的个人。日本、菲律宾、我国台湾地区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纳入了消费者的范畴。因此,我国应当顺应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潮流,扩大消费者的范围。
鉴于生活消费的狭窄性,有学者主张应坚持“生活消费”的开放性、发展性,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生活消费”。笔者认为,为避免歧义,我国可以将传统的消费者概念修正为:消费者是为个人消费而获得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商品或消费的除外。这种定义将消费者同样限定在自然人范围内,取消了“生活消费”的限定,使用排除的方式将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情形排除在外,避免了消费者概念的泛化。
二、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的界定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在金融领域里采用“消费者”的概念,其外延也在逐渐扩大,各类金融机构之相对人的统一称谓“金融消费者”应运而生。英国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首次采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200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法案,使金融消费者作为法律概念得到确认。
(一)我国有关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立法现状及理论争论
我国银监会2006年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但是,我国的证监会并未将“投资人”称为金融消费者,我国的保监会将投保者视为“保险消费者”,我国目前的证券法律、保险法律中,并没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我国学界目前对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如有学者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提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专业化,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交易关系、接受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这种观点沿袭传统的看法,主张区分“投资者”和“消费者”,区分“投资”与“贸易”,区分“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
另有学者则借鉴国外立法的定义,提出应将“消费者”的概念作扩大解释,只要交易双方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地位和实力悬殊,对于弱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可以作为消费者来对待,使之受《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是金融消费者。
我们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但主张应将消费者的外延局限在自然人范围内,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消费者的身份而享有消费者的特权。由于消费者在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法律通过赋予消费者特权以保障实质上的公正。但是,赋予消费者特权,毕竟打破了民法之交易双方法律地位在形式上的平等,扩大消费者的外延将可能产生严重破坏交易主体地位平等的恶果,阻碍交易的进行,因此,非自然人不应纳入金融消费者的外延中。
(二)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特征
结合前述对消费者之修正后的概念,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可定义为: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其特征如下:
第一,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为自然人。满足自然人的需要是人类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之所以赋予消费者特权,正因为消费者是个体的自然人。在各种经济组织越来越强大的现代社会,只有通过强化个人的特权,才能使个人有效对抗强大的经济组织,避免人类生产、经营之终极目的的异化。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机构投资者,无论该机构是否足够专业或强大,因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人消费,就应当排除在外。无论将多么小的企业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畴,都违背了对消费者权益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初衷。
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在于“个人消费”,而非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根据美国CFPA法案第1002条的规定,金融消费的目的限于“个人、家庭或居家之目的”。将前述定义金融消费者之消费目的限定为“个人消费”,虽从字面上看缺少了“家庭或居家之目的”,但在中国个体属于家庭之不可分离一部分的文化语境中,“家庭或居家之目的”实质上可以被“个人消费”所涵盖。不论某自然人的某个具体行为是金融消费还是金融投资,只要其目的在于个人消费,该自然人就具有金融消费者的身份。以公司或机构之人的身份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由于其以生产或经营为直接目的,因而属于金融机构的客户,而非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对象通常表现为一种服务,即使购买的是金融产品,该产品也通常表现为代表权利的产品而非传统意义的物质性产品。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个人的收入越来越多,在满足了其日常的生活消费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将其剩余收入用于投资。个人消费与个人投资在本质上都是个人处分其收入的行为,因此,在单纯的自然人参与的情况下,区分其身份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或区分其行为是“金融消费”还是“金融投资”,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已经没有必要。人类的经济呈阶梯式的周期性发展,即投资-生产-交易-分配,当分配的成果(即个人的收入)超出供养人类自身所需要的物质数量时,分配的成果常会被自然人主体分为两部分,一是用于“消耗”,二是用于“投资”,于是人类经济得以进入下一个发展周期。“消耗”即传统的消费者概念中的生活消费,“投资”与“消耗”并无本质的差别,都是对分配成果的处分,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其差别仅仅在于,“消耗”满足了自然人当前的个人需求,而“投资”则通过与他人进行时间与空间上的价值交换,赚取更多的成果,所满足的是自然人精神的或未来的需求。
有学者将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限定为满足“日常金融消费需要”,这种限定一方面会导致对“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的区分,另一方面无法将公司或机构之人的自然人排除金融消费者的范畴。有学者主张在金融消费者的定义中加入“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限定。这种限定并无必要,因为消费者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不一定就不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否则,一个金融学的教授为个人消费而购买金融商品,其金融消费者的身份就会受到怀疑。至于我国是否应仿照美国CFPA法案第1002条的规定,将金融消费者之特权主体由消费者本人扩大到其人,尚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三、金融消费者之特殊保护的特权
消费者权利不同于一般民法上的民事权利,它与消费者的身份相结合,法律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明确特别赋予的权利,因此消费者的权利又可以被称为消费者的特权。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特权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权、信息权、隐私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损害赔偿权等等。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一种,享有消费者所享有的全部特权,与其他普通消费者的特权相比较,金融消费者的以下特权需要在立法中加以特殊的保护:
(一)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
虽然目前学界尚无将该权利提炼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金融消费者的安全权不仅表现为人身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更重要地表现在财产安全上,即金融机构应确保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并能够获得可预期的结果,如果存在风险,这种风险必须是明示的并且可预见的,绝对不是因为金融机构自身的不可信而导致的。
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是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最基础的一项权利,在金融消费者之特权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试想如果人们不相信将现金存入银行是绝对安全的,有谁会将现金存入银行?如果人们不相信出了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一定会按约定赔偿,有谁会购买保险?如果人们不相信购买股票可以赚钱,又有谁会去炒股?从金融的一般意义上看,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交易,建立在前者对后者的信任基础上,保障后者的可信性,就是保障前者的财产安全权,一切监管后者的措施及制度安排,其最终的目标都可以看成是对前者财产安全权利的保障。
(二)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的知情权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因此,金融消费者之知情权,即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金融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称谓及含义,学界认识并不统一。有人称之为“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权”,指金融消费者及时获取与消费有关的、真实、准确、
全面信息的权利。还有人提出,知情权,包括知悉、获取两层含义。知悉即主观上知晓,而获取即主动索取,因而强调应赋予金融消费者咨询权。
笔者认为,应按大多数人习惯的称谓并按法律对知情权的规定来定义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这样更容易取得共识,避免不必要的学术纷争。消费者的知情权强调的不是消费者主观上要不要知晓或获取相关信息,而是消费者在客观上知晓相关信息的能力和条件,即通过相对人之告知义务,结合消费者自身之认知能力,确保消费者在客观上能够知晓相关信息。对消费者在客观上是否具备知晓相关信息的条件和能力,其他人能够做出客观而清晰的判断,但是对消费者在主观上是否已经知晓或是否想要知晓,除其本人外,无人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赋予金融消费者的咨询权,并不一定能增加消费者知晓之信息的内容,反而易使金融机构获得不问即可以不答的借口,从而增加了消费者的义务。
是否知晓某商品或服务之相关信息,必然会影响消费者是否消费、怎样消费的决策,因此,是否知情,对潜在的消费者能否变为现实的消费者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加以特殊立法保护,是由金融商品与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技术化特性决定的。消费者知情权对于消费者的重要性与其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的专业性、技术性呈正比例关系。在传统的一般交易中,由于作为消费对象的商品与服务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较低,消费者易于知晓,对消费者的认知能力要求也较低,消费者的知情权显得并不重要。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正是由于商品或服务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才出现了知情权这个倾斜性保护消费者的法律概念,以纠正专业化、技术化带来的消费者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遭受的实质的不公正。在金融交易中,因金融商品与金融服务非常专业化、技术化的特性,没有金融机构客观、真实、全面的信息告知或者金融消费者本身不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其很难知晓专业化、技术化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确切含义,因此,没有知情权,金融消费者很难就是否消费、怎样消费金融商品或服务做出合理的选择,在金融交易中,也就更容易遭受实质的不公正。
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通常是通过赋予金融机构告知义务来实现的,即要求金融机构作为提供信息的一方,负担信息传递的义务,强制金融机构披露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应向金融消费者告知其商品或服务真实、完整的情况,提供使其能充分了解有关情况的便利。此外,金融机构应本着对金融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在出售专业性、技术性强,风险性高的金融产品之前,关注具体的金融消费者在客观上的认知能力,如果确认该金融消费者对所要消费的产品不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应建议其不要做出消费的决策。
(三)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的安稳与幸福,对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需求开始出现并不断提高。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各国尚无统一的隐私权的定义。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隐私权”首次以独立民事权益形式出现在了我国的法律层面上,但是,该法并未对隐私权的概念、范围等做详细界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尚未将消费者的隐私权纳入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保护范围,但是一些地方性法规已经将消费者的隐私权纳入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8)
从概念教学的角度出发,《动物怎样保护自己》的教学内容可以在“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概念层次下,从两个方面进行设计――动物的行为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动物能够适应季节的变化。
经过对学生情况的分析,将《动物怎样保护自己》的教学内容设计为两课时,第一课时,学生学习有关“动物的行为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分解概念的内容,如保护色、拟态、逃跑、硬壳保护等动物保护自己的方法;第二课时,学生在第一n时的基础上形成有关分解概念“动物能够适应季节的变化”的认识,如换毛、冬眠、迁徙,使学生螺旋式地形成科学概念――“动物能适应环境,通过获取植物和其他动物的养分来维持生存。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9)
消费者作为一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主体,是应当首要明确的。只有在明确消费者概念的基础上,对消费者的保护才能有的放矢,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的保护。我国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全国性的消费者保护法律。该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一表述并未明确消费者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些问题,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对此进行修正,明确消费者的概念。
二、世界各国及有关国际性组织关于消费者概念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运动起源于美、英等国,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性消费者组织对于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对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消费者是与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相区别的人,是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①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的人。”②英国在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条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③英国1974年颁布的《消费者信用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是“非因自己经营业务而接受同供货商在日常营业中向他或经要求为他提供的商品或劳务的人。”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通过的《消费者保护》规定:“消费者是使商品和服务供个人使用的那些合法人。”④欧盟《消费者法》第2条第5款规定:受到此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自然人,他购买产品的目的不为了商业的或者职业行为。
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在1978年5月10日召开的日内瓦年会上,把“消费者”一词定义为“为个人目的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⑤
从美英等发达国家及国际性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立法来看,对于消费者的定义主要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就消费性质而言,消费者的消费为个人的生活消费,与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资料消费相对应。立法中多注重从身份上进行划分,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生产经营者排除在消费者概念之外;第二,就主体而言,消费者为个人和家庭,不包括团体。立法上多提到个人,将个人作为消费者保护的主要对象,家庭消费次之,不承认团体的消费者地位;第三,就客体范围而言,消费对象包括商品和服务。
三、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学者对消费者概念的定义
对于如何明确消费主体,定义消费者概念,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也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大陆地区
王利明教授认为:“在市场中,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①王利明教授主张在商品交易领域将消费者与商人作为相对的概念。消费者获得商品和服务的目的主要在于消费,是非盈利性的。商人(包含生产者、经营者等)获得商品的目的在于交换,由此获得利益,是盈利性的。从这个本质上可以区分开消费者与商人。对于消费的认识,王利明教授认为不限于指对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的消耗。只要是出于非经营转让的目的,均可认为是在进行消费。王利明教授认为明确消费者的概念,不需要对消费者的内涵进行过多的解释,法律只需划出一条线,将商品交易活动中作为相对概念的消费者与商人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划分开来即可。至于消费者交易前后的动机如何,是为求使用、观赏、储藏甚至是索赔,不在法律考虑之列。
吴景明教授认为:“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公民个人。”②该定义直接援引了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没有对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更多规定。吴景明教授认为消费者的概念具有下列法律特证:(1)消费者是公民个人而非团体,团体、组织应当排除在消费者概念之外;(2)消费者的消费性质是生活消费。但其并未对生活消费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解释;(3)消费者数量众多,且在商品交易中处于弱者地位。
李昌麒教授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满足自己或他人个人生活需要而购买或使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人,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终极消费的主体,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的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其本身并不具有消费者的资格。”③
(二)台湾地区
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指以消费为目的,而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者。”台湾地区学者对此概念有不同的解读。
朱柏松教授认为,消费概念来自于经济学,是与生产概念相对的专用语。法律上使用消费、消费者等用语,内涵更为广泛。消费,指在人类生活过程中,使用财物或消耗服务的行为。消费者,指基于生活消费而购入、使用或消费由事业者所提供商品或服务之人。在法律对消费和消费者的定义上看,重点都在于与生产相对立。
冯震宇教授认为:“只要是以消费为目的而(1)交易;(2)使用商品或;(3)接受服务之人,就是属于消费者。”④冯震宇教授认为交易对价不能成为区分消费者概念的标准。只要是以消费为目的进行的,无论是因购买的、交换的甚至是赠与的商品或服务受到损害,受损者都是台湾《消费者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同样,与商家没有交易关系,但使用了商家的商品或接受了服务而受损的人,也是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对象。
李伸一教授认为:“消费者之认定标准应采主观与客观的综合理论,即须购买者于购买时具有非营利性之主观意思,而购买后实际用于非营利之用途者,其购买者及使用者始适格为消费者保护之对象。”⑤该认定将交易过程与消费区别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观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学者对消费者概念的定义,不难发现,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是否应规定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2)消费者是否应包含单位、团体。
四、消费者概念的定义探究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消费者的概念应当定义为:“消费者,是指为满足个人需要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最终消费的个人。”最终消费者(End User)的概念来源于英美《消费者保护法》发达的国家,它强调的是作为《消费者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应当是对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进行消耗的个人,而非利用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价值的人,以此与生产经营者进行区别。此时消费并非指商品或服务的交易中支付对价的行为,而是指对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进行消耗的行为。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经营者占据商品、服务信息和组织实力的巨大优势,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仅仅按照民商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的原则,赋予双方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保证消费者得到实质上的公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对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对经营者课以更多的义务,由此平衡双方在交易中的力量,达到实质上的公平。既然是进行倾斜保护,不同于民商法调整经济关系常用的填平原则,那么保护的主体必须严加限制,防止由此产生的利益被不当的使用,矫枉过正造成新的不公平。因此,消费者的定义尤为重要。笔者认为不能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经营者店大欺客,利用自身优势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就过多地扩大消费者的范围。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并非只能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许多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能够进行规制,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执法部门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扩大消费者的群体,增加消费者概念的外延并不能真正起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反而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弱势消费者的制定目的。笔者认为,考虑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倾斜保护的特性,不但不应当过多扩大消费者概念的外延,增加消费者群体的数量,反而应当更加严格地定义消费者,挖掘消费者概念的内核,缩小获得倾斜保护的人群数量,保证市场中交易者双方不会因为倾斜保护产生新的实质上的不公平。
最终消费者概念中对商品或服务使用价值的消耗,才是消费者概念的内核。商品和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生产经营者追求的是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价值,以商品或服务换取货币或其他利益。而消费者需要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耗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以满足个人的需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分界线,就在于对于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追求不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区分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只能把消耗了商品或服务使用价值的个人定义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划分开来,使其得到倾斜保护。其余的人群应当根据其交易的性质,依据合同法等民商事法律进行调整。
笔者将消费者定义为:“为个人需要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最终消费的个人”,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一)消费者只能是个人
能够对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进行消耗的人,只能是自然人个人。只有自然人个人才能对商品或服务进行实质性的消耗。其他的民商事主体,如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团体,因为其本身不具有消耗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自然属性,团体对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的消耗都是通过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个人完成的。因此不能认定团体作为最终消费者,仅能把实际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团体中的自然人个人认定为最终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保护法》所保护的对象。
(二)消费者并不限于支付了对价的交易者
消费者消费商品或服务时,是否必须享有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论是所有权归属于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团体,还是归属于家庭,判断是否是消费者,都不以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决定。消费本身是一个事实问题,取决于实际对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进行消耗这样一个事实。在消耗的过程中,消耗的对象是已经投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或服务。只要是对于已经投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或服务,即使还未支付对价进行购买,获得其所有权,但只要对其进行消耗,也是消费者。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如盗窃商场中销售的电器进行使用的,也是消费者。在此情况下,盗贼并未支付对价,也无正当理由占有所用的电器,电器的所有权仍归商场所有。但盗贼因其使用电器,消耗该电器使用价值的事实,就应当获得消费者的地位。如若因此造成其合法权益的损失,商场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应承担的经营者责任进行赔偿。在其他免费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如促销赠送,免费试用等,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消耗者均应当能够被认定为消费者。
(三)交易时不需要特定的目的,但消费时只能是满足个人需要而非经营需要
是否成为消费者,基于其是否消耗了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的事实,而消耗的(上接第19页)目的应当是满足个人需要而非经营等其他需要。因此,在商品或服务交易过程中不必探寻交易者的目的,只有在消耗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时才应当考虑其目的。交易者获得商品或服务是为了赠与他人、自用或是其他什么目的,即便是转卖经营的目的也可,经营者无法探查,也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探查。因为交易者此时并没有实际消耗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他还没有开始消费。例如,某商贩作为交易者以转卖的目的购买了一批饮料,此时他因为口渴喝了其中一瓶。其购买饮料时的目的在于转卖,但他个人消耗了其中一瓶饮料的使用价值时的目的在于满足他个人的需要而非转卖的需要,因此他就是这瓶饮料的消费者。某些学者混淆了交易与消费的界限,认为交易行为即是消费行为。笔者认为,交易行为只产生商品或服务所有权转移的结果,而上述可知,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与是否消费并无关联。因此,交易行为与消费本身并无关联。前几年曾引发热议的“王海打假”事件,笔者认为许多评论中就犯了此种错误。某些评论人将王海购买商品等同于王海消费商品,因此认为其是消费者,应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而笔者认为,王海虽然购买了质量有缺陷或有瑕疵的商品,拥有其所有权,但其购买后仅用于鉴定,确定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从未真正使用该商品,从未消耗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其从未消费过该商品。王海从未消费过这些商品,更不用谈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还是牟利了。因此,王海不应当被认定为消费者。笔者反对实践中将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一并认定为消费者的做法。购买者若没有参与消耗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则根本不应当具有消费者的地位。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10)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温家宝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着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整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历史建筑概念界定及其保护价值评定标准
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历史建筑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尤其历史建筑被确定为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法规适用对象以后,这种特殊含义就上升为法定概念,具有了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换言之,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于是涉及到如何诠释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采用怎样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和筛选历史建筑的问题。历史建筑作为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作出了规定。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历史建筑随之也提升为法定概念。这个概念基于法制管理层面的需要,不再是专业术语,也不再属于学术概念和行政概念的范畴。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之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技术规范,因此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抓紧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技术规范的内容服从行政法规,保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然而目前尚未修改的技术规范仍在继续使用,指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因此因为规范与法规表述不一,使得历史建筑概念更加含混,直接影响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界定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照此进行把握评价,弹性很大。鉴于该规范不仅没有具体说明“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只须评价建(构)筑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包括建(构)筑物承载的特殊历史信息;而且也没有讲清历史建筑界定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指以木构为主的古代建筑?还是砖混结构的近代建筑?或者是包括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是明清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建国初期建筑、文革时期建筑,也或是各个时代和时期兼而有之的建筑?这就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大量事实表明,已经编制、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分析历史建筑现状时,通常都会按照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肌理、现存建筑的数量、建筑结构、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保存完好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采取相应保护整治措施,并在规划文本中绘制成图册。这样做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保护规划会对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进行分类比对,也从来不做这一类的分析。保护规划注重的往往只是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而忽视其历史文脉,只以建筑梁架结构、墙体结构以及现存的完好程度论其保护价值高下,决定对其取舍保弃。于是各地类似“梁林故居”和南京老城南那样承载大量厚重历史信息的老房子,由于规划编制人员认为其建筑质量不佳,便在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将其“判处死刑”,一拆了之。各地普遍形成这种随意拆迁历史建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思想理论存在缺失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缺失造成了技术规范偏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还同时提出了“保护建筑”与“历史建筑群”的概念,并将有权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定位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确定保护建筑是“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进行保护的”“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一方面,这与历史建筑法定概念的基本属性不符;另一方面,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认定“保护
自然保护的概念篇(11)
一、人身权
(一)人身权的概念
人身权的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在我国至今没有一个关于人身权概念的统一理解和界定。首先,从名词概念上,是称为“人身权”,还是称为“人身权利”。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法律中是有区别的。
“人身权”(personal right)被认为是一个民法概念,是指人身非财产权,即人格权和身份权,它所用的“权利”是单数。在中国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中,使用的是“人身权利”这个概念,是指一类与人身有关的内容广泛的权利,治理的“权利”是复数。
诚然,学术界大多只在民法中出现人身权这一概念。在我国的公法领域,一直很难找到人身权这个概念,而只有人身自由权等概念。
在此,笔者认为不应该把人身权概念只作为民法这一部门法概念。人身权是人与生俱来所固有的权利,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以及享有其他一切权力的基础和前提。笔者比较赞同建立起统一的人身权概念。作为一个公私法统一的人身权概念,可以做如下定义:人身权是人与生俱来所固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非财产权利。由此可以实现对人身权法律保护的更全面、系统化。
(二)人身权的内容
民法为保护公民的人身关系而赋予公民以人身权。公民不得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当自己的人身权受到侵害时也可以请求法律救济。
人身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解读那个人身的法律含义。学者认为人身权的客体是人的精神上、躯体上、道德上的利益或幸福,它存在于权利主体的人身,是权利主体的人身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不是财产,既不能有经济学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种利益的享有可以由权利人对人格、身份利益直接支配。
人身权即民事主体在人身关系上所享有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一种民事权利。
人身权是民事主体固有的民事权利,公民自出生到死亡自始至终都享有人身权;是绝对权,具有对抗任何他人的效力;是专属权,具有强烈的人身专属性,一般不得转让(法人的名称权例外);是支配权,是权利主体对自己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支配。
人身权一般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这是人身权与财产权的重要区别,但是部分人身权可以间接地转化为财产利益,如肖像权的使用可能产生的经济利益。
二、人身权的民法保护
众所周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身权的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人身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以宪法为核心,以刑法、民法为基础,包括行政法、劳动法等其他的保障人身权的法律。在此,比这主要简要探讨一下民法对人身权进行保护的相关问题。
(一)人身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民法是保护人身权的两种最主要的法律手段之一。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而是分别制订了民法通则、婚姻法等。
民法通过规定公民享有哪些人身权和侵犯这些人身权应负的民事责任,来实现对人身权的保护。我国现行民事法律有关人身权保护的规定,集中体现在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法律中,内容涵盖了人身权的各方面。
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全面的保护人身权的民事法律体系,这无疑是我国法治进程的一大进步。但同时我国民法在人身权的保护方面仍存在着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我国对人身权的保护水平处在初级的阶段,对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方面的保护比较重视法律比较健全;而对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其他方面的保护力度,相对比较薄弱,且民法规定的比较原则化,不够具体,弹性较大,致使公民这些方面的权利较易受到侵犯,并且较难获得及时、有效、充分的救济。
同时对一般人格权未作规定。 从国外立法例来看,都肯定一般人格权的存在,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在这一条中似乎人格尊严包括在名誉权中,但名誉权作为权利却是人格尊严这一法益在法律上的体现。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确认一般人格权。
三、改革与完善方向
人身权的民法保护既是一个重要的民法课题又是一个崭新的民法课题,从世界范围来看相关制度的建设多处在摸索与发展之中。
我国一方面要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借鉴相关经验,并要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勇气。从人身权民法保护的大局出发,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制定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人身权保护制度。据此,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必须规定一般人格权的民法规范。一般人格权的立法,我国立法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在民法的基本规定中,还没有加以确认。
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母权,立法者将若干人格利益,具体化为个别人格权(如生命、身体、自由、名誉、姓名)。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身权的类型。目前已经确认的人格权类型包括: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婚姻自主权;同时国家赔偿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人身自由进行了保护;司法解释还对人格尊严、隐私、死者人格利益等进行保护。法律予以保护的身份关系包括配偶关系、监护关系、亲属关系等。
在此基础上,未来的民法典要对已有的人身权具体类型进行确认;同时要将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已经予以保护的人身利益上升为具体人身权类型予以确认。
第三,人身权的救济方法应该完全统一。人身权的就及方法一直以来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具体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各项赔偿目的的具体计算标准、赔偿项目性质的确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