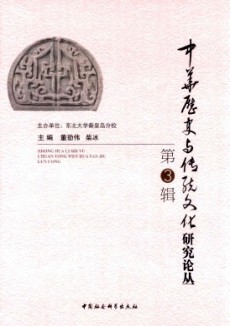传统文化的概念大全11篇
时间:2023-08-15 17:12:21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1)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7-0091-03
1 前言
21世纪的今天民族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从整个大的世界格局看,经过了西方文化全球性扩张的世界,给人类社会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重新返回本民族的文化源头,重新思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找出修正本民族文化在当今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体育方面,以西方为主的现代竞技体育同样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体育场馆的大量建设、兴奋剂的使用、运动方式模式化等等,使得各个国家的政策收入要大量的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而减少了对健身活动本体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体育界开始逐渐把民族传统体育的建设提升到了重点位置,并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从1997年被确立为体育学下的四个二级学科,1998年各体育院校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招生,到现在可以进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培养的学校已经达到了45所,每年有数千名学生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实践等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概念赋予经验以形式,并使明确表达成为可能。甚至在我们试图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概念就已经使我们可能去认识世界中的事物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肯定,只是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作了一个范围上的界定。研究者深知以自己的能力不可能为民族传统体育下一个准确而另人信服的概念,但是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负责和兴趣,本文对以往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与界定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从对概念的实质论辩如人,旨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作一次全新视角的讨论。
2 对目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的理解
概念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模式,它是人们认识事物总体特征的思维起点,是人们对其进行认知、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人们对概念的认识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体现于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等各个层面。人们对概念的认识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事物的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我们所无法达成一致的是概念,而概念又反过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侧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经历不同、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选择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动态的概念。时代的不同,人们的需求不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同,所指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相同。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建设处在初级阶段,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正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处的利益群体不同所给予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从体育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和界定。本文选择了以下几个比较权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时行梳理如下:
张建雄等采用文献研究、逻辑推理等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相关问题进行探析后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独有的,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承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技击、休闲养生、竞技表演、观赏游艺、趣味惊险、民俗音乐歌舞交融特色的体育活动形式。赵进在《“民族”、“民族传统体育”概念及其他》一文中,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人手,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分为“大概念和小概念”两种,界定他所认为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刁振东指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源于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后来人们以世界体育角度为民族体育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大并概括为一个群体,即民族体育的概念通常用来表述与世界范围内规范传播的现代体育竞技活动相对应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这种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导致民族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模糊和混淆。张选惠主编的《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教材中,从强调民族性、传统性及特色性入手,将民族传统体育界定为:是在中华民族中开展的,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叶加宝等主编的《体育概论》中,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多种民族文化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的养生、健身和娱乐体育活动的总称。以上的概念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探讨的主要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本研究在借鉴以上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文化学、逻辑学等相关知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分析。
3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实质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无法给予一个精确而唯一的标准,这是一种妄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对任何概念的界定使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完全信服,而逻辑学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客观现象还是主观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可以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这样概念的可界定与否似乎成为了一种悖论。这一问题的解决让我们回到对概念界定的主体上来,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任何概念的界定都是人们有意识的按照某一逻辑结构进行思维的结果。概念产生的核心是人,是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是最难以把握的变量,每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教育及成长经历等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思维的不同。所以,所有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即便是通过大量的实践和经验,有科学的数据作支撑,并称之为客观,其实这也是一种主观,是主观选择下的客观,因为“如果科学的真是基于经验总结和实践的客观,那么经验总结和实践的客观已经带有某种主观的意向,客观已经打上了主观的烙印,最终问题是:客观问题本身会不会是主观的。”这样,所有对民族传统体育这一概念的界定,只是告诉人们在界定者的心目中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符合这一界定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存在过。因此,对概念的可界定与否并不是一种悖论,只是界定者认为在他心目中某一事物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是界定者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符合这一思维逻辑的所有事物的概括。
4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认知的角度
我们无法给予民族传统体育一个精确而唯一标准的定义,并使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完全信服,但是,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是民族传统体育还是有其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如上所述,所有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是主观选择下的客观,所以,这些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却是可以根据我们的价值期待,或者说根据我们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潜在价值的需要,使民族传统体育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安排。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用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所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我们也要用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规律来看,要从实际出发,不照搬已经成形的、固定化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然后按照它的规定来界定今天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划定今天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切,评判今天所发展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也即是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的一种方法。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2)
【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martial arts more clearly present in front of peopl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tial arts, this paper has a logical analysis on the definition of martial arts in the anci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and logic analysis. It points out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definition of martial arts put forward by the past scholars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using correct logical form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Wushu, clear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martial arts, distinguishing the extension of martial arts.
【Key words】concept of martial arts; logic; essential attribute; extension
引言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以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思维方式。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概念论》中称:“概念无疑是形式,但必须认为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在自身内,并能够同时不为内容所限制或束缚。概念乃是内含于事物本身之中的东西: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即有其中包含概念,因此把握一个对象,即是意识着这对象的概念〔1〕。”因此,对武术概念的逻辑学探究,一方面能揭示武术这一技击内涵,建立良好的武术思维的基础,另一方面能明确武术的外延,亦是形成武术理论体系的基本条件。
然而,武术这一运动文化载体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既要看到古代、近现代的大社会背景对武术发展的影响,又要看到当代“大武术观”对武术“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指导性意义,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明确武术这一概念。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运用形式逻辑定义武术概念,吸收前辈们对武术概念的感性认识,深化、发展、升华武术概念这一理性认识。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以武术概念的定义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查阅了中国武术史、中国武术导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等专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
逻辑分析法:从武术概念的整体到武术概念的部分,再从武术概念的部分到武术概念的整体,以此为逻辑基础,运用归纳、演绎论证方法,对武术概念进行逻辑分析。
2武术概念的演变及逻辑分析
2.1武术概念的历史演变
2.1.1古代武术概念的萌芽
任何事物的概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漫长久远年代里走过来的武术,今天的概念和往昔的概念及所涵盖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少差异,但本质属性是一脉相承的。
武术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称谓,如春秋战国时称“技击”,汉代称“武艺”,清初称“武术”,民国时期称“国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命名为“武术”。“武术”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与门下文人共同编定的《文选》中,但不具有今天武术概念所具有的含义,文中有诗句为“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南朝宋・朱颜年《皇太子释奠会》),其意指停止武战,发扬文治,并非反映今之武术的概念。后人将“武术”一词作为自卫强身之术的专门用语。“武”在甲骨文中指人持戈行进。“术”在甲骨文中指道路。本义:城邑中的道路。《辞海》解释“武”字有多个义项,其中前两个义项是:①“泛称干戈军旅之事”;②“勇猛”。《说文解字》中称“术”字为“邑中道也”,后引申为“技艺”,即方法、技术,如同道路是通达目的的手段。实际上,中国的“武”字,(字面上是战斗),其实是由“止”字(表示“停止”)和“戈”字(意指“矛”)组成的。所谓止戈为“武”。意思是:“停止战争”或者“维护和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古代武术只发挥了其军事功能、防身功效,即与人斗、与兽斗的指导思想。
2.1.2近、现代武术概念的初探
近、现代武术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在政治上帝国列强的侵入、封建制度的瓦解、新政的出现;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经济开始瓦解;文化上,闭关锁国政策不再,中西文化开始碰撞,武术吸收了西方的“体育说”,但武术的技击本质属性、外延没有明确,只是确定了武术的功能和意义,正如以下概述:
1932年编写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认为国术原为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技能,一方面可以锻炼体格之工具〔2〕。
1943年《中国国术馆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宣言》对武术的定义是:“所谓民族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武术也!源远流长,体用兼备,不独在运动工具具有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上有显著之功效〔3〕。”
1949年10月26日至2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武术名家张文广发言:“武术是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强身健体的特点〔4〕。”
2.1.3当代武术概念的争鸣
当代武术概念的争鸣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体制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化上百废待兴,为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而在这个阶段,武术概念的表述出现了唯技击论。
1957年3月张之江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指出: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主要的体育活动方式,这个体育活动方式,在民族健康、民族自卫以及民族医学治疗上,都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5〕。
1957年6月“关于武术性质问题的讨论”,诸专家认为:武术是民族形式体育的内容之一,具有健身、技击、艺术的成分,它是为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培养思想品德,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6〕。
1961年的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则认为,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它具有强筋健骨、增进健康、锻炼意志等作用,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项民族文化财产〔7〕。
1987年出版的武术教材认为,武术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按照攻防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的相互变化规律,编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以及包括对抗技击内容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8〕。
1988年2月,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学分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武术学术专题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武术被定义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9〕。
1988年武术教材编写组编写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认为,武术是一种由踢、打、摔、拿、劈、刺等攻防动作组成的徒手与持器械者搏斗的套路和对抗性运动〔10〕。
1988年由张高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教材认为,武术亦称武艺,是由中国古代技击格斗技术演化而成的一项兼具套路演练及攻防搏斗演练形式的体育运动〔11〕。
1989年由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编写的体育学院普修通用教材认为,武术是以技击为内容,通过套路、搏斗等运动形式,来增强体质、培养意志的民族传统体育〔12〕。
1990年由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体育运动学校教材则认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对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传统体育项目〔13〕。同年,由马明保、张中尧、黄益苏主编的武术教材认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对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传统体育项目〔14〕。而这一年由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人教版武术教材则认为,武术是以带有攻防含义的动作为素材,按照一定的运动规律和规则要求,以套路演练或技击格斗为不同的表现形式,达到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体育运动〔15〕。
1992年由孟昭祥、王建华编著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术教材认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主要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16〕。
1995年由马明保、张中尧、黄益苏主编的全国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专科教材则认为,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散打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17〕。
1996年由武术教材编写组编写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教材认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18〕。
1997年由体育院校成人教育协作组武术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体育院校函授教材则认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19〕。
武术概念的稳定期在21世纪以后,如表1中所著:大部分学者基本认可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2.2武术概念的逻辑分析
2.2.1界定武术概念的形式逻辑规则及意义
从形式逻辑上对武术概念下定义包括三个部分,即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也就是武术的本质属性、分类、武术的上位概念。而形式逻辑也规定对武术概念下定义的规则:第一,定义必须揭示武术的区别性特征。第二,定义项(武术)和被定义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外延必须相等,否则会犯形式逻辑的定义过窄错误(即一个定义把本来属于被定义概念外延的对象排除该概念的外延之外),例如:1988年12月,全国武术专题论文研讨会上,武术的概念被界定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该定义就犯有定义过窄的错误,对武术的分类缺少了功法运动形式。当然,对武术的定义也会出现定义过宽的错误(一个定义把本来不属于被定义概念外延的对象也包括在该概念的外延之内)。又如:1961年的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则认为,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它具有强筋健骨、增进健康、锻炼意志等作用,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项民族文化财产。该定义就没有指出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仅仅指出了武术的体育属性,同时提出了武术的运动形式,而且把武术表述为体育,把武术的外延给扩大了。第三,定义不能恶性循环。在用定义项去刻画、说明被定义项时,定义项本身又需要或依赖于被定义项说明。第四,定义不可用含混、隐晦或比喻性词语来表示。第五,除非必要,定义不能用否定形式或负概念。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方法对武术准确定义呢?形式逻辑上规定属加种差定义是对武术概念最准确的定义方法。即找出被定义概念的属概念,然后找出相应的种类,被定义项就等于种差加上属。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概念的外延之中,而后者的外延并不全部包含在前者的外延之中,则这两个概念之间就有种属关系,前一概念是后一概念的种概念,后一概念则是前一概念的属概念。而武术概念的属就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概念的种差就是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对武术的准确定义,有助于人们能够把对武术的已有认识总结、巩固下来作为以后新的认识武术活动的基础,有助于人们揭示武术这个词语、概念、命题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明确武术的使用范围,进而弄清楚武术这个词语、概念、命题的使用是否合适,是否存在逻辑方面的错误;有助于人们在武术理性的交流与传播中,所使用的武术术语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从而避免因误解、误读所产生的无谓争论,大大提高武术交流的可能性,促进武术传承与传播。
因此,可以将武术概念定义为: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表现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2.2.2武术的内涵:体育属性、技能属性、文化属性、技击属性
武术作为身体运动方式的存在,是记载身体运动的符号,也体现出了武术的体育属性,那么武术的概念应该表述为:武术是一种中国传统攻防技击的体育运动。但是,除了武术,其他运动项目也具有身体运动的属性。所以说,体育属性不具有排他性,不能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
武术内容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技术,它在古代军事斗争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古以来武术就一直发挥着技能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看家护院的家丁,还是镖师、艺人、拳师,都将武术作为一种防身自卫技能。如果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能属性,那么武术概念的表述应为:武术是具有技能属性,以攻防意识为主的体育运动项目。但从中不难发现,跆拳道甚至拳击也具有这样的技能属性,因此,技能属性也不能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
武术不仅具有技能属性、体育属性,还是诠释文化的符号,作为一种文化资源阐释着中国文化,如果其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那么武术则是具有文化属性的攻防意识的传统体育项目,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征,其他的民族传统项目太极拳也具有文化属性。所以说文化属性作为武术的内涵也是不妥的。
武术是中国历代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将零乱的攻防技术不断综合整理、发展,并用套路、格斗、功法形式提炼出来的技术体系。技击属性是武术区别于其他体育运动项目的本质属性。因此,武术的概念必须反映其本质属性――技击性及其技术范畴,如徒手的踢、打、摔、拿和器械的劈、砍、扎、击、刺等攻防格斗技法。
2.2.3武术的运动形式是对抗格斗、套路演练和功法
武术的概念不仅要反映武术的本质属性,而且要反映武术的运动形式。武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抗格斗和套路演练两种基本运动形式,它们平行存在,相互补充。对抗格斗是武术攻防技术在双方直接对抗中的应用,套路演练是武术攻防技术具有一定艺术性的体现,两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通过对抗性练习,可以提高攻防技术,具有强健体魄、防身自卫价值:通过套路练习,既能掌握一定的攻防技能,又能熟练地展示武术的艺术性,具有观赏审美价值。武术概念反映的运动形式既属于体育范畴,又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
2.2.4“内外兼修”反映了武术的文化属性
武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习俗和宗教思想的影响,自然地融会了中国传统的易学、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军事学、美学、养生等多种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逐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武术文化体系。它内涵丰富、寓意深邃,既具备了人类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的共同特性,又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体育运动中的智慧结晶。使武术超越了一般的技能技术层次,也超越了以体能形态为主的竞技的西方体育。武术以阴阳哲学为基础,以“主动”与“主静”及中庸为支架,体现了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诸如整体运动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论、气论、动静说、刚柔说、虚实说,等等,形成了独具风貌的武术文化体系。它既具备了人类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东方文化特有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它是中国文化在人体运动中的表现和载体,从一个侧面辉映出东方民族文化的光彩。“内外兼修”的内容可归结为四个方面:武术追求外在的形健和内在的神韵,从而达到形神兼备;武术训练中既强调练“内”,又强调练“外”,所谓“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武术的“内三合”与“外三合”、内外相合、上下相随,追求一种高度的协调与统一,体现了整体运动观;武术追求内外交修之功,要求武德与拳理、技术与修养结合,达到武术育人的最高境界。所以“内外兼修”一语较形象地表达了武术的传统文化属性。
总括起来说,武术是中国传统技击术,归属于传统的民族体育,又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广义上的武术,是一种包含实用技击的人体文化;狭义上的武术,应称为武术运动,是一种体育运动,主要包含套路和格斗、功法运动形式。从逻辑学上认识,中国传统体育是武术的属概念,武术的套路运动和格斗运动则是概念的外延。比较确切的提法,作为体育项目之一的武术应称为武术运动。
3结论
3.1准确运用形式逻辑界定武术概念
武术概念的界定既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又要体现其本质属性技击和套路、格斗、功法运动形式,以及“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这一文化属性。因此,在对武术概念下定义的同时,既要考虑到形式逻辑上对概念的属加种差的定义规则,又要认识到武术的属、种差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做到对武术概念下定义既不能定义过宽,也不能定义过窄。
3.2明确武术的本质属性
体育学是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而民族传统体育又是体育学的下支,那么民族传统体育是武术的上位概念,其中,三者是从属关系。因此,选择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既要看到武术的整体民族传统体育学,又要看到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组成部分武术;也要从体育学这一宏观视角把握武术这一微观定义。这样才会对研究武术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3.3正确区分武术概念外延
据刘兰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可知,庄子和老子均认为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运动是普遍存在的,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因此,要以运动的观点来对待武术,武术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的文化中完善的。但是,我们也应该以传承的观点来对待武术文化,其中张岱年先生认为:新文化承认原有文化基础的历史继承性,承认文化的发展进化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变化,否则就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同时,这种新文化也承认原有文化在空间上的交流、民族间的沟通,以开放的胸襟迎接、吸纳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充实和增强生命活力〔20〕。这就启示我们要在发扬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武术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会使武术发扬光大,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刷;1996:323.
〔2〕邱丕相,蔡仲林.中国武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
〔3〕王岗.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7.
〔4〕张文广.我的武术生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5〕中央国术馆史编辑委员会.中央国术馆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6:75.
〔6〕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
〔7〕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6.
〔8〕毛景广,吴姗姗,赖国耀.武术〔M〕.河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
〔9〕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
〔10〕武术教材编写组.武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1.
〔11〕张高顺.武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1.
〔12〕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武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1.
〔13〕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教材编写组.武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
〔14〕马明保,张中尧,黄益苏.武术〔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
〔15〕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教材编写组.武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
〔16〕孟昭祥,王建华.武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
〔17〕马明保,张中尧,黄益苏.武术〔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3)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206-01
一、概念书设计与传统书籍设计的界定
概念书被定义为这样的一种书籍:形态上与众不同、内涵、材料令人眼前一亮,具有独创性的书籍。概念书设计应该建立在对书籍内容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但也应该是跳脱出一般的思维方式,从对内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反映本质属性的设计。
传统书籍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从卷轴装、旋风装到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整个中国传统书籍形态的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传统概念里的书籍设计更多注重的是书籍的封面,往往忽略了书籍设计的整体效果。而概念书在注重书籍封面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胆的设想,不再是简单的封面设计而更多的是对形态的创新。
概念书设计是在吸取了中国传统书籍的内在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对传统书籍形态进行的思考,传统书籍对概念书设计起着引导启示的作用。概念书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反映书籍内在的本质,这一点和传统书籍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致的。
二、概念书设计与现代书装设计的比较
现代书装相对于传统书籍设计已经有了全新的设计理念,现代书籍设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部包装,而是以书籍形态为载体的设计。现代书籍更注重的是整体设计。概念书的设计充分发挥了现代书籍整体设计的理念,是一个从内在到外在的视觉设计,是从平面设计到立体构成的完美结合,而且设计者应该充分考虑市场的实际情况,把书籍看成一个360度全方位的销售整体。
现代书籍整体设计强调的是书籍选题、封面、版式以及材料和制作工艺的整体设计,概念书是在书籍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对书籍形态进行的一种探索。概念书是一个“活动的整体”,根据书籍内容的不同可以利用纸张甚至是纸张以外的材料来对书籍的形态进行设计。
现代书籍装帧不再是单纯的书籍设计与制作,更不是仅仅局限于书籍封面的设计,而应该是一种从书籍的内在发展到外部设计的行为。可见概念书是对书籍形态、版面以及材料工艺等进行的全方位的思考,在形态上具有独创性的书籍。
三、概念书设计与书籍形态
(一)概念书设计的内涵
概念书的设计理念,是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对事物的本质有了一定的概括之后进行的设计,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他并不是脱离时代、脱离现代设计而存在的,而是在现代书籍形态设计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概念书不单是封面的设计,而应该充分考虑书籍构成、材料、制作工艺、展示方式直至如何销售等一条完整的系统工程。概念书设计是在书籍整体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要考虑书籍的实用功能。概念书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全面的书籍审美需要,是设计师创造力的展现,它的出现是在总结传统书籍的发展历程上,结合现代书籍设计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设计理念,也是对未来书籍发展提出的一种具有引导意义的设计理念。
(二)概念书设计与书籍形态设计的关系
概念书是一种创新的书籍形态设计。正如杉蒲康平说的:“书籍,不仅仅是容纳文字、承载信息的工具,更应该是一件极具吸引力的物品。”书籍形态的变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每一个时代背景都会有与之相呼应的书籍形态。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4)
一、方法
从方法论上看,中国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的经典构建,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工作者共同编写,1964年3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为标志。这一标志性著作所构建的话语系统,遵循的是一种历史的和本体的逻辑。正如学者吴璨所评述的,“从总体内容上来说,《概论》对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形式,包括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的发展源流、各种体裁形式与风格、表现手段上的艺术特点以及民族音乐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传统等,均做了必要的理论阐述和介绍”。显然,这一话语系统的所指和能指主要是“传统音乐是这样”,而对于“传统音乐为何是这样”,却缺乏更强的阐释能力。
与之不同,民族音乐学话语系统的构建,遵循的是一种不但包括历史的和本体的,同时还包括生态的和互动的在内的(指环境因素的考察分析及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考察分析)、更为多维的逻辑。伍国栋著述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是我国早期民族音乐学专著的代表作之一,分引言、1至7章、后记及附录等10个部分。其中除引言、后记与附录三部分外,其他的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具体说,第1章第2节界定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含义、性质和研究对象,是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的宏观叙述;第2章介绍了民族音乐学的相关学科,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生态的、互动的、网络的方法论的宏观叙述:第3章至第7章详细地介绍了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质量观、实地调查、音乐事项描述和解释及音乐学写作等各种观念和方法,是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具体叙述。同样显明,这一话语系统的所指和能指,就不只是单一的“传统音乐是这样”了,而是“现象——解释——描述——态度”的四维合一,是一个立体的、丰满的、生动的、普遍联系的话语系统。它更具有从宏观的高度和微观的深度来解释“传统音乐为何是这样”的能力。
既然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话语系统运用在我国是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现象的阐释,其阐释成果既具有音乐文化本位的特征,又具有研究方法论的特征,那么,在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中,尽管课程性质更多的是关注音乐文化本体,但在教学话语系统的构建上,仍然非常有必要借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语汇。因为诚如前述,唯有把《民族音乐概论》所代表的传统教学话语与民族音乐学学科话语结合起来,才能从多维的、普遍联系的视角,描述一系列音乐文化现象,并使这种描述具有高度和深度。
按照上述思路,从方法论上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学的话语系统,其语汇可以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音乐学语汇。这包括前述以《民族音乐概论》为代表的、以民族民间音乐分类学为基础的、以传统音乐历史变迁及风格特征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传统语汇,也包括其后大量传统音乐研究文献所建构的,以结构学、乐谱学、乐律学及表演学等为基础的经典语汇:其二是民族音乐学语汇,这包括构成民族音乐学学科范畴的所有原理和方法。在撷取这两类语汇时,我们必须首先对上述诸如分类学、乐谱学、乐律学及民族音乐学的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质量观、田野调查、案头分析、现象描述、音乐学写作等各个领域有较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合适地运用到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之中,从而构成既有学术质感,又有学科意识的教学话语系统。
二、逻辑
《民族音乐概论》一书的写作,其目的首先是为高等音乐院校开设的“民族音乐概论”课提供教材。所以在经集体写作修缮及全国音乐教材会议审定后,其被肯定的体例逻辑,就不但成为一段时间里传统音乐研究文献的经典写作逻辑,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课程教学过程中经典的叙述逻辑。勿容置疑,历史上《民族音乐概论》所奠定的教学叙述逻辑有着开创性、经典性和系统性的意义,但在音乐学发展的今天看来,这一话语系统已经由于它的纯音乐本位化而显得有些不合适。
《民族音乐概论》共5章,分别描述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及器乐五类传统音乐。其中每章又对应对称地分为历史概述、特征描述及新的发展等3节(除第1章分列古代歌曲一节外,其他均同)。仔细研读这一经典作品可以发现,它所建构的实际上是一种纵向历时的、类别线型的、叙述扁平的和纯音乐本位的叙述系统。以第2章歌舞与舞蹈音乐为例,第1节介绍我国歌舞音乐的发展渊源及主要类别;第2节从形态上介绍我国传统歌舞音乐的主要特征;第3节介绍新文化背景下传统歌舞音乐的新发展。显然,这1、2、3节的构置,描述的是单一的歌舞音乐门类(类别线型)从古到今(纵向历时)的概要发展。第2节对传统歌舞音乐“富有生活情趣”、“歌舞结合”、“旋律节拍节奏特点”、“结构形式”及“器乐伴奏”等五大特征的介绍,则是一种问题意识不浓的(叙述扁平)、纯音乐本位的描述。
在我们建构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时,如果说纵向历时的叙述作为一种动态的话语逻辑,是值得继承的话,那么,缺乏多类别横向比较的线型叙述、缺乏问题意识的扁平描写以及缺乏文化网络意识的音乐本位主义,则需要加以改进。
新兴的民族音乐学学科话语,实际上已规定了一种音乐学的写作逻辑,即包括单项音乐事项的纵向历时性叙述、多重音乐事项的横向共时性比较、以人为本的多学科交叉以及从纵向横向、历时共时、学科交叉、普遍联系等多重视角阐释音乐事项因果关系等各种方法在内的,综合的思维逻辑和叙述逻辑。民族音乐学的这种写作逻辑,实际上已经为我们的民族音乐教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语逻辑范式。余下的,只需我们在具体教学中合理选用即可。
就叙述逻辑而言,针对中国民族音乐中的任意一个乐种的教学,我们都可以借助民族音乐学的这种范式,在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基础上,构建出思路简约而又有学术质感的叙述系统。比如,某乐种(下文称为乐种A)的叙述系统示例如下:
1.乐种A历时性的叙述:对乐种做历史学的阐释,以寻求历史依据。
2.乐种A共时性的叙述:对乐种做同空间内的横向比较,包括同质乐种、异质乐种之间的比较,以寻求相互之间的联系。
3。乐种A与环境关系的叙述:对乐种做地理、人文环境的分析,以寻求普遍联系的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规律。
4.乐种主体“人”与乐种A互动的叙述:揭示文化的本质归属——人。
就思维逻辑而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些典型的范式,如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法,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以及在二者基础上生成的三段式推理等。这些思维逻辑,实际上也是一切成熟的,包括自然、社会及思维三大科学形态在内的所有学科所共有的思维逻辑。在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中,针对一些具体的音乐事项,如果适当运用这些逻辑规律,将会使教学话语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和结构力。以下试列表说明:
表1 演绎法示例(以“蒙古族等各中国民族的音乐主要是五声音阶”这一判断的教学为例)
为阐释蒙古族等中国民族的音乐主要是五声音阶这一判断,表1采用了演绎法。其中逻辑起点是一个拟定为已知的正确判断,是逻辑推理中较为抽象的大前提;逻辑中项同样是一个拟定为已知的正确判断,是逻辑推理中一个较之大前提而言稍微具体的小前提;逻辑终点是一个新的判断,是逻辑推理的结果,性质最具体;实践验证不属于三段式逻辑推理链条,而是使用最具体的实例对推理结果正确与否的验证。
表2 归纳法示例(以“西北高原音乐以双四度为特色腔音列”这一判断的教学为例)
为阐释西北高原音乐以双四度为特色腔音列这一判断,表2采用了归纳法。逻辑起点中分析了大量西北高原乐种中的双四度现象,然后以之为基础,经过逻辑中项,推理出西北高原音乐以双四度为特色腔音列的结论。
上述两例,构建了教学话语系统的两种基本的思维逻辑范式。这两种范式,在运用上都具有可逆性。即随着阐释对象的转换,演绎法可以转换成归纳法,反之亦然。如在表1中,当我们把教学目标设置为“中国乐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时,演绎法就转换成了归纳法。而在表2中,如果我们把其设置为“花儿、信天游等西北高原乐种的特色腔音列是什么”时,归纳法就转换成了演绎法。同时,作为思维科学的两种重要逻辑模式,它们普适于中国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任何音乐事项的叙述。无论是历时或共时的形态比较分析,普遍联系的因果关系分析,还是以人为归属的文化功能分析。所以,如果在教学话语系统的构建中,我们能以学生已知的判断为逻辑起点,运用上述的逻辑方法,为学生设计一条逻辑链,帮助他们形成新的判断,那么这种教学话语系统,必定是具有极强的表达力的话语系统。
三、概念
思维运动的起点是概念,概念的相互作用形成判断,判断的相互作用形成推理,推理的终点形成新的判断。这种由概念到判断到推理最后到新的判断的过程,就是思维运动。思维运动是借助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是思维的物质载体。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没有无语言的思维,也没有无思维的语言,思维运动就是语言运动,语言运动也就是思维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概念之于语言运动,同样是基础性的构成。所以,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学话语运动,也必须建立起科学的概念系统。只有在科学的概念建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思维和叙述逻辑,才能建立科学的话语系统。
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叙述系统,缺乏较为严谨的概念意识。以《中国音乐词典》“春调”条目的概念表述为例,条目写道:“民歌的一种。流传于江苏省。……春节期间或立春前后,农村举行迎春、送春等活动时所唱的民歌,统称春调。春调曲调较多……。歌词一般为七字一句……。”一概念界定了春调的类别属性、流传区域以及主要的文化特性和形态特征,可以说基本上构建了一个“春调”的概念。但严格来说,这一概念还存在学科知识层面及学科意识层面的缺陷。从学科知识层面来看,“春调”流传区域的表述并不准确,事实上“春调”的流传区域远不止江苏省而已;从学科意识层面来看,“春调”概念的表述,还应涉及历时性和共时性内容,才显丰满。以概念建构为目的的词典尚且存在概念表述上的疏漏,其他著作就更加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了。脱胎于这一传统著述话语系统的教学话语,在概念表述上当然也存在相似的缺陷。所以,科学地进行概念修辞,解决名正言顺的问题,就成了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构建中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实,民族音乐学在概念建构上同样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参照。这种参照,既包括对民族音乐学学科话语系统中部分已有概念的拿来主义,也包括对民族音乐学概念界定范式的学习借鉴,同时还包括对民族音乐学“局内人”研究方法的运用。
首先,直接把民族音乐学学科中常用的诸如文化价值观、本体观、质量观、网络观、共时性、历时性、本位法、非位法、文化人类学、民俗学、音乐形态学等学科概念拿来构建教学话语系统,是最为便捷和有效的方式。因为这些概念,是民族音乐学长期建设和发展的产物,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原理和学科方法的经典表述,是民族音乐学学科语言中风格统一的、所指和能指约定俗成的核心语汇,同时也是极具学科意识和学术质感的语汇。理解并运用这些概念,使之成为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中的构成部分,不但有助于建立起一个深刻严谨的教学话语系统,同时还能促使民族音乐研究、写作及教学三元的高度统一。
其次,我们可以借助民族音乐学的概念范式,建构民族音乐文化的概念系统。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在其著作中,继承和发展前人关于“乐种”概念界定的成果,提出了“乐种”界定的三要素之说,即“历史构成、文化构成及本体构成”(指某一乐种的概念,应包括它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环境及人的关系、乐种本体形态及特征等三个方面,笔者按)。伍先生这一“乐种”界定新说,实质上正是力图为我国丰富多彩的乐种文化提供一种概念建构的范式。这一范式,深得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精髓,不但可以运用在“江南丝竹”的概念界定上,也可以运用在“西安锣鼓”的概念界定上;不但可以运用在器乐这一狭义的乐种概念界定上,也可以运用在民歌、曲艺及戏曲等广义的乐种概念界定上。它完全可以指导我们在民族音乐教学中逐步建立科学、完善的概念系统。
最后,我们还可以运用民族音乐学“局内人”的研究方法,以完成教学中的概念构建。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意欲建构的概念对象时,为使这一概念更为生动和丰满,我们可以改变“局外人”的身份,转换审察的视角,而成为经验式的“局内人”。传统的教学,通过教师、借助教材来进行,这种方式建立的概念,往往显得枯燥呆板。如果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让学生置身于活态音乐事项之中,采用经验式的教学,那么,他们对音乐事项所形成的概念将完整灵动得多。比如“京剧”,无论我们如何叙述它的历史构成、文化构成和本体构成,学生始终难以真正体会到它的魅力,理解它的特征。但如果让他们唱上几个段子,甚至与京剧演员同台表演几次,那他们心中的京剧概念就会深刻得多。所以,在民族音乐教学中,为帮助学生形成某一完整的音乐事项概念,必要的时候,我们应当效仿民族音乐学“局内人”的研究手段,把这种“置身其中”的经验活动作为建构概念的语言运动的补充,纳入到教学话语系统里来。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5)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23-02
一、民族概念及其起源的双重错位分析
民族,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名词,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根据费孝通教授的解释,“民族”一词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即政治层面上的中华民族统一体,文化层面上的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中国各民族,以及各个民族内部各具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如瑶族内部就有花篮、茶山、盘瑶等[1]。
在中国目前的研究中,关于民族概念存在着双重错位的现象:一是因其起源西欧,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在空间上有错位;二是其作为近现代概念,与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有错位。这两种错位造成了对中国文化整体性的扭曲和分割[2]。笔者对此持有保留意见,并从下面两个方面对双重错位现象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民族”一词是中国古代文献固有的名词。中国古代“民”和“族”的概念及其“民族”观源远流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分类体系[3]。据《汉文“民族”一词考源》一文:1840年以前,中国古籍中用以表达“民族”概念的词语即有:族、族类、族种、种族、种众、种类、种姓、种人、氏族、部族、、部落、等等。①而秦汉以后的“氏族”、“部族”、“种族”、“宗族”、“国族”,“族民”、“部民”、“宗民”,乃至如今耳熟能详的“民族”,与先秦文献中的“族”、“种”、“类”、“姓”、“氏”、“宗”等都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演化过程,孕育了中国古典“民族”概念活性表达的系统[4]。可见,中国具有本土“民族”概念起源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表达“民族”概念的词语俯拾即是,但是“民族”一词却很少见。郝时远在《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一文中列举10例,来证明“民族”一词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固有的名词。比如“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南齐书》中,在该书卷五十四《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的语句[5]。本文在此不便详细展开。然而结合叶舒宪先生所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根据考古工作者在1965年发现的西晋华芳墓的考古资料,“民族”一词渊源还可继续上推一段。华芳的墓志铭上“……夫人华氏,平原高唐人也。其民族繁茂,……”②的“民族”,实际上是指“华氏亲族”。华芳之墓造于永嘉元年,即公元307年。③以此为据,则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汉语传统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6]。
其次,现代民族概念并非是与古代中国社会文化相错位。相反,现代民族概念是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自古以来,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古汉语“民族”一词在传入日本之后,在近代日译西书中对应了西方所采用表示“民族”的概念,继而由日本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族”概念开始逐步采用西方的现代民族概念。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理论预设使用的是斯大林定义的民族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却对此做出了巨大的突破。因此,中国古代“民族”概念是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被赋予了现代意义。
现代民族概念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进入中国的。西方的“民族”概念,主要是为了迎合了当时西方社会一系列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的需要。现代“民族”概念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逐渐融入“民主”、“公民权利”等概念,开始演变为一个政治化的概念。“民族”(nation)概念的演变集中反映了其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这也奠定了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基础[7]。革命后的西方仍需要这个“民族”是因为在西欧语言中,国家state是一个冷酷的字眼。列宁在《国家和革命》将其定义为:“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8]这样的“国家”认同基础狭隘,难以唤起国民对其认同和为其献身的热忱,所以西欧各国不得不把一个与“出身地”和“血缘”有关的拉丁字“natio”提升成具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统一关税)和共同文化含义的“民族(nation)”[9]。
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民”和“族”连缀使用而产生的组合词汇“民族”出现的历史较早,但是“民”与“族”的结合使用却比较松散,其真实含义往往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才能确定。有时,民族是指宗族,例如,《太白阴经》序言中有“倾宗社,灭民族”的语句[10]。有时,民族是指黎民百姓,例如,《忧赋》中有“上自太古,粤有民族”的语句[11]。有时,民族在华夷之辨的意义上使用,例如,《南齐书》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的语句[12]。可见,“民族”一词在古代文献中既可指宗族之属,又可指华夷之辨。
因此笔者认为,“民族”一词的起源不能单纯地划归为西欧。“民族”概念的每一个基本源流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话语体系之中,都以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丰富着“民族”概念[13]。现代中国的“民族”概念主要是将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和苏俄的民族概念与中国本土的民族概念相结合而产生的。前两者都对中国的“民族”概念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民族”概念是不同源流之间相互融合和交汇的结果。
二、“汉民族”体现出“民族”概念的模糊性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提到的汉语“民族”概念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中第一个层次指的是“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而第二层次则是指构成中华民族的“多元的56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概念的“一体”与“多元”两个层次性观点,被学者叶江进一步深化为“中华民族人们共同体是一个由多民族(ethnic groups)共同构成的民族(nation),即文化层面的民族构成国家和政治层面的民族”[14]。
具体而言,汉语“民族”概念在第一层次(即外延较宽,内涵更深)上表现为“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即费先生所说的“一体的民族”概念,也就是与国家相互关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在西语中称为“nation”;而汉语“民族”概念的第二层次(即外延较窄,内涵相对小一些)上表现为我国“56个民族”这一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即费先生所说的“多元的民族”概念,是与文化认同相关联的,在西语中称为“ethnic groups”[15]。因此,如果将西方民族概念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使得“民族”概念在中国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即:民族――nation――国家、政治;族(民族)――ethnic groups――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中,“民族”作为专有名词,只出现在两种场合:一是用于“少数民族”;二是用于“中华民族”。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本土民族概念传统的了解,忽略了中国实际,一些学者往往习惯于套用西方现代民族概念(nation),把用于描述国内各个民族(ethnic groups)的汉语“族”看成由若干相当于近代国家层面“统一特征”或“共同要素”构成的“同质体”的nation。他们模仿诸如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等概念,用“汉民族”来代替“汉族”,这样“汉民族”一词的出现,无疑是将原本清晰的概念再度模糊化,使得“民族”的概念再次陷入争论的焦点。
“汉民族”一词,体现出了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模糊性,是在没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情况下,在“汉族”的基础上,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本身既无法准确传达出中国本土民族概念,同时也不利于中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三、“汉民族”暗含民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汉民族”的出现,很容易让人将“汉民族”与“中华民族”联系起来,并将两者概念加以并置,在国际交流中,就很容易使国外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即“中华民族”就是“大汉民族”,中国文化就是汉民族文化。这就严重扭曲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概念,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人为地割裂开来,强调“汉民族”,忽视各个少数民族的存在、发展以及为中国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这种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二元对立的做法,明显体现出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
因此,本文很是赞同张海洋教授所提到的一个方法,即“保守疗法”:叙述中国历史时,能用汉人的地方,免用汉族;叙述当前中国情况时,能用汉族的地方,免用“汉民族”。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中国需要的不是把汉族这个被对应出的概念提升为“民族”而是把“中华民族”这个“确确实实的民族统一体”用历史文化的内容加以充实[16]。
四、结束语
民族,是一个普世概念,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当今民族概念的内涵常常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中国本土的民族概念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内涵。当代中国的民族理念是在与西方国家的nation和ethnic等概念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为了使国内的民族研究更好地与世界进行学术交流,民族学界在引入西方先进理念的同时,应当注意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尽量避免因忽视传统文化理念而形成的褊狭概念,如文中提到的“汉民族”这一概念,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国内的研究成果展现给世界,为人类民族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
注 释:
①韩康信.汉文“民族”一词考源.1985.
②晋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汉魏南北朝墓志选(通行本).
③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12).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2〕〔9〕〔16〕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11〕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J].民族研究,2004(6).
〔4〕〔6〕龚永辉.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传统考略[J].民族研究,2011(6).
〔5〕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J].民族研究,2004(3).
〔7〕〔12〕〔13〕高永久,等.民族概念的演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09(6).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6)
关于课程这个概念,研究者们在试图使课程概念逐步明朗化的过程中却使之越发变得五花八门、模棱两可。这些定义,按照我国学者郝德永的观点,分别是从学科维度、目标维度、经验维度、活动维度和计划维度来对课程的本质内涵进行限定的。这些维度都回答了课程这个概念的某些功能、特征和属性。如:学科维度反映了课_概念的历史性特征,因为最为传统的课程定义就是从学科角度进行界定的而且,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课程研制科学化运动之前,这种状态从未受到置疑,课程的含义也较明确、一致,而课程形态则表现为单一的学科课程”%目标维度和计划维度则强调了课程的预期性和计划性的特点。显然,如果从属概念必然是一个能够明确、涵盖课程这个被定义概念的定义概念的角度来看,学科维度、目标维度和计划维度都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也不可能成为课程概念的属概念。另外,经验维度虽然超越了传统的“学科”层面,淡化了课程的预期性和计划性,但是,这种把学生在教育过程结束后获得的经验称为课程的观点只能导致“把课程变成了教育的一个结果。这种把课程实施后的结果定义为课程本质内涵的观念造成了极大的逻辑混乱,实质上,课程已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而从活动维度来看,更能看出人们对课程定义的轻率与无奈。“更多的学者把活动视做课程只是出于课程‘全面性’的考虑,因而,这种课程观通常并不反对‘学科课程’,只是考虑到学生在除了教学活动之外的其他活动中也能获取某些知识、经验,而这些知识、经验又是传统的学科课程所无法包容和解释的,于是,便以堆积的方式把这部分活动也纳入到课程含义中”吧“课程是学科与活动的总和”的认识可谓是深入人心。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活动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活动的角度来界定课程,则未免失之偏颇。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课程概念。不同的是,这个命题并不等同于劳顿所谓的课程是“对某种课程文化进行选择”?的课程文化工具存在,而是“还原课程的文化本体地位,是指将课程自身视为一种文化,即课程文化,使课程不再是单纯的、无自为性文化品质的社会文化的承传工具”?,而是“赋予课程一种文化主体地位,使其具有自律性的、内在性的、独特性的文化属性与品质”。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将文化作为课程概念的属概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文化作为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涵盖了人类现实生活的全部领域,而人类的现实生活无非表现为精神、制度和物质三大领域。因此,按照文化形态逻辑和结构的需要,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层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又可分为三个系统:语言符号系统、思维方式系统、价值观念系统。课程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以语言符号形式直观地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又无不受到某种特定文化的渗透,课程也是这种特定文化的产物。一些人类学家更是明确指出所有主要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然包括教育的成分在内,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指明文化应包括哪些领域,一一说明其涉及内容,但它首先应包括教育等在其中。可见,课程本身就是一柄独特的文化存在。
其次,从现有课程概念的定义来看,如果更粗泛地来划分,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把课程看作是学科、计划、人类经验,这一维度实质上就是强调人类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对个体的作用,把课程看作是一种人类文化的凝缩,目的在于使个体成为“文化人”。二是把课程看作是学习者个体的学习经验。而实质上,这种个体的学习经验就是人类文化在个体身上的辐射,内化而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个体文化。而个体又总是生活于前一时代的文化之中又创造着后一时代的文因此,这种个体文化必将成~后一时代的“类文化”,或言“主宰文化”,从而完成文化的传递功能,使得文化得以不断延续。三是把课程看作是一种活动,一种“构成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生气勃勃的活动流'这种课程观看到了隐含在以往的静态课程观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律动,与“文化的内在性、精神性、生命性、创造性和过程性的一面”?达到了惊人程度上的契合,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和捕捉课程的内在主体性。由此可见,课程是一面集人类文化与个体文化,静态文化与动态文化于一体的多棱镜,折射着单色光的美丽,亦折射着复色光的魅力。
再次,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课程,可以对我国目前课程改革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一个崭新的理解。比如,一直困扰课程界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及设置比例等问题,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科学、艺术、道德本身就是观念形态文化的三种基本形式,学校只有“相应地设置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大部类文化相对应的课程,由此才能传递和传播人类文化的整体要素,从逻辑结构上保证学生接受完整性的文化。
二、从内部构成来看课程的种差
如果说属概念提供了被定义概念一个认识的范畴,那么,种差则是对被定义概念的限制,从而使此被定义概念区别于彼被定义概念,因此,仅仅为课程概念寻找到它的属概念还是远远不能揭示课程概念的本质内涵的,还必须要寻找到使得课程这一“种”区别于其他“种”的属性,即种差。
传统逻辑对种差的揭示方式有多种,我们可以从被定义概念的内部构成上去界定,指出被定义概念有哪些子类,或者说由哪些要素组成,从而寻找到课程概念的种差。构成课程这一概念的种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主体。课程主体是课程概念的首要要素。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只有发生了主客体关系的地方,才有主体”气自主性、主观性和自为性是主体的根本特性通使得主体在与客体发生关系时总始终处手主动、支配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对课程主体的不同认识,将决定着对课程支配权、主宰权的不同认识。因为只有课程主体才有权利支配、主宰课程,而非主体者则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和顺应者。
(二)课程指向。课程指向体现着课程概念的功能要素。功能指的是“一个事物系统所具备的对周围其他事物发生作用的能力或根本属性。因此,课程指向反映着课程的外张力,一种对周围事物的外张力。在课程这一生态系统中,授受知识保存文化、发展能力适应与改造社会以及个体完整个性的养成这三种指向从来没有放弃过争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及不同的课程观下总有其存在的时空与理由。
(三)课程本位。课程指向影响着课程本位的确立。同时,课程本位也是个体需要的具体化和实现化。如果说课程指向因素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外在规定性,那么,课程本位则是课程的一个内在要素,是不同个体在卷入课程活动之前必须要明确的预期的结果,也是个体活动延续的维系。现实本位与理想本位构筑了课程本位的两极,在此影响下的课程观于这两极之间作着微妙的“钟摆式”运动。
(四)课程实施途径。课程实施
途径是课程走向实践的重要的中介要素。课程必然要走向实践,实现其预期的目的,这就需要一定的手段、工具及途径。途径的实质就是主体内在力量的物化,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课程活动的效率,也是衡量主体活动的必不可少的直接的客观标准。传统的手段、工具与途径不会由于现代手段、工具与途径的出现与运用而消亡,而现代手段、工具与途径的出现与运用也只是为了能够更好更优化地使课程从理论走向实践。
(五)课程存在形式。课程存在形式是课程实施的载体。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仅要有主体,还要有实施之“物”。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实施之物”应包括一切资源。其中,既应有正规的,也应有_有正规的;既应有显性的,也应有隐性的。也就是说,传统课程观所关注的知识经验理应是课程的一种存在形式,但它仅仅只是一种存在形式,传统课程观所忽视的价值观念、内在体验等也都应该成为课程的必不可少的存在形式。
(六)课程评价。课程评价也是课程概念必不可少的要素。主体按照一定的目的,选择适当的途径,作用于客体后,在主体以及客体身上必然会产生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直观的,也可能是隐含的;可能是正结果,也可1邑是负结果;在个体身上还可能会呈现出量的区别。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评价的手段加以检测,同时通过评价所提供的反馈信息,坚定、扩大或修正、放弃原来的目标。
以上六个方面是课程概念种差的六个主要构件。回溯课程理论发展及其课程研究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课程概念的诸多解读,还是对课程问题的困惑冲突,甚或是对课程理想的憧憬描绘,都离不开这六大构件内部的不断纷争与不断选择,而承载不同价值的选择结果则催生了不同的课程思想。因此,这六大构件的提出,首先可以为解读课程概念,探讨课程问题提供基本的思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目前“云者众多,实则不知所云;争论不断,实则难以成论”的状况。其次,这六大构件为广大实践工作者尤其是一线的教师提供了一个理解课程、建构课程的基本框架,可以使他们在目前铺天盖地而来的“新课程理念”中寻找到一条理解课程、建构课程的途径,走出目前迷茫困惑不知所背的困境,尽快建构起个体的课程哲学,有利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再次,从课程的六大构件来认识课程,也符合人类“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方式,同时也是“分而析之,概而论之”的研究方式的反映。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7)
文化概念对平面设计起着情感依托的平台作用。在我国本土文化中,有许多符合现代设计的文化概念,如文学形象、神话传说、民风民俗等,这些文化概念积淀深厚、内涵成熟,能够有效增强作品的情感表现,更加贴近本土群众,也更加体现区域特色。具体来讲,民族化表现的概念抽取主要有两种方式。
1.1联系历史传统
传统文化是前人经验与思想的结晶,设计师可从古代文明中寻找文化概念,联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构建设计思想。如抽取河图洛书、太极图、八卦图等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图形符号辅助主体图形,或运用古典哲学思想来组织作品的精神世界。在从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概念原型时,设计师要注意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等特定因素,努力发掘受众熟知和乐于接受的部分。陈楠设计的细推科技标志见图1,其文化概念就抽取自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曲江二首》。设计师在构思前对细推科技的名称出处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其原诗中所蕴含的持乐观进取的态度来推究事物的变化,不要让功名束缚与阻碍自身的内涵,并挖掘出潜藏于内涵深处外圆内方的中国传统处事哲学[1],于是便诞生了这一作品。整个标志以黑白两色为主色调,象征阴阳,以首尾相接、一笔呵成的方形和圆形为主图形,象征格物致知、恪守自身的治学精神。
1.2依托文化体系
平面设计民族化的概念抽取不能仅局限于历史传统与现实主题之间的联系,还要放眼于对文化体系的深度剖析。在向传统文化体系抽取设计概念时,设计师要将其看成系统化的单元模块,以文化体系为依托,按照观念—物化—受众的环节对其进行抽取,切不可似懂非懂、生造概念[2]。龙门美术培训机构的标志见图2(图片摘自视觉中国),作品中作为主体图形的“鱼”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设计师依据传统文化典故“鲤鱼跃龙门”提取而来。在典故当中,鲤鱼逆流而上,历尽艰辛,只要越过龙门便可化身为龙,以此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或是逆流前进,奋发向上的精神,其同祝愿考生顺利升入高等学府的主旨寓意相同[3]。受众只需对机构的性质有稍许了解,便能够很快联系到其原有的典故出处,理解标志设计的涵义。
2形象序列和框架体系的构建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复杂和庞大的对应体系,如太极图对应周易,五行对应白青黑黄赤五色等。但有时候指代意义并不明确,能指和所指也不清晰,这就要求设计师要以清晰的观念为指导,根据主题需要从浩瀚的民族文化元素中挖掘自己所需要的符号,并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赋予其创新性的现代化意蕴。传统符号的选择过程既是一种美学判断过程,又是一个内容整合过程,同一个版面设计中的符号元素要形成一定的骨骼框架,并要根据形象的层级序列来进行有机编排,从而引导受众形成独特的心理体验。
2.1形象符号的层级次序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层级次序、系统规划的国家,自商周时期就建立了严密的等级制度,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具有严格的阶级、层次划分系统;发展到明清之时,层级秩序变得更加视觉化以及直观化,就连朝服之上的神兽形象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对应不同品级的官员,如一品鹤、二品鸡、三品雀、四品雁等[4]。这种带有层级次序之意的形象符号,也被应用到了现代平面设计中,尤其是一些体系性较强的平面作品中,更加注重对这种系列化的传统元素符号的使用。例如,香港著名设计师石汉瑞为渣打银行设计的10、20、50、100、500以及1000元港币中的图案,就选取了传统的神兽图形,见图3。其图案分别为鱼、灵龟、狮子、麒麟、凤、龙,遵循由低到高、由水中到陆地再到天上之序,形成一种传统的递进式的层级关系。
2.2象征体系的地域规制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也不尽相同。从五行之中的东西南北中5个地域方向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受海洋影响,形成了渔猎文化,为儒家文化发源地,有关规制化的系列符号较多;西部受高山峡谷影响,形成了山地文化,其生存条件较为恶劣,故多以等作为吉祥符号;南方多为水田,有稻米文化,其精耕细作,造物巧妙;北部多草原,有狩猎文化,多以猛兽纹为装饰图案;中部地域辽阔,为麦作文化,其连接四方,文化较为杂糅[5]。由此可见,特定的象征性符号是一个地区、一种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是当地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审美范式和抽象程式,也是现代人得以缅怀祭祖及回望过去的历史文化符号,因此,设计师要想通过平面作品来取得某一地域的联系与受到该地受众的青睐,就要考虑到象征体系的地域规制,考虑到符号的地域性属性。
3元素规范和版式秩序的确立
在视觉信息高度泛滥的当代社会,只有样式新颖、意蕴深厚的设计作品方能打动受众,民族化的平面设计则凭借其特有的艺术特性和文化内涵在世界设计史上大放异彩。民族化的设计首先源自于对本民族的敬爱,欲借助设计作品带领受众找寻到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其次,民族化的表现较为注重意象化的实现,其通过意象化的处理手法过滤掉次要信息,保留主要信息;再次,在意象化的基础之上对物象进行概念化、概括化、秩序化的处理,以制造出视觉上的愉悦感[6]。总而言之,元素规范和版式秩序的确立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3.1概念化的理解
根据人们对主观事物的理解,将原版民族化的图形符号进行提炼、重组,只留下主干形象,以缩短有效信息的读取时间,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性。例如,图2的标志将鲤鱼的须、鱼鳍、鱼鳞、鱼尾等较为琐碎的部分一一舍去,只留下了富有饱满精神的鱼眼、鱼头以及奋力跃起的腰身,这便是对传统“鲤鱼跃龙门”的图形符号进行了概念化的理解和处理,节约了设计师以及受众的时间。
3.2概括化的表现
我国传统图示纹样的审美功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象征意义得到了弱化。为追求平面作品和谐与审美的要求,设计师对符号原型的处理开始从写实走向抽象,从凌乱走向规整节奏,从物质走向精神,从客观再现走向主观陈述,从而使得原型更具社会性以及人性化[7]。昆曲《桃花扇》宣传海报见图4(图片摘自昵图网),借用撕裂的扇面来概括表现朝代更迭、战火纷飞中世间百姓的凄苦哀愁,用血滴状的图形来概括表现战争的血腥和无情。
3.3秩序化的强调
秩序化强调的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它促使各个视觉要素之间产生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联系。秩序化的生成既可以借助图形的近似、色彩的关联来实现,也可以借助肌理、质感的相似度等来实现[8]。以色彩为例,针对绿色而言,白色、浅绿、中绿和深绿等不同明度的绿色系列,就生成了一种视觉上的秩序感,其提高了设计对象的关联度,降低了设计对象的跳跃性。
4传统文化与现实主题的结合
在选定文化概念、建立基础框架、确立版式秩序后,设计师就需要考虑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实主题相结合,即平面设计民族化表现的最终实现方式。从微观角度来讲,传统文化与现实主题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4.1置换
在确定好能够负载、象征民族化内涵的符号形象后,设计师要在图形条理化的基础上,选择其中主题表达最为典型的一部分对主体形象进行替代,让受众自己根据已有的文化元素联系现实主题,以此联想到作品所要传达的意义[9]。中秋礼盒包装见图5(图片摘自百度百科),设计师选择了圆形的立体实物,即纽扣,对“月”字中的两横笔画进行替代,如此一来,朴素、平实的表面就有了对称和凸起的点装饰,不仅造型新颖,民族风浓郁,而且更贴合了“月圆中秋”的设计主题。
4.2同构
同构是平面设计中经常出现的组合手法,它能够将不同时空、不同比例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觉图形,以有限的图形语言表达无限的内涵。在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同构设计时,设计师要找出该元素同现代主题之间相契合的部分,然后以轮廓相似部分或共有部分作为桥接元素将两者组合到一起,以此传达某种主旨[10]。一笔定清廉公益广告见图6(图片摘自求是理论网),设计师以毛笔笔头位置作为同构部分,将毛笔杆和含苞待放的荷花两种事物组合在一起。其中,荷花代表清正、廉明的品质,毛笔杆则象征官员的权利,两者同构结合在一起传达了官员要保持廉洁作风的主旨。
5结语
民族文化本身蕴含着前辈睿智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数代人不断完善的实践成果,往往比较接近事物本真面貌和本质特性,能够揭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面貌与价值观[11]。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进行平面创作之时,首先要根据主题需要设定一个清晰的概念,然后结合现代人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从浩瀚的民族文化中撷取最具表现力的民族符号语言,并对此进行符号转换、编码加工、秩序构建等多层次的处理,促成平面设计作品与民族化元素的完美结合,引起受众心灵上的触动。
作者:叶萍 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禹.浅议包装可持续设计的定位原则[J].中国包装工业,2014(8):25—28.
[2]赖亚楠.设计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的文化系统[J].包装工程,2014,35(14):137—140.
[3]张凯.传统民间造物艺术在本能水平情感化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14,35(20):71—74.
[4]胡心怡.论绘本设计中的视觉形态暗示[J].艺术百家,2013(6):241—243.
[5]金国勇.传统图形元素与品牌形象策划[J].新美术,2014(5):108—110.
[6]郭宇承,刘淼.海报设计中图像表现形式的创新[J].包装工程,2014,35(24):76.
[7]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M].纪江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王增成.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D].天津:河北工业大学,2013.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8)
1、中国图案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通过劳动和生活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存,中国特有的传统图案有如龙凤纹、如意纹、四神纹、合头鱼、人物……各类图案,还包括自然崇拜所留下的日、月、星、山、水、树木以及佛教中的莲花、佛手,少数民族的更是多而美丽,这些图案纹样都具有各自美好的寓意,表达了人们的审美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传统图案都经过了历史的积淀,反映出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许多在这个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标志,以它体现出的鲜明特点、文化内涵深受人们的喜爱,广而流传。
在许多航空公司的标志中,我们都立刻提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一只腾飞的凤凰,它的灵感就取材于一出土青铜器的神鸟的造形,无论在远古还是现代,凤凰都是中华文化中美丽的祥瑞之禽,是华夏文明的象征,传达了航空业“展翅飞翔”的理念。同样是以凤凰为主轴的还有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标,它是借用了彩陶上的凤鸟图型,并使用了中国特有的“喜相逢”的结构形式,反映出一种厚实的文化底蕴,而凤鸟那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特色,像这种取其“形”的设计当然不等同于简单的不看对像的照搬,而是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创造是设计师在理解的基础上,用现代的审美观念对其传统元素的改造、提炼、运用,使其更有特色,更易被现代人所接受。
2、中国书法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书法是通过象形文字来传达概念的,每个汉字都同时兼备词和图像的功能,将概念和表达,语义和图标融为一体,展示出令人惊叹、复杂而丰富优美的视觉语言,而西方艺术却没有可与之比拟的东西,中国书法五种主要书写体篆、隶、楷、行、草均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各具个性的视觉美感,其中篆书用笔“骨气丰匀,方圆妙绝”,结体“平稳端严凝重,疏密匀停”,极具古雅的装饰之美;隶书笔画方中带圆,撇捺舒展,结构均衡,华贵典雅;楷书结构平正,严整规矩,沉着稳重,端庄秀丽;草书奔放遒劲,潇洒飘逸,连绵回计中时,要看内容的需要,再选择适合的书体,如“喜之郎”的标志,它就是以草书字体造型,它的结构组合、大小安排、笔画处理均显出草书艺术自由洒脱,表达了欢快、喜悦、活泼和感受,孩子们很喜欢并接受了这个品牌。
3、中国印章在现代标志设计的体现
提到篆刻在现代设计中的阐释,我不得不提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2003年8月3日,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在北京天坛祈年殿,一时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我认为“中国印”的设计是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设计中最完美的体现,所以,我要在这里主要谈一谈“中国印”的设计。
说起以往的奥运会,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想起当时的象征——会徽和吉祥物,举办一届出色的奥运会,首先要创造一个非常出色的会徽。而这次“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之所以会被选中,我们首先要从它的图形设计的概念讲起,经过我对一系列资料的详细了解,原来“中国印”图形设计有它5个方面的概念,分别为“印信”概念,“象形文字”概念,“奥林匹克”概念,“龙”的概念,以及“红色”概念。下面我分别详细的阐述一下这5个概念的不同涵意。
3.1“印信”概念
作为奥运会徽主体图案的“印章”早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了,是渊源深远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印”以此来寓意北京将“举办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是对大家的庄严的承诺。 印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透明部分的“京”,喻意“公正”、“友谊”的原则及君子风范,同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并将发扬广大,以它崭新的面貌走出世界,给人们以诚信中国的感受。
3.2“象形文字”概念
象形文字是汉字的起源,具有我们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觉特征的象形文字,它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和古老文明,而“中国印”我们可以称之为符号艺术,它这种会徽的造型运用是集中国传统艺术特征与现代设计语言于一体,“中国印”中的“京”字,用中国传统的金石,篆刻及书法……艺术风格,又与运动会主题相结合,重新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崭新的、舞动的“京”字。
3.3“奥运匹克”概念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现代艺术的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的人是一种迎接胜利的人物形态,形象很欢快,在蕴含中国文化的同时,充满了动感。
3.4“龙”的概念
提到龙,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华文明及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征,而会徽中的“京”字巧妙在与“龙”字相结合,就形成了现在这个被赋予龙文化的形态,从文化的层面展现出了运动的风采,使奥林匹克精神有了更美好的寓意。
3.5“红色”概念
红色历来都是中国的代表性色彩,中国的国旗主体色就是红色,代表喜庆、庄严、传统的文化特点,红色本身具有热情、向上、阳光……自然属性又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庆典的特征,红色在这里就象征着奥运圣火与运动的激情,它也是北京呈献给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以上这会徽的5个图形设计概念和字体设计加在一起成就了一个让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也明确的传达出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独特的个性,鲜明的设计理念,创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奥运精神最完美的结合。与会徽图形设计组成为完整会徽的还有它的字体设计,BEIJING2008字形是兼承了中国书法传统,采用的是汉简书写、简洁、流畅,还要和奥运五环混然结合,而且用汉简风格书写英文字母的方式独具特色,这一英文书写是中国独创的。
说到这,我们都能感受到我们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感受大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精神上的和谐,这恰巧与西方艺术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中国的艺术要想走向世界,成为独树一帜的艺术体系,我们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就必须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给予东西方艺术最恰当的结合。我坚信有一天中国平面设计也会繁荣兴旺起来。
参考文献:
[1] 钟明善.中国书法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7.
[2] 王凤义.商标图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5.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9)
〔分类号〕TH18
Research on Vector Retrieval Model Based on Ontology Concept
NieHu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275
LongZhaohui
Lingnan College,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275
〔Abstract〕For obtaining a document's feature value of vector space model, this paper pust forward an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document's feature value, which is not based on term space but concept space. This methodis supported by field ontology, and the words of document are firstly mapped to the ontology concept spac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s of each other. Then, unlike normal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weight of term is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thematic conceptual vector retrieval model.Since document's feature vector is constructed in the light of semantic content of Doc,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oncept VSM is better than normal VSM.
〔Keywords〕ontologyconceptual retrievalvector retrieval model
1引 言
目前文本检索最常用的是基于关键词的矢量空间模型,该模型利用出现在文本中的某些关键词语及表征关键词重要性的权值构成矢量,表达文本与查询需求的语义内容[1],并采用矢量内积计算文本特征矢量与查询矢量间的相似度,以此给出中选文本的排序。由于矢量空间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内容的特征描述,又以词匹配策略为检索机制,因此往往存在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①矢量空间模型以文本中出现的词形表达文本的语义内容,其相关性判断只是词语的字面匹配。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等情况难解决;②缺乏具有语义特征的规范词汇集,抽取索引词的方法建立在语法基础上,索引关键词语表达语义的能力有限,致使文本的特征矢量并不能有效地代表文本的语义内容。另外,因为没有具有语义特征的规范词集,检索请求的矢量描述随意且不精确,也不能有效代表用户的信息需求[2]。这种检索模型的性能自然不佳。
在检索机制中引入语义处理技术,是文本检索智能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即针对矢量检索机制中的语义处理展开研究。为了使构造的特征词矢量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用户查询或文本原义,我们将文本及查询表示为概念的矢量表达,化传统的矢量检索模型为基于语义的概念矢量检索模型,不仅能解决一义多词和一词多义等问题,而且经过语义处理的文本特征矢量与查询矢量更准确地表达了其内容的原义,沿用矢量内积的方法计算得到的相似度也更能体现文本间的语义关联。另外,大量研究表明,本体作为表达语义的基础是合适的[2]。基于此,在本体支持下,我们构建领域知识的概念空间,利用本体概念间的相等关系、同义关系、上下位关系及其他相关性归纳融合文本词条,重构本文及查询语句的特征描述,实现基于概念空间的矢量检索模型。
文章的第2部分给出矢量检索模型的一般定义。第3部分探讨在本体支持下的文本及查询的概念矢量表达及概念权重的计算方法,给出概念矢量模型中的相似度计算。第4部分与传统矢量检索模型进行比较,实验分析该方法的检索性能及效果。
2矢量空间模型
传统的矢量检索模型,以词形为基础选择索引词,再运用一定的项加权策略(通常为tf-idf)设定索引词的权值,构成文本及查询的特征矢量。一般情况,文本被表达为词条( Term )空间中的某个矢量T{ti, dtij},
公式(1)中的tfi为词条ti在文本dj中出现的频度,表示一个词出现在文本中的次数,其值越大越能体现文本的特征。但如果一个词出现在多个文本中,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则该词的特征表现力不强,应抑制tfi的作用[3]。因此,增加权控制log( n/dfi ), n为文本集的总数,dfi为包含词条ti的文本数。dtij随dfi值的增大而减小,特征表现能力减弱。
可见,传统矢量模型评价一个词在文本中的作用主要考虑的是孤立词本身出现的频度tf [3],因为没有对表征内容的词条进行进一步的基于语义特征的规范与融合,由此构造的文本特征值难以有效地反映本文的语义内容,检索性能难保证。另一方面,索引词条数量庞大,使得基于词条频度的文本特征向量维数过大,导致实际匹配计算产生困难。
3本体支持下的文本特征描述
为了使构造的特征词矢量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用户查询或文本原义,同时降低特征矢量的维数,我们在构造矢量的过程中引入本体。本体,尤其是领域本体,是对领域知识的规范定义,具有概念化,明确,形式化和可共享的特点,它将领域知识抽象为概念、关系、实例等一组元素,以概念关联建立起领域的知识体系,其核心为一组描述领域知识的规范术语。由于规范的术语概念不受词汇语种、多义性和歧义性的影响,利用概念的抽象性将数个同义词条归结为同一概念,以概念来表征文本特征,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其本质内容[4]。
3.1词条-概念的映射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词条空间-概念空间的映射,借助本体中的类属关系及同义关系,将一组有关联的索引词条映射到本体的某个概念上。
文本的预处理。采取排除法,剔除对表达语义内容无贡献的虚词、助词及普通词,将语义处理的对象定位在一组表征内容的实体词上。
映射。利用本体概念间的各种关联描述,以一定的映射规则,将表征文本内容的实体词条映射到领域本体的概念空间。规范流程如图1所示:
构建“词条-概念”的关联矩阵TC。经过规范,建立起概念与词条的对应关系,由此生成 “词条-概念”的关联矩阵TC。设k,m分别代表概念及索引词条的数目,有
(2)式表明,当ti为描述概念cj的规范词条时, 对cj的表征程度最高,为1。当ti的近义词为描述cj的规范词条时,表征cj的程度在0-1之间(a的取值根据ti的同义词与cj的关联程度设定,若简化处理,a的经验取值为0.8左右。但在实际应用中,还需根据所采用的同义词典或词汇本体量化词条与概念间的相似度或关联度,并依此进一步细化a)。关联矩阵TC将文本中的一组索引词条映射到本体中的某个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基于概念的向量空间模型。
本计算模型,我们只考虑了类属关系和同义关系的概念融合,事实上本体词汇的关联丰富多样。对复杂的情况,更合理的处理应该依据本体定义中具体的概念关联,量化词汇间的语义相似度,并以此为度量的标准,建立映射关系及关联矩阵。
3.2构建概念矢量空间模型
得到每个词条所对应的概念后,我们建立概念基础上的文本特征矢量。文本 di 被描述为一组概念C{cj,dcij}, cj为概念,dcij为cj的权值,表征cj对文档di的特征描述程度。设文本的数目为n,m为特征词条的数目,k为概念的数目。则:
dcij表示文本di中概念cj的特征权值. 该公式的意义为首先将文本集映射至特征词条空间,即建立文本-词条关联矩阵DT,dtij表征文本di中词条j的特征权值,求解方法采用传统的tfi×df。再利用词条空间到概念空间的映射,即建立词条-概念关联矩阵TC,tcij的求解见公式(3)。由(1)(4)式得:
基于同一概念空间的矢量描述,经过归一化处理,我们以两个矢量的夹角余弦衡量文档与查询矢量的语义相似度[5]。
4实验与分析
本文研究的是基于领域本体概念的矢量空间模型,因此实验建立在已构建的领域本体之上,测试数据选取的是受限领域的相关文本。
实验一:选用Protégé3.0为本体开发工具,参照相关的计算机词典及《中国规范主题词表》,手工建立了一个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术语本体,涉及领域概念术语约50个。层次化的本体结构规范了概念的描述及概念的类属关系(术语本体结构的部分内容,见图2),同义词典进一步明确了概念的规范用词及同义关联。
实验二:选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相关科技文献。为了更清晰地明确主题,我们取文摘部分为具体的测试文本。经过文本预处理,抽取文摘中的相关词条为索引,建立以词形为基础的矢量空间模型。进一步,将抽取的索引词条映射到本体的概念空间,化传统的矢量空间模型为概念矢量空间模型。对这两个模型,统计词条频度与概念频度的分布,进行分析比较,(见图3)。
图3为期刊论文“基于弹簧质点模型的二维/三维映射算法”(软件学报,1999年 02期)文摘部分词条频度与概念频度的分布图。全文抽取索引关键词,映射至术语本体的相关概念。如图,经过概念的融合与归纳,矢量空间高频义项的分布得到加强并趋于均衡。比较看出,一般词条统计下的高频词少,最高频度集中在0.6附近,占词条总数的23%。而概念统计的平均义项频度就达到0.6,高频概念集中在0.9附近,占到40%。这说明,一方面,基于本体的词条-概念映射法则不仅过滤了一部分领域知识外的低频词,另一方面,相当部分的低频词条通过语义关联抽象为概念,文本中的语义内容得到了有效的归纳与提炼,高频概念频度增加,由此生成的文本特征表达更符合文本的实质内容。
实验三:检索性能的评测与分析。我们选取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有关文档50篇,利用实验一建立的术语本体实现基于本体概念的矢量空间模型。依据给定的查询语句,检索并返回相关的文本。为评测检索性能,我们将检索结果与传统的矢量检索模型进行了对比。图4显示的即是准确率与召回率曲线(本实验中映射函数的参数,设定为0.8)。从中可以看到,基于概念的矢量检索模型的检索效果明显优于面向词条的矢量模型。因为,经过概念的融合与归纳,文档的矢量描述有效地表达了文本的主题内容,语义内容更明确,检索性能得以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概念检索建立在领域本体基础上,同时评测数据也为受限领域的相关文本,因此检索性能与领域本体的定义有直接的关系。但在同一个测试环境中,对于大多数查询,概念矢量模型都具有较之传统矢量模型更好地表现。个别例外的产生多是由于构成文档的词条关联丰富,采用简单的上下位及同义映射所获取的文本特征矢量不足以表达文本的真实语义,从而影响到最终的检索结果。因而,利用本体概念间的语义关联更细致的刻画词条-概念的映射关系,可以进一步优化细化模型,获得更好的检索效果。
5结论及未来的工作
本文针对传统矢量空间模型文本特征值的计算,给出了将文本的评价由基于语法的词条空间转化为概念空间的方法和策略。考虑到本体在语义检索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利用了本体概念间的各种关联,以一定的映射规则,将词条映射到本体的概念空间,构建出词条-概念的关联矩阵。而基于词条统计的文本特征矢量经过词条-概念的矩阵变换,实现了词条特征权到概念特征权的转换。该方法用概念统计和语义归纳替代传统的词频统计[6],从语义层次构建文本的特征矢量。理论和实验证明,较之传统的矢量空间模型,这一方法可以获得更好的检索效果。下一步工作,我们将利用本体的语义关联,计算本体概念间的语义相关度,进一部细化词条与概念间的映射关系,优化检索模型,以期获得更理想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赵军,金千里,徐波. 面向文本检索的语义计算. 计算机学报,2005, 28(12):2068-2077.
[2]宋峻峰,张维明,肖卫东,等. 基于本体的信息检索模型研究.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 41(2):190-197.
[3]罗三定,陆文彦,王浩,等. 基于概念的文本类别特征提取与文本模糊匹配.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16:97-104.
[4]张敏,宋睿华,马少平.基于语义关系查询扩展的文档重构方法. 计算机学报,2004,27(10):1395-1401.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10)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38-10
汉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积累,其中新文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开拓与发展,亦以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日益充实的内蕴,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格局中颇为活跃及颇具潜力的学科。不过这一学科从概念而言尚缺少有力的学术整合:明明都是以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写作为内涵,却被习惯性地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某种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常常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1] (P76) 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现,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承认。
一、“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的通称“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三个月之后,胡适于19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2] (P34)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3] (P59) 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① 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的政治考量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相当关键。刚刚开始运作这样的概念更替之时,“中国新文学”概念也刚刚得到了普遍的学术确认,一些研究者便从反思乃至批判新文学的角度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以示另辟蹊径,这方面最初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乃是钱基博出版于193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先行态。钱基博不满于新文学,不无偏执地将新文学视为“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4](P472) 因而自然不同意将“民国纪元以后”的文学概称之为“新文学”,而是认定新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成就还是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它们都属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与操作。这样的概念把握虽然基于一种偏见,却较之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概念更显得健全与科学,因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将现代历史时期的“古文学”视为自己的当然研究对象,直到近些年在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有限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才部分地体现出类似的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30年代初期钱基博等人想到用“现代文学”概念冲击“新文学”,并不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现代文学”概念在此后的文学学科发展中更具优势,而是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现代”一词的敏感与呼应。那时正是中国在战乱频仍的短暂间隙中向世界现代化潮流大规模开放的辉煌时刻,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生活直逼西方摩登时代的前沿风气,“现代”及其译音词“摩登”势已成为时代文化的关键术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以取代“新文学”一度已成必行之势。那时《现代》成为最具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代》的前身乃是《新文艺》。《新文艺》改为《现代》,作为关键词的“新”为“现代”所取代,正喻示着“新文学”概念将让位于“现代文学”。虽然研究者仍习惯于沿用“新文学”概念,但“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早已隐然成势。据称,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便称“现代文学”。[5]
新文学概念强调的是与旧文学的相对性,较多地融入了传统因素的考量,所揭示的仍然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现代文学概念关注的是时代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内涵还是从摩登涵义来考察,都是将文学的外部关系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其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学术含量都不如新文学概念。新文学倡导者无论如何偏激地反对旧文学,都是在价值观念上承载了旧文学传统的巨大压力,因而迫切地追求新的文学传统,铸成新文学,以求得解放与超脱。他们深知旧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学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于旧文学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学传统,即陈独秀所谓“陈陈相因”的文学“形体”,以及“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文学“内容”;于是,在斥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之余,并不回避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柳、元、白以及“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的称颂与赞赏。[6] 同样,胡适反对代表过去时代的旧文学,也不过是因为旧文学所体现的“古典主义”传统“当废”,[7] 这并不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组建文学研究会时立意将建设新文学与整理旧文学联系起来,在改革《小说月报》时也承认给“旧有文学”以一席之地,以肯定其“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都说明他们对于旧文学传统的价值承担。对于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而言,旧文学传统力量是那样地巨大而沉重,一般性地注入时代性因素难以形成克服乃至抵御的力量,于是,文学的“现代”内涵远没有文学的“新”传统的铸成更有力度也更加重要,这便是新文学作为概念远胜于现代文学的深层原理。
因此,作为新文学概念的“新”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性地理解的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等等,这种浅表层面的“新”确实可以用诸如“现代”或“当代”等时间概念来替代;新文学概念之“新”乃是吁求着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尽管这种新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新文学家的表述中有差异:在胡适的表述中常有“真文学”与“活文学”之称,在周作人的表述中则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在陈独秀、沈雁冰的表述中似成“写实文学”之类,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表述中常是“为人生的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者试图建立新文学传统以摆脱旧文学传统的思想印痕。新文学家们在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同时,每每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多有不满,同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充满敬意,但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心态下坚持新文学的方向,其奥秘乃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自信与坚持:惟有从新的传统的角度才能使得新文学家充满着面对旧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别的因素,包括时代性因素都无法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胡适一贯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理论,正像他一贯力倡“白话文学之为文学之正宗”,[8] 但他们却并不十分强调“真文学”、“活文学”的时代因素,更不认同“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摩登色彩,相反,他们主张普通的抒情写世文学,表现人生之一般的文学,而不是成色十足地体现时代因素的文学,因而,新文学概念比现代文学概念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能体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学术厚度。
热衷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概念建设的人们忽略了“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新文学传统命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忽略使得新文学概念在时代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强调中变得灰暗不堪。如果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标志,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还有可能在新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概念之间找到徘徊的余地,则“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文学作为学术和学科概念的历史性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来表述,① 内涵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某种政治强势,于是在50-60年代之交②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格局,将汉语新文学从与传统文学的诸多纠结中擢,完全成了具有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的概念,一个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最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港澳台乃至于国外的汉语文化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来探讨,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这样的学术尴尬只有通过强调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新传统来加以克服,任何时代性或地域性的分割与强调最终都必须让位于新文学传统的统驭。③
新文学概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不仅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两层基本含义,而且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命意。新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致力于建立和发扬新的文学传统,这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意志行动,也是汉语新文学内在统一的根本依据,这一根本依据最终将中止人为的学科分割,促进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为历史所接受。近年来“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的陆续出现,[9] 体现出学术界从概念上整合这一学术整体的跃跃欲试心理。
二、“汉语”作为中心词的理论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另一中心词自然是作为语言种类的“汉语”。新文学传统当然会通过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加以承载,可在更沉潜更深入的意义上乃是通过现代汉语得以风格论的呈现。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理论上较之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概念更具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概念以国家、政体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负面影响。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新文学传统强调的语言革新因素甚至思想革命因素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体因素的考量。新文学所开辟的新传统以现代汉语(通俗地说便是白话)为基础和基本载体,这就注定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对于国家、政体范畴的某种超越性,决定了它作为学术概念对各个时代各个不同区域的汉语文学所具有的高度涵盖力。
汉语新文学,从理论上说,就是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作为概念,它可以相对于传统的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汉语文学,也可以相对于以“政治社团”为依据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等等。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言语社团”即是指依靠同一种语言相互交往的族群,它显然与“政治社团”(国家之类)并不统一。[10] (P36) 文学是通过语言思维创造,也是通过语言载体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无论从其创作活动的内部情形还是从其被接受的外部效应来看,文学的“言语社团”属性总是比其“政治社团”属性更大、更明显、更重要。文学接受的外部实践证明,一般情形下的文学诉诸于接受者的首先不是作者的国籍或作品中的国族意识,而是它借以思维、创造和呈现的语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一个“言语社团”有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整体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作为学术概念的一门文学既可以以国家和政治社团为依据进行界定,也可以以“言语社团”为依据加以涵括。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加以分割的整体形态,这便是汉语的“言语社团”作为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在文学表达的韵味、美感及象征意趣上的明显趋近,构成了汉语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文学的特色、风貌,这样的文学风格及其审美特性,往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度文学或民族风格更能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作出实质性的和整体性的贡献。有些语言学家明确认为一种语言的总体风格与操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文化完全一致:“语言风格首先是指某一种语言在世界上全部语言的总体中,它所特有的全部区别特征的总和。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的民族风格。”[11] (P110) 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成果需要多种语言形态甚至需要所有语言形态加以体现,在这种巨大丰富性的积累之中,汉语文学客观上必然是以统一的文学方阵出现并区别于别的语种的文学。事实上,就新文学而言,全世界的汉语写作所承续和发扬的都是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所带来并鲜活地体现的现代汉语巨大的审美表现力和逐渐成熟的表现风格,越来越明显地镶嵌在人类文明的审美记忆之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区域的汉语写作者都程度不同地作有贡献并与有荣焉。
总体上和整体上的汉语写作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无论被称作“中国气派”还是民族风格,其实都不过是中华文化原型的语言体现。任何种类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主要通过语言的表述和写照加以传达;文化有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等等各类形态,不过最切实的文化形态则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表象,而且还恰恰是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12] (P270) 而作为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的文化,也还是通过语言承载并体现出来的。因此,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本质体现最终回落是在语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经常被理解为或诠释成东亚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但通过汉语表达并成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遗产,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任何别的民族都无法强取豪夺的,有了汉语这一硬性的承载,诸如孔子学说这样的灿烂文化传统就不可能被涵括进别的文化系统之中。
汉语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但用以审美地处理这样的环境与经验,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念依据甚至伦理依据,却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并在现代汉语中凝结成型的新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创造性思维。尽管异域文化和文学对新文化和新文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现代汉语及相应的现代汉语思维通过文学创作已经对之进行了无可否认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作为特定的精神遗产积淀下来的一定是为现代汉语所经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达的成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刻画还是在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上,外国文学影响通过汉语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都可能积淀成汉语文学的精神遗产,而不经过这样的语言转化则无法取得这种精神遗产资格。早在80年代初,文学史家唐就对西方文学影响必须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相吻合的现象作过精辟论述:“西方思潮和外来形式在同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时,尤其是同中国人民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由于不能同中国语言或者中国生活相结合,因而遭到失败的结果,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关于后者他例举到了李金发食洋不化的象征诗歌以及一些人尝试着引进终归失败的商赖体。[13] (P22-23)
由于语言对文学的性质,以及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相互关系有着如此深刻而鲜明的决定性作用,当一种文学需要作为一门学术乃至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时候,理应首先作语言分类,在确定语言类别的前提下再顾及这种文学的其他品性。汉语新文学的首倡者胡适虽然未能证明他十分稔熟于这样的理论,但他当时的言论足以表明,他十分清楚这一类道理。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比《文学改良刍议》更加准确地切中了新文学建设的要穴――国语的要素。文章的副标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相关论述虽未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境界,但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倡白话文学深刻得多,也本质得多:“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 (P64) 这实际上首次提出了以国语的白话(也就是现代汉语)构建新文学的汉语新文学本质命题。这是汉语新文学富有活力的品质,也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对于新文学的语言品质及其与使命的联系,先驱者貌似浅泛的认识却远远比后人所理解或批判的深刻得多。胡适的“国语的文学”观除了坚持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外还强调白话语言的普通化,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自明性的内蕴。
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的和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首先站出来反对新文学的恰恰是身体力行地倡导文学和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严复、林纾,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非质疑新文化倡导者的开放态度和现代意识,而是为了捍卫文言的正统以狙击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对文学语言的侵袭。黄侃、刘师培等国故派以及章士钊的甲寅派攻击新文学的要害问题也在于白话文的提倡。特别是学衡派,在文学上也持有改良之论,其浓重的西学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新文学的天敌,正如梅光迪所言“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他们只是觉得文言和白话分别体现一定时期文学体裁的需要,不应偏废文言而独尊白话:“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4] 至于新文学同路人的一些议论争持,例如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商榷意见,也都集中在对废除文言的某种偏激性言论的不满。这些关于汉语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在五四时代频度较高,它们不仅对现代汉语作文学表现的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主动的或事实上的帮助,而且也为新文学家在不断提高现代汉语表达的艺术性和精熟度提供了或正面或反面的激励与鞭策,从而加速了白话文学的成熟,提高了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水平。关于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并非走出五四时代便已结束,在20年代末的白话“文学专制”论,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的“大众语”讨论,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30年代与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的探讨,如此等等,牵扯到文学语言的争讼一直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即使似乎早已尘埃落定的文白之争,便是到了近些年也常有风生水起之兆。这些都足以说明,新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凝结着汉语语言的若干关键问题,新文学进化的每一个关键时段,其突出的矛盾都会通过语言问题彰显出来响。汉语新文学发展至今,其在总体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意象的创造方面所积累的每一个成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汉语语言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汉语新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程度,在各个区域都会大致持平,体现出共同的时代风貌。这样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同区域汉语新文学的相互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归结为现代汉语的内在基质及其生长、成熟和发展频率的作用。后一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便是大陆与台湾经历了30年的彼此阻隔,当两岸文学可以彼此交流的时候,人们也还是能够不无惊讶地发现,虽然一些术语和表述习惯有了距离,但文学描写、文学表现的语言仍然是彼此相通,且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近些年两岸的汉语新诗都充斥着后现代的鼓噪,看看那些后现代的诗,汉语语言策略和语言秩序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异,但这变异的趋向与幅度,无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台港澳抑或是海外的华人世界,都相当接近。这便是汉语新文学整体性发展的一般情形与基本规律。
汉语新文学超越于国家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学术界在重新认知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前提下,突破现有的各种以政治疆域为基本范畴的概念体系,建构或还原到以语言为本位的概念体系,实事求是地承认并使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这一概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基本状貌,弥平了由政治板块、政治疏隔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在内涵与外延明确统一的学术前提下建构起和谐、整一、协调发展的汉语新文学学科,使得这一学科能够超越政治板块和地域分割,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科学而稳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新文学研究者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弥平国家和区域分别,整一性地把握汉语文学的学术趋势。即就文学批评史而言,“90年代以来,近、现、当代三个时期断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逐渐多起来;在地域上也有台湾、香港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而近几年来,更提出了撰写整体的、综合的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是着眼于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近、现、当代拉通,又涵盖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15] (P86)“整个民族”乃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按照新文学研究者的基本构成说,应为“整个汉民族”更确切;而说到整个汉民族,则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旅居国外的华人,因此最可靠的整合概念还是应以汉语言为中心,“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在类似的学术吁求中呼之欲出。
三、学术实践的价值与趋势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而深刻的历史依据,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其作为学科概念,也体现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
这样的学术实践价值仍然首先体现在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在实践意义上,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就是精神的家园,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这种对于母语的文学情感甚至会冲淡、覆盖或代替原本应该十分敏感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上个世纪50年代,周策纵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新文学写作方面显得尤其活跃,胡适对此倍加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① 另外两个中心则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胡适当然不会真的将在美国发生的文学现象算作“中国的文艺”,而且还是中心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白马社是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写作的第三个中心,足以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界并列。当他将这样的意思表述为“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时,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对于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而言,当去国怀乡之思只能在异国异乡遥远地、凄楚地述说,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国族的区分,客观上无法在中国文学大家族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时,其惟一的安慰便是,他们的作品毕竟还是汉语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聂华苓那句“汉语就是我的家”① 才分外显得那么真挚、真切和真实。
并不单是汉语新文学所涵盖的文学现象适合于从语种的范围加以定义,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被中国学者习惯上笼而统之地称为外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文学现象,其实都适用于从语种而不是从国别进行定义,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立足于语言范围的定义总是比立足于国族范畴的定义更科学,更准确,也更富有张力。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过《中国文学史略》并编有讲义,到中山大学后旋即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这里应该包含着从汉语语言角度命名中国文学史的卓越开创之功。中国古代文学资深学者程千帆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前些年合作撰著了一部别致新颖的文学史专著,对于学术概念的“一名之立”特别重视,不惜“旬日踌躇”的程氏,在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阵脚中终能别立一帜,以“汉语文学史”为中心概念,将这本专著命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16] 强调文学汉语范畴的“汉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概念比强调国族意识的“中国文学史”概念显然更准确,更科学,也更恰如其分,它谦逊而又实在地表明自己研究的不过是以汉语写作的古代文学史,而不能涉及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汉语文学史有可能部分地超出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早在林传甲、黄人等还没有撰著《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人、日本学者已经著有多部《支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连韩国学人都有类似的著作先后问世。日、韩学者的此类著述没有从汉语角度定义中国文学史,可能含有一定的文化防御成分,因为传统的日本、韩国文学有相当部分属于汉语文学,在他们有些人的心目中,本国语言文学是在与汉语文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确实有韩国人就是以“汉文文学/国文文学的斗争史”来写作一部本国的文学史。②
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教授心目中,世界各国的文学史都以国别史加以区分,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等等。其实,这其间的情形特别复杂,类似的命名往往还是以语种辨别为多,例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因为以语种划定文学品类,才能厘清各种文学的传统,才能体现各种文学的整体风貌。一般理解的英语文学包括英国文学,也包括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以及一些英属殖民地的文学。在中国人的翻译和理解中,英语文学常常与英国文学相混淆,随之这其间的复杂性更显得恍惚迷离。例如中文翻译的美国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在讲述英语文学的第14章所列的有关参考书目书名翻译就是如此,与英语文学或英国文学相关的书籍有:圣特博雷的《英语文学史精编》,高尔兰兹等参加的《剑桥英国文学史》,亨利・莫雷的《英语文学初编》,泰纳主编的《英国文学史》,F.瑞兰的《英语文学编年史》,斯托福特・布洛克的《英语文学》,此外,作者特别提到,“与《剑桥英国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理查德・加内特和爱德蒙・格斯主编的《英语文学史图解》”,“另外一部如百科全书似,比较有价值的书就是B.E.K.谭・宾克和J.J.朱塞朗德主编的《英语世界文学史》”。③ 在这种混乱迷离之中应能看出作者和译者为准确地区分作为国别史的“英国文学史”和作为语种类别的“英语文学史”所作的艰辛努力,更应看到,所列举到的这一类专书以“英语文学”作为中心概念的占到3/4,可见人们更习惯于使用“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的概念。其实英语概念“English Literature”在更多语境下更妥当的翻译应是“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它常常包括美国文学等其他国家的英语写作。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的《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原书名是“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 Art”,译者注意到这里的“English Literature”不单是“英国文学”,于是翻译为“英美文学”,[17] 殊不知这样还是不能涵盖书中的内容,应摈弃国别考量而进入语种界定,译为“英语文学”便顺理成章。同样的道理,“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这样的概念一般情形下都将比“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具有更大的涵盖力和更明确的内涵指向。有些跨国语种的文学从来就无法用国别史来定义,如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18]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吠陀语、巴利语使用地区的文学现象,涉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其所包容的内涵根本无法以其中一两个国度的文学来定义。
以语种定义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体现着一种人们乐意承认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事实、学术趋势与学术成果,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应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相并列,从而取得历史的与世界的文学视野和巨大涵盖力;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又十分有必要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定义出汉语新文学,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不仅学术实践可以证明,学科建设的实践也已证明,以语种定位并弱化了政治意识的概念并不会产生任何负面效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本科专业被定名为“汉语言文学”并应用了几十年,其所显示的准确性、科学性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汉语新文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名称,纳入“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序列之中应显得更加协调与吻合。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确立或运用,简洁明快地克服了原先各种概念和名称的混乱、夹缠和模糊,为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理论空间。当然,这一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用医学术语说可能有若干“预后”问题,不过这些“预后”问题仍可以通过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而逐个解决。
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或许是,汉语新文学概念似乎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但全面而科学的汉语新文学研究将会冲破这种想当然的妄测。汉语新文学概念无论是在学术主题还是在学术科目甚至是在学科意义上确立,并不应遮蔽或替代各个政治实体的文学板块的研究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共时态的汉语新文学整合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不影响更不应阻止对各个条块的汉语新文学作任何国别的、区域的研究,正像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号称是“世界文学”(the World’s Literature)的故事,可他还是必须分列成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板块进行分别阐述,尽管看得出来他并不十分愿意这样做。当研究者将中国新文学置于国际性的汉语新文学这一全视锦屏之上时,会更加清楚地发现,中国新文学相对于其他离散的汉语新文学,其传统辐射力、现实影响力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地位将更加突出。
从汉语语言的角度定义新文学的概念,并且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实践论证汉语之于新文学建立与发展的主导性价值,是否会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这是汉语新文学概念运用之际可能会遭遇到的质疑。表面上看起来,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语言学家萨比尔等倡导的语言影响和决定思维的语言决定论,[19] 违反了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类思维的基本命题,但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他的语言不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体现?因此,“语言决定论”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未必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确认并注重汉语语言对于新文学概念的某种决定性,由此框定汉语新文学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这只是概念建构过程中的学术论证和理论陈述,并不是对汉语新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设计与规定;在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前提下,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大可以沿着任何学术路数慨然前行,完全不必一定眷顾其中的语言因素。汉语新文学概念旨在拓展这门学术的研究路径,由此概念抽绎出任何更觉限制的学术规定性,都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误解。
总之,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讨论,所涉及的乃是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语言本体的认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与学科空间的拓展。这一概念吻合于新文学倡导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形态,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以汉语语种定义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这一学术趋势使得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地位,而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汉语新文学又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被定义出来;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当然,汉语新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整合性概念当中的一个,它带着明显的理论优势,同时也显露出一些难以圆转的理论缺陷,包括上文提及的“语言决定论”的某种嫌疑。整合汉语新文学学术和学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学术任务,需要在更加扎实的学术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理论,寻求新的有效的路径。
注:
①均有讲义为证。朱氏讲义后人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周氏讲义仍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
①这样的表述不时地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和专著之中,如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茅盾《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等等。
②一般认为以如下二部集体编著为标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③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最为流行和最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例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092-2106页。
①据周策纵回忆,见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高雄)2007年第10期。
①转引自饶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②参见[韩]柳浚弼《东亚视角的可能性――中日本国文学史叙述的产生、特点及其历史脉络之比较》,《新文学》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1页,注释1。
③[美]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原书名为A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1924年出版。中文译者孙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
[参考文献]
[1]杨玉圣,张保生主编. 学术规范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胡适.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A]. 胡适文集(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 胡适文集(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5]萧乾. 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J]. 新文学史料,1992,(1).
[6]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7]胡适. 寄陈独秀[J]. 新青年,第2卷第2号.
[8]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J]. 新青年,第2卷第5号.
[9]朱寿桐. 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文学”[J]. 东南学术,2004,(2);黄万华. 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曹万生主编.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李开. 现代结构主义的一颗明星――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导引[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11]王希杰. 语言风格和民族文化[A]. 程祥徽、黎运汉编. 语言风格论集[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Ross Pool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A]. Identities: Race, Class, Gender and Nationality[C]. edited by Linda Martin Alcoff and Eduardo Mendiet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
[13]唐.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A].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4]梅光迪. 评提倡新文化者[J]. 学衡,第1期.
[15]黄曼君. 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6]程千帆,程章灿.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传统文化的概念篇(11)
abstract: some oversea schola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aise some valuable questions which are worthwh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y thoroughly. observing from the backgroung of thoughts, the inspiration of “asiacentric” theory i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afrocentric”, and benefit from a stro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ence, to form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emise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s a fair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undamental ideas, key concepts, and models. although the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enlightening,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problems, e.g. “imagining asia” and weak academic achievment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centric theory;communication ethnics;literature review
近来,一批海外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者[1]投身于亚洲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方法和前提,比如陈国明和starosta(2003)讨论了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其中的领军人物三池贤孝(miike,2002/2004)已经明确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通过一些 文献 和会议形成了一些相近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松散群体。WWw.133229.Com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形成。”(赵晶晶编译,2008:2)所谓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可能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亚洲中心论”并不过分,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以廓清未来的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思想背景与哲学预设
miike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miike,2004)
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自然 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的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the afrocentric idea,asante,1998,1999)的观点的启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 历史 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 教育 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
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普遍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
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罗杰斯(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就很容易忘记印度、 中国 、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
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 现代 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20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的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的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1998)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
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具有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来着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本土性文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们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1987)。
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
正是基于这样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
miike(2002)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其中包括三重预设。
首先,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的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作为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提倡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
其次,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成的松散文化圈。
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通过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义。ishii(2001)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
第四,亚洲中心性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miike,2003)
除了miike所提出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
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 总结 (chen & starosta,2003):
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在认识论上,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如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法”(dharma)的、中国“道”等境界。
二、基本理论架构
(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
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
第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时候,“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
第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来看,传播是一个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
第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
第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的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
第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洲传播的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个人的传播活动能够增进宇宙或者人们之间的和谐程度,那么会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会受到批评。而且,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chen,2001),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由这五大理念直接导致一些关于传播的假设(miike,2002):第一个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第二个假设是在多情境下,传播者在认识和行为两个方面既是主动又被动。第三个假设是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有核心价值。
(二)核心概念和模式风格
对于一些新的理论主张来说,概念是如此重要,因此最初对概念建构的力度是最大的。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亚洲”或者“亚洲中心”(性)必然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围绕“亚洲”概念,亚洲中心论有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等(miike,2002)的五大得到较多共识的核心主题。上述五个核心主题自然成为核心概念,围绕这些主题或与之相关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式:
比如中国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面子”、“气”、“占卜”、“缘”等概念 (chen & miike,2006),这些概念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解释中国传播行为的特点,而且这是其他传播理论做不到的。
陈国明尝试依托这些概念来发展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 “报/互惠”意味着一种相互往回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具有超时空效力,当然“关系”意味着比互惠更多的东西,它们总是指向和谐。“客气”指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所保持的一种忍让克己的态度,有时是一种尊重,这涉及“面子”问题,其目标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必备的“礼”仪。“风水”、“占卜”和“气”都是为了妥善与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诸事顺利,以达致和谐之境。
还有日本的enryo(谦虚、客气、保留)和sasshi(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恭敬)、amae(小孩撒娇式的依赖感)、awase(与他人相互适应协调)、sunao(正直服贴)、kotodama(言语和文字不可思议的灵力)、(ne)mawashi(非直接表达)on(恩报)、en(缘)等概念(chen & miike,2006)。
比如kume(1996/1997)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的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并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集体决定。
除了上述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核心概念外,亚洲各国都有很多核心概念可以被整理出来,并有很多概念都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传播理论模式。比如印度的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e)、语境(praka-rana)等(dissanayake,2003)同时对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也能够获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伴随这些理念和概念体系的是对某些特殊亚洲传播风格的描述:直觉式感知、同情的、安静或沉默、内敛与敏感的。(chen & starosta,2003)
(三)研究路径与实绩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 中国 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 文献 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第二,从传统经典文本和 现代 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第三,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比如容世诚(2003)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就对海外的一些中国剧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但却是在人类学框架中。
第四,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怎么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 历史 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陈国明、starosta、dissanayake、ishii等人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lili shi(2007)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各种比较研究非常重要,也较多。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2007)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
三、评论与思考
(一)批评与质疑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风险,面临许多的陷阱,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相关概念的含混。
“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等概念往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或者某种西方“霸权”等东西。虽然miike(2002)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主义”定为以亚洲人们作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精英中心意识取向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导致这个概念可能最终失去其区分能力和理论活力。
另外,“亚洲中心”的“亚洲”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概念。starosta就认为“亚洲传播”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话题(chen & starosta,2003)。因为亚洲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是如此之多,地区的之间的不平衡非常严重,导致“亚洲”对于很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都是过于抽象和空洞。虽然,陈国明与starosta(2003)从本土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亚洲的潜在统一性,但是却不一定能够代表“亚洲性”。在亚洲的差异性比共性更加显著的情况下,使用“亚洲”概念无疑充满风险,可能导致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的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掉进“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的“陷阱”,把亚洲置于一种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成为西方的异域镜像和永远沉默的他者存在。
还有“传播”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并未最后认定,大部分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此概念充满争议,还处于活跃的扩展、深化过程中。(shepard & striphas,2006)miike(2003)指出我们还未在亚洲语境中思考过传播,他本人确实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miike,2004)。但是,至今传播研究亚洲中心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探讨还非常欠缺,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远未得到阐明。
其次,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理论质疑。
chu(1986)认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要面对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问题:即在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普通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态度之间的差距和裂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被提出来,就是理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可观察性。从更大的方面的来看,这还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普遍性和文化特性的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要面对一个老问题。wang和shen(2000)就指出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求是对一个理论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这个甚至已经超出“亚洲性”的要求对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亚洲中心论”并不预备(也不能)在亚洲取得某种统一性或者一般性(miike,2002)。
dissanayake(2003)也指出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亚洲传播理论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其主要针对亚洲传播理论可能会拘泥于一些古老概念而忘记其历史性,这在某些时候确实值得注意。另外一种批判也与本质论相关,就是东西方极端二分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东方不是单一的,西方对东方的近代影响随处可见,两者有时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甚至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传统的地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建构或者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努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褒扬,但是在当代反人文主义思潮中,就成了一种“合法”的指责。实际上新文化思潮主要的标靶是欧洲的“个人化”人文主义,亚洲的人文主义内涵不尽相同且更加复杂,这种批评看来会无的放矢。
dissanayake(2003)还认为需要对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研究、更多的介入大众传播研究、进行更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上面的问题或者挑战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范式转换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是否需要效度或有用性评估等等一系列更加更本的问题。(miike,2000)还可以加上理论是否必须是普遍的?我们是否非得按照西方知识学的标准来判断?“亚洲中心论”者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挑战这些更加终极的问题。
(二)思考与结论:走向传播伦 理学
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 发展 起来的一个分支方向,主要由一些身份特别的研究者(其核心成员都具有亚洲背景,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组成的一个规模较小而集中的研究场域(从他们的交叉引用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种情况导致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想像亚洲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和研究者都是亚洲人,来自亚洲各地,中国、日本、印度居多。他们多是长年在海外求学教书,比如miike、陈国明等人,或者在亚洲任教也接受了多年的西方传播学的训练,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他们的主要成果发表在西方相关杂志上),比如ishii。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其所主张的“亚洲中心主义”既有对美式传播学的“接受疲劳”,无疑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反弹意识在里面,但由于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只有“亚洲”才能够为这种主张提供某种空洞的共同性。在面对真实亚洲那难以把握和归类的差异性时,对于他们来说,亚洲注定是想像的。比如,由于加入这种“亚洲中心”讨论的西亚学者的缺乏,导致这个“亚洲”并未把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视野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
而作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受东西方二元固定思维,其“亚洲中心”的提法将使之难以真正和种族主义、东方学等话语划清界线;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和界定自有其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导致亚洲更加容易被整体化和刻板化为一个沉默的想像物。
第二、理论创新与研究实绩薄弱
源自跨文化传播既赋予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相对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在传播理论研究上向纵深发展,去进一步关注传播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在上面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关系问题上、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等必须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亚洲中心”主张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miike对理论建构西方范式的根本性质疑到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chen & miike,2006)。而dissanayake(2003)所指出的本质论倾向和东西方二分的问题也是理论建构方面保守和缺乏活力的表现。
另外研究力量的薄弱,没有引起传播学主流研究群体的注意,也导致在面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力不从心。比如,当前大部分人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元理论和一些传统概念的阐释过程,那么应该同步进行的对传播本身的亚洲意义和理解问题、对相关概念和亚洲各国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传播行为、传播心理和传播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实证研究 自然 就比较缺乏,更加不要说相对困难的特殊方法论思考与探索。而且,对于夹在文化中间的研究者来说,视野可能要多元些,但也可能导致其既不太了解族裔国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进行讨论和对话,结果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寥寥。
第三、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
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或者缺陷,是不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呢?其实不然,一直以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被当作欧洲中心的)占据传播学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潜力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个正在“凋零”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想像亚洲(实际并非亚洲独有,也没有这样一个同质化的亚洲),因为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作为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者中和剂而寄予了厚望,许多研究者希望在亚洲能够寻找到带来新灵感的思想资源,亚洲传播研究或者“亚洲中心论”背后实质的内涵就是传播伦理学,是源于一种求知创新的热望,只不过这种传播学发展的新方向借由“亚洲”的名义得到了彰显(或者是亚洲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传播学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虽然传播伦理并非专属亚洲传统,却是在亚洲的各种主要思想传统中表现的最突出;也恰恰在东西方的二元对比和历史性关系中亚洲的道德性等到了强调,亚洲的一些传播理念、方式和风格看来能够有效的弥补西方过分强调线性传播效果的不足。
现在来看,miike提出(2002)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五大主题,并由此衍发的五大亚洲传播理念无一不是从伦理角度来考虑传播的问题。比如miike(2004)指出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这种同情式的传播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
陈国明就明确的指出亚洲的传播行为强调三种道德特性:互依、尊重和诚实。(chen & starosta,2003)陈国明还提出了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这里的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亚洲的一些思想传统和传播特色确实能够为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放下“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主义”这样过于沉重和含混的概念,通过传播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大胆创新,把亚洲的各种语言、宗教、智慧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扬光大。
首先,应该通过对传播思想的重新追溯,结合亚洲一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全面探索传播的意义,尽力丰富“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搞清楚传播现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才可能调动一切的思想资源为深入发展传播学服务,包括亚洲的或者欧洲的,历史的或者现代的。
其次,传播伦理学既是传统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又是一次革新意义的范式转换,应该有观念、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全面改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miike(2000)对欧洲中心式“理论建设”和知识基础提出彻底的质疑,全面思考创建新的“游戏规则”和对话原则。那么,亚洲的思维方式、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文化思想和传播理论和一些来自它学科的知识将为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与传播相关的现实和问题,让问题牵引研究的视线和注意力,这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重要的动力源。亚洲还有许多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混杂地区都会成为很好“样本”和“媒介”,为理论转变提供足够新鲜的灵感、素材和舞台,当然这些研究不惟实证,方法总是多元的,特别在面对混杂的现实问题,方法是综合甚至的对照式,需要足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