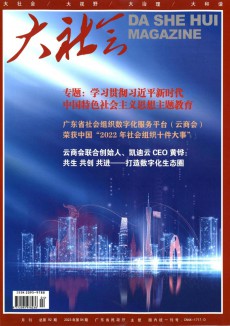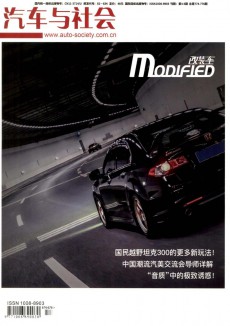社会类型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11-05 14:33:38
社会类型论文篇(1)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社会类型论文篇(2)
(一)紧跟潮流,适应大众旅游时代
自2016年“两会”之后,旅游业首次整体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推出,更多人瞅准机遇,将旅游作为日常所必备的生活方式。可见,旅游业即将成为当下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专业应当紧随潮流,有必要引入一些科学的理论,构建一套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的理论体系,从各方面进行理论规范行为,使之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地服务于旅游社会实践。
(二)迎合当下,匹配人才市场需求
随着旅游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各部门对旅游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了餐饮、酒店、交通、邮电等第三产业的各个部门,甚至还会依赖第一、二产业的产业链。如此庞大的综合性产业,需要应用型人才去规范、整合和管理,因此,旅行社、景区、旅游规划公司、旅游管理部门以及新兴的在线旅游平台等旅游企事业单位对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激增。这就需要高校能培养出应用技能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此外,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在培养学生应用技能过程中对这些基础学科理论的运用必不可少,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培养出匹配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主要学科依据
(一)旅游管理的人类学理论基础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生物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体质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体构造和人的生理特性,通过对某一群体身体特征进行解剖,探讨人类的起源、分布、演化和发展。文化人类学是通过对某一民族行为特征及其接触的实体做出判断,进而揭示该民族人类文化的本质。而当下旅游拓展“六要素”――商、养、学、闲、情、奇无不处处体现人类学的学问,旅游者不再满足于饱览山水景色,而纷纷开始关注异域文化,凝视异地民族人们的相貌体征、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等,并从中探寻历史足印,来达到扩大认知、寄托情感、探奇求异等目的。
(二)旅游管理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包括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和主观事实的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而旅游显然既是一种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更是一种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旅游管理正是对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进行标准化,以及对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学理论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是旅游发展的基础,经济发达的程度越强,意味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旅游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党的“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会给旅游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因此旅游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作为一门学科,旅游管理需要与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如旅游经济学正是二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学问。经济学理论也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
(四)旅游管理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需求按阶梯一样从低至高按层次可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既能使精神愉悦,又能促进人际交往的健康方式――旅游,它既能带给人们自信、愉快的心理体验,又能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还能拓宽眼界,强化自我概念和自尊,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旅游管理无疑要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使学生能从旅游者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进行旅游项目的策划和营销。
(五)旅游管理的文化学理论基础
休闲作为一种现实存在,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并由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历程和所抱有的生活理想而确立起来的文化样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休闲旅游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文化是旅游的环境,旅游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载体,没有附着文化的旅游行为是没有灵魂的行走过程。因此,旅游管理学科中的规划方向、设计理念、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无不需要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文化学为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
社会类型论文篇(3)
在中国,类型研究与社会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是决定类型研究兴衰沉浮的关键因素,类型研究的变化与转向往往也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反映与折射。类型研究与社会发展的镜像关系导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类型研究具有不同的面貌。
]
一、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从1905年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诞生之后,就开始了类型化的征程。早期的中国电影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商业竞争的状态,在市场的调节下,同时也是在欧美商业电影的影响下,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喜剧片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了明显的类型化趋势,形成了中国商业电影的第一次浪潮①。正是在这次浪潮中诞生了一种中国独有的电影类型——武侠片。类型化的创作潮流为类型片的研究萌芽提供了条件,但早期的类型研究是印象式的、感性的,散见于各种报纸的影评文章,缺少理论性和系统性。与西方的类型研究相似,自发的商业状态使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注意到了电影的类型化与观众需求的关系。郑正秋敏感地指出:“观众的要求决定了影片的艺术水平和质量,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会迎合观众的要求,进行创作,造成模式化。”②青苹注意到观众对武侠片类型化的促进作用,他尖锐地说:“就剧材与摄制言,现今国产电影之趋势,不能不偏重武侠一途,阙故何在,盖编剧者之选择材料,每观看客之心理为转移,故为公司设想,不得不稍改弦易辙,迎合观众心理,以求营业之发达。”同样,金太璞发现神怪片流行的原因正是为了满足观众窥视秘密的需要。他说:“简单的解剖神怪片可以说就是公开的秘密,把秘密的东西公开出来当然是人人所欢喜的,所谓愈秘密愈使人怀疑,如果能够现在眼前,当然有人会欢喜的。”而对古装片的盛行,评论者也从观众希望更换口味的角度给予解释。陈趾青说:“常吃一样菜,必定要改改别的菜换换胃口,摄制古装影片,就是要替观众换换胃口……影片之于观众,亦犹之菜蔬之于日常生活,胃口总要常换才对。”
参见青苹《从武侠电影说到<火烧红莲寺>和<水浒>》、金太璞《神怪片查禁后》、陈趾青《对于摄制古装影片之意见》,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7、666、639页。
与西方的类型研究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萌芽于20年代晚期,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使任何研究都脱离不了这个时期特有的时代命题。所以早期的类型研究大多津津乐道于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对当时盛行的武侠片、滑稽喜剧片、古装片往往评价不高。
类型电影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惜的是,1931-1949年,社会持续动荡和连年的战争打断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的进程。其中1931年的“9#8226;18”事变和1932年的“1#8226;28”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振兴国产影片促进电影进步为号召,以变革和创新为核心的新兴电影运动(又称左翼电影运动)走上了历史舞台。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该协会宣称:“我们必须亲切地组织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来探讨未来的光明,来扩大我们有力的电影文化的前卫运动,来建设我们的新的银色世界。”
《电影文化协会积极进行》,《晨报#8226;每日电影》1933年3月26日。
随后,夏衍、王尘无、唐纳等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加入使这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电影,宣扬革命的电影观,希望通过电影来推动社会的变革
有关新兴电影理论的论述,参见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78页。
。1937年到1949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爆发,中华民族始终在硝烟与战火之中挣扎,这使电影理论只能聚焦于民族危亡、团结抗战等社会政治问题,相比之下,类型研究在当时显然是无足轻重的。
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阶段的电影研究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拒斥早期的电影类型如武侠片、神怪片的存在,因此新中国17年间的类型研究不是建立在20年代类型研究的成果之上,而是将早期类型研究成果悬置起来,致力于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类型理论。类型电影在好莱坞是商业电影的代名词,是满足观众的工具和好莱坞的经济保险政策,而当时完全处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电影不是以取悦观众为目的,而是以宣传国家意识形态、教化民众为己任,好莱坞的类型理论显然不能适应新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时冷战时期的政治氛围紧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得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可能借鉴好莱坞的类型理论,而只能参考苏联模式。因此这个时期的类型研究是在独特的理论话语即“题材与样式”(来源于苏联的体裁诗学)的概念下进行的。“题材与样式是‘十七年’电影创作中的两个重要概念。题材是就影片的内容而言。‘十七年’电影创作上的一大特色是进行题材规划,其要点是先确定影片的主题,然后围绕主题来编织情节。主题是第一位的,情节为主题服务,直接反映国家意识形态,按照表现内容的不同,可细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反特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等。……样式则是指影片的表现形式。……这一概念是个舶来品,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文学与电影创作中引进的。‘十七年’间,除了惊险样式以外,还有喜剧样式、史诗样式、正剧样式等。”
关于类型与样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胡克一语道破:“类型与样式的区别在于,题材和样式基本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观念,意味着由行政部门代替观众决定应该看什么电影,按照计划安排生产。类型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由观众自己选择电影,被多数人反复选中的影片模式,就形成特定的电影类型”
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郦苏元也谈到:“类型与样式不是一个概念,然而其内在联系显而易见。影片样式的不断创造和逐步完善,有利于形成电影的定型化创作和规范化生产,从而推动了电影类型化进程”
郦苏元:《当代中国电影创作主题的转移》,《当代电影》1999年第5期。
。新中国17年,喜剧片、革命历史片、惊险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对惊险片的探讨尤为突出。首先表现在对惊险片这个样式的识别上。对于什么是惊险片,惊险片有哪些特征?钟惦棐、罗艺军等人先后做出了回答
参见钟店棐《影片〈智取华山〉的惊险样式和它的表演艺术》,《戏剧报》1954年第1期;艺军《关于样式的多样化》,《电影艺术》1961年第6期。
。其次表现在电影批评中的样式意识上。白景晟强调,要从样式的角度去评论电影:“很多同志谈论惊险影片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种影片样式方面的特点,往往用一般对待‘正剧’的要求,去评价、衡量这种影片,因之常常会混淆了问题的性质,得不到准确的结论”
白景晟:《惊险影片中情节和人物的二三问题》,《电影艺术》1961年第6期。
。羽山认为“我们在研究惊险样式时,有必要谈谈这一样式和别种样式的不同之点”
羽山:《惊险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电影艺术》1962年第1期。
。钟店棐则把样式提到了另一高度,认为不懂得电影的样式,就无法正确地欣赏电影艺术
钟店棐:《怎样看电影——致黑龙江的电影爱好者》,《黑龙江文艺》1956年第4期。
。这个阶段中值得一提的理论成果是羽山《惊险电影初探》一书,该书对惊险样式电影的艺术特性、人物塑造、情节以及艺术结构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惊险片样式研究的上乘之作。该书于1981年正式出版,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本书于1961年就已经完稿,后因政治运动,18年后方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面世,因此本文将其作为60年代的研究成果。
1966年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据姚晓濛统计,“”刚开始的三年,即1967-1969年中,中国只生产新闻纪录片,没有一部故事片问世。1970-1972年间,中国电影的成就仅仅是把八个样板戏搬上了银幕。从1967-1972的六年中,中国一共拍摄了17部电影,其中主要是样板戏电影。1973年开始,中国各电影厂才恢复拍摄故事片,但这些故事片仍遵循着样板戏电影的“三突出”原则
参见王土根《无产阶级史/叙事/意识形态话语》,《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
。十年,电影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9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类型研究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重大转折,主要表现就是对类型电影的娱乐性进行了大规模讨论。改革开放初,刚刚打开国门,外国以及港台电视剧和录像带对电影观众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了走出市场困境,拯救这场观众危机,1986年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对娱乐片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明确提出要“研究类型电影”,于是“为娱乐片正名”的讨论下进行的类型研究拉开了序幕。由于中国自身的类型研究一直没有形成有深度的系统的理论,而对娱乐片的研究又迫在眉睫,因此电影理论界选择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直接引入西方的类型理论,于是以《世界电影》杂志作为主要阵地,对西方的类型理论进行了翻译介绍
参见[美]达德利#8226;安德鲁《评价——对于类型和作者的评价》,彬华译,《当代电影》1988年第3期;[美]查#8226;阿尔特曼《类型片刍议》,《世界电影》1985年第6期。[美]维维安#8226;索布切克《类型影片:神话、仪式、社会戏剧》,《电影新作》1987年第2、3、4期;《时尚影片与类型影片》《世界电影》1985年第6期;《美国类型影片选》,《世界电影》1984年第2、3、4、6期;[美]爱#8226;布斯康布《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世界电影》1984年第6期。
。西方类型理论果然成为国内学者论证娱乐电影正当性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如贾磊磊《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抉择》,《当代电影》1989年第2期;郝建、杨勇《类型电影与大众心理模式》,《当代电影》1988年第4期;宫宇、蔡光《正名:类型电影作为艺术》,《当代电影》1989年第5期。
。然而这个时期国内学者对西方类型理论的运用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经过了有意的改写,故意“隐去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用来正面论证娱乐片的价值和社会作用”,以此来“帮助大陆电影界了解西方商业电影成功的诀窍”
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国内学者在这个时期对西方类型理论的翻译与介绍主要局限于西方早期的类型理论,对西方后期的类型理论大都敬而远之。直到新世纪,这种状况才出现改观,西方类型理论的引入不仅为娱乐片的正名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参照、提供了新路径,启发中国学者去探索自己的类型电影。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的是姚晓濛,他率先将中国的武侠片与美国的西部片做了比较研究,认为武侠片就是中国自己的类型电影,但这个论断在文章中由于缺少细致的论证而停留于简单的比附,文章并没有在类型研究的角度上对中国武侠电影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参见姚晓濛《美国西部片与中国武打片之比较》,《当代电影》1985年第1期。
。而这方面的缺陷在以后陈墨与贾磊磊等人对武侠片的研究中得到了弥补。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界的状况相当复杂,曾有学者用主旋律电影、娱乐电影、艺术电影三足鼎立、三分天下来形容。这种复杂性在类型研究领域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类型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及领袖、革命英雄人物的传记片为主)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这种互动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与电影市场化、商业化的双重加强,这种一仆二主的状况使得主旋律电影不得不自觉地采取了类型化的策略,主动去借鉴类型电影的经验,试图将国家意识形态与娱乐融合在一起。这种特殊的现象为类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即分析和论证主旋律和类型片互相成就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在这方面,尹鸿对“主旋律”电影、饶曙光对“新主流电影”、贾磊磊对“主流电影”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伦理化倾向,参见尹鸿《在喧哗和骚动中走向多元化——90年代中国电影策略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世纪转型时期的历史见证——论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关于新主流电影,参见饶曙光《关于当前电影创作的思考》,《当代电影》1997年第1期;饶曙光《论新时期后10年电影思潮的演进》,《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饶曙光《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主流电影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贾磊磊《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与价值体系》,《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二是类型研究中后殖民话语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戴锦华、张颐武、王一川、王宁等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开始将后殖民主义理论应用到电影批评上。他们以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创作实践为对象,运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电影的“他者”地位,表达了对第三世界中国电影处境的担忧,以及回归民族性的美好愿望。其中,张颐武从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对类型影片进行了学术分析。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充满了跨国文化经验的类型电影,这些电影都是将故事置于全球联系之中,力图将中国的事态放在国际性的问题中。张还对警匪片、滑稽喜剧片以及黑社会影片等做了具体分析,进一步指出好莱坞电影是以示范作用支配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中国类型电影往往试图以独特的本土方式即创造一种有关“发展”的想象,来模仿好莱坞电影的形态
参见张颐武《发展的想象——1990—1994年中国大陆类型电影》,《电影艺术》1999年第1期。
。
在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好莱坞给中国电影带来更为强烈的冲击,《电影艺术》杂志2000年第2期的首栏标题就以“面对WTO增强中国电影的竞争力”来命名,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巨大考验也使得理论界对类型电影的研究日益重视起来。2005年恰逢中国电影百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国内理论界也展开了对中国电影的总结与回顾,先后出版了若干专门研究类型电影的专著,这些专著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中对西方类型电影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全面介绍与分析,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聂欣如的《类型研究》;郝建的《影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沈国芳的《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郑树森的《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另一类是探寻中国本土的电影类型的生成与流变,如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吴琼《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总之,中国电影史上一切可以利用和开发的类型资源都尽可能地被梳理出来,武侠片、喜剧片、惊险片被重新认识与评价,重新确立了类型电影的地位和价值,营造出类型研究的繁荣景象。
]
二、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演进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的研究旨趣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过几次转变:
首先,从重实用、重实践走向学术化、专业化。中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往往期望理论能够直接用于指导电影的创作实践。郦苏元曾断言:“中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就其形态和实质来说,基本属于实用理论。它偏重阐释一般原理,普及电影知识,介绍创作方法,传授摄制技巧,以帮助人们了解电影并进而掌握拍摄影片的具体操作步骤与方法。”
⑤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陈犀禾也有过相似的论断:“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而轻视思辨的民族,从孔子到庄子都视思辨为无用有害之物,这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的精神,……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精神也同样影响到了电影理论领域”论文写作
陈犀禾:《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载《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作为电影理论研究一部分的类型研究也自然地染上了偏重实用、偏重实践的色彩,早期对武侠片、古装片等类型化电影的研究比较注重从导演、剧本、演员、摄影、布景、服饰、道具、化妆等具体制作方面入手来分析影片的优劣得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当时就有人敏锐地指出,滑稽片的要害是喜剧表演人才的缺失;历史片、古装片中布景和服装因缺少相关的历史考证而随便杜撰;武侠片中武打演员在表演上对京剧程式的模仿与抄袭等参见蕙陶《〈火烧红莲寺〉人人欢迎的几种原由》、冷皮《王氏四侠》、碧梧《看<金刚钻>试映后》、映斗《神怪剧之我见》、罗树森《摄制历史影片的研究》,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53-678页。
。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一是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学以致用”的思想传统,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明末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以至清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无一不体现出对理论的实用性的重视
参见张绪山《我国传统“学以致用”观是非论》,《光明日报》2005年4月26日。
;二是由于电影理论家大多直接参与电影的创作,当时的一些杰出人士,比如顾肯夫、郑正秋、洪深等人都是既从事理论研究又亲自参加创作实践,因此早期的电影理论往往是对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思考⑤;三是由于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缺少相关可利用的理论资源,与中国的类型研究明显不同的是,西方早期的类型研究因借鉴了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的成果而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深度,而中国早期的类型理论却一直缺少理论的观照,因此始终没有形成对类型电影的深度把握,理论资源的缺失导致我们的类型研究不得不沦为经验上的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类型研究出现了学术化、理论化的倾向,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学术氛围比较自由,如果说早期的中国电影类型研究承载着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新中国17年的类型研究肩负着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
1942年,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51年,周扬发表了《坚决贯彻文艺路线》,从此,“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出新的人民的这种新的品质,表现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这是目前文艺创作上头等重要的任务”。参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则逐渐被放回到学术领域。二是西方类型理论的影响。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研究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电影理论,在短短的数年内补齐了西方数十年积累下来的电影理论,作者论、类型研究、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成果都被全面翻译介绍进国门。西方类型理论为中国学者们带来了认识中国电影的新角度,让他们发现了新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本土的类型研究,使传统的重实践、重实用的中国的类型研究开始出现学术化的倾向。
其次,从注重社会教育功能走向关注娱乐功能。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电影通常被视为启发民智的媒介、通俗教育的工具、改良民风的利器,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早期的类型电影也被赋予推动社会进步等历史使命,因此这个时期的类型研究注重社会教育功能。对于滑稽喜剧片,评论者大都强调喜剧片的作用不是简单地让观众发笑,不能用无理取闹来取悦观众,而是要通过笑来达到教育观众、讽刺社会、感化愚顽、针砭时弊的目的
参见易翰如《滑稽影片小谈》、张秋虫《滑稽影片之价值》、罗树森《谈滑稽电影》、曹痴公《我对于笑剧的感想》,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677页。
;对于武侠片,评论者除了对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的武侠精神大加赞扬之外,还认为武侠片具有导世的功能,对恶人有威慑作用,对误入歧途之人有警醒作用,可以教导他们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因此有利于改良社会
参见姚庚宸《谈武侠片》、周素雅《论武侠剧》,嫠莺《武侠片的结构问题》,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671页。
;对于古装片的存在价值,有人认为古装片不仅能向世界宣扬中国古代文明,让西方人由此改傲慢为敬仰,而且可以教化民众,有造于民德
参见天笑《历史影片之讨论》,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页。
。由于早期的中国电影完全依靠市场运作,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使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出现了与西方相似的研究对象,即对观众的重视。但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对于观众的分析不仅是出于市场经营的考虑,更是出于教育大众的目的,郑正秋“营业主义加良心”
郑正秋:《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明星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版。
的创业主张正是这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典范,所以,对观众进行分类、分析观众的心理等研究更主要的目的是吸引更多观众走入影院,让更多的观众接受教育,更好地发挥电影的社会教育的功能。同样,17年间电影的教化功能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它与国家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宣传国家政策,教育与引导民众的重要工具。当时大量的战争片、反特片、喜剧片都是对新社会制度的歌颂与维护
参见黄会林《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当代电影》1999年第5期。
。然而,1986年的娱乐片大讨论展开了对电影娱乐性的艰难体认,类型电影的娱乐功能开始受到重视。《当代电影》1987年连载了题目为《对话,娱乐片》的三次讨论。这三次讨论涉及到了娱乐片的美学功能和特性、人类的游戏本能与娱乐片的关系、类型电影的基本规律和模式等。不久,《当代电影》于1988年12月1日召开了“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也已触及了娱乐片的类型规律。进入20世纪90年代,类型电影的娱乐性已经得到了公认,主要体现为主旋律电影的娱乐化,以及贺岁片的闪亮登场。新世纪之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大片时代,这种靠营造视觉奇观的大片更是对娱乐性的裸的追求。
最后,从学习西方的类型理论走向研究民族类型电影。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类型理论进入国内,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类型研究,甚至影响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创作。但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日趋强劲和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冲击,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本土的类型研究不能仅仅关注西方的理论,而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现实需求,正如《电影艺术》杂志2003年第4期的编者按中所说:“对于类型电影经验的总结,我们也多以美国经典类型电影为标准。这样的类型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对中国商业电影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总的看来,促进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我们希望此次类型电影研究是立足本土经验与东方经验的研究,是如何从我们熟悉的文化出发创作观众喜爱的电影的研究。”由此可见,强调本土经验,呼吁创建本土的类型电影,探索从本土文化资源和电影经验中寻找类型电影的创作规律,进行民族类型电影研究,已成为电影创作界与理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成为新世纪类型电影研究的主题之一。《电影艺术》2003年第4、5、6期连续对类型电影进行了专题探讨,这些探讨中既有对中国类型电影的经验概括,又有对类型电影的理性认知与学理把握;不仅有对具体电影类型的梳理,还有对具体时期的类型分析。所有的研究都出于同一目的,即对建构民族类型电影的呼吁。大家都认为不能完全模仿好莱坞的类型电影,要慎重借鉴好莱坞的类型经验。同时要努力挖掘本民族的类型经验,形成自己的类型电影。研究者们都意识到,中国的类型研究面临一个尴尬,即如何做到既不脱离西方的理论话语,又不脱离中国电影的独特经验;既不能用西方的类型理论来格式化中国的类型研究,又不能使中国的类型研究完全脱离西方的理论而成为自言自语?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从中国类型电影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中国电影类型作出具体的符合中国电影语境的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改革开放初,对西方理论的照抄照搬不同,如今的理论界已经有能力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且表现出要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决心和信心。而在民族类型电影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本土的独特类型——贺岁片无疑提供了有效经验。贺岁片的探讨成为我国类型研究的新领域,在新世纪,学者们对贺岁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对冯式贺岁片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更是成果颇丰。中国电影类型片应当如何打造自身的本土特征?王一川认为,冯式贺岁片的特征体现为团叙仪式、小品式喜剧、平民主人公、京味调侃及其扩展、二元耦合模式、想象的和谐社群以及时尚的泉眼等。而冯式贺岁类型片探索表明,只有着力建构鲜明的本土特征并形成成熟的艺术品格,影片才会既叫座又叫好
参见王一川《中国大陆类型片的本土特征——以冯小刚贺岁片为个案》,《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中国艺术研究院丁亚平研究员认为,从早期上海滑稽电影到建国后的影片,从《七十二家房客》这样的滑稽片再到近十几年来的贺岁片,这个历程可以视作本土主义的电影人或曰本土主义电影知识分子对于电影舶来品,或者西方话语、全球性的视觉形式,进行独特的阐释与对话、独到的本土化的建构过程。贺岁片的重要价值正体现于中国电影传统的接续、回位与复位上
参见杨晓云、周夏《“贺岁片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
]
三、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未来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的类型电影研究经过多年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经验与成绩为今后的类型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展望未来,我国电影类型研究的发展困境与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
一、目前,制约我国类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本土类型理论的缺失。西方的类型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的,关注类型电影的基本特性和文化意义,着眼于类型性(genreness)这个概念,即那些为所有类型所共享的形式和叙事的特征,以及它们与文化间的普遍联系
参见[美]托马斯#8226;莎茨《好莱坞类型电影》,冯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第二部分是对个别类型或类型电影的研究,主要针对各种类型电影的历史演进。而中国本土的类型研究恰恰缺少类型理论的部分,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就出现了类型化,但却因缺少理论的指导和观照,没有形成对类型电影的深层把握和系统的理论形式,从而丧失了形成类型理论的机会。改革开放后,面对类型电影研究的迫切性,理论界不得不实行拿来主义,直接引入西方的类型理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电影理论界彻底放弃了从本土产生类型理论的努力和希望。从此,中国的类型研究就大多只局限于一个研究领域,即对本土类型电影流变的梳理,成为西方类型理论在中国类型电影上的应用,中国类型电影彻底沦为西方类型理论研究的质料,而类型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方面,中国的类型研究几乎失语,没有发言权。
第
二、如何实现西方类型理论的中国化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西方的类型理论为中国的类型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有力促进了中国类型研究的学术化和理论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类型研究的发展。但中西方之间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这就导致西方的类型理论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类型电影。因此如何理性面对西方的理论资源,与它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大胆地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将其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结合起来,与中国具体的类型电影语境联系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将其与西方的类型理论进行对话与交流,实现互补互动,形成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构建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本土类型理论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第
三、中国的类型研究应关注一些世界类型研究中的共同问题,应该具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的类型研究作为世界类型研究的一部分,对世界类型研究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西方的类型研究从1948年诞生至今出现了几次转向。首先是从文本研究为中心转向以语境研究为中心。早期的类型研究主要关注类型电影的界定与识别,无论是最初的根据视觉符号来识别类型还是稍晚的以相似的叙事结构来划分类型,这些研究或者专注于电影文本内部的符号分析或者聚焦于影片文本的意义结构,都是在一个封闭的文本内部进行,是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随着好莱坞制片厂被一个更大的电影工业所取代,当代的类型研究逐步认识到以文本为中心的类型研究的缺点,于是出现了以语境研究为中心的倾向,越来越重视类型电影与工业、文化、观众之间的联系。其次,从注重类型识别转向重视类型功能。西方早期的类型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类型的界定和识别。最早对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相似性,从某些电影中寻找出相似的类型元素如共同的图像和视觉风格。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类型元素的混用、混列(bricolage)已经越来越普遍,以识别为主的类型研究显然对这种混合类型电影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于是类型研究慢慢地转向了对类型功能的关注,即试图回答类型电影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由此,类型电影对社会心理的反映与揭示、对观众愉悦需求的迎合以及类型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等一一被挖掘出来。最后,对类型研究从确信转向质疑。西方早期的类型研究实际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认为类型研究的有效性、适用性是确定无疑的。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研究者开始质疑类型作为好莱坞电影的研究方法的准确性,有人甚至提议应当放弃类型这个术语,建议用其他能更合理地描述全球化背景中的好莱坞电影的术语,如重复(repetition)、系列(seriality)、循环(cycle)、趋势(trend)、模式(mode)等
参见陈犀禾、陈瑜《类型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美]吉尔#8226;奈梅斯编《电影学入门》,陈芸芸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社会类型论文篇(4)
与1980年代大多数法律论者的研究相比较,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显然要深刻得多,因为他的观点和方法论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法律制度并不是一种自足的功能系统,因为它还在根本上受着某种由看法、态度、观念、意识、价值等构成的“文化类型”的支配。正如他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努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试想,没有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怎么可能有法制的现代化?但是,要改造我们民族的法律意识,就需要重新估价它,需要作一番比较的工作。而第一步,是比较和重新估价我们民族的文化。”[90]当然,梁治平强调文化类型之于法律制度重要性的方式,乃是我在上文所指出的那种 “文化类型”决定论。
正是根据这种“文化类型”对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或“决定论”,梁治平在下述个案的分析中指出:“比较的目的是要找出异同点,所以,不能一提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就以古罗马的家父权相比,只说上古社会家族观念发达云云,此外再无下文。在罗马,家父权只是单纯的法权,国、家不相混,法与道德两清。在中国,长幼亲疏被认为是永恒秩序,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律常常只是附加了刑罚的伦常。这种差异对两种法律制度乃至文化的发展,都有至为深远的影响。可见,只求其同,不见其异的排比、罗列是不可取的。总之,文化之整体的比较的研究乃是探索中国古代法精神的必由之路。”[91]当然,《法辨》一书中所收录的“法辨”一文,则可以被认为是他上述努力的最佳范例之一。在该文中,梁治平以西方“法”的概念作为比较的参照,对中国历史中“法”这个概念做了认真的辨析,并据此指出,中西历史上的“法”概念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观念。虽说近代以来论者们业已习惯用“法”这个术语来对应英文中的“law”,但是梁治平却认为,这只是一种翻译而已,因此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而必须进入到这些术语的背后去追究各自文化的根据。于是,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法”与“law”不同,因为在这些概念背后所隐含的中西有关社会秩序的观念和价值观完全不同。[92]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显然受到了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文化大讨论的影响,因为这两场文化大讨论有着一个共同的基调,即技术改革和制度改革都不足以应对中国的社会危机,惟有国民性的改变或文化的彻底变革才能使中国走出危机。他在“法制传统及其现代化”一文中指出:“试想,没有古代希腊罗马法观念的恢复,怎么能设想近代的《拿破仑法典》或《德国民法典》。反过来,印度、中国等东方古国虽有发达的文明,却不曾(我以为是不可能)产生罗马法意义上的法律体系,怕也不是偶然的。观念固然不能取代技术,但它客观上为技术的发展确定了方向,界定了范围。因了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二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者,没有不失败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也曾向西方学习。不过,最初只是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时的人相信,文物制度总是中国的好,并不认为西人的观念有什么优越之处。结果我们失败了。这样,到了‘五四’时期,才有了民主和科学的呼声。总之,虽然是技术,其发达与否还要看与之相应的观念怎样,进一步说,哪怕是学习一种技术,接受其相应的观念也是势所必然的。”[93]
毋庸置疑,梁治平这种以“文化类型”决定论为基础的“法律文化论”,确实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乃至中国法学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影响甚至在当下有关中国法律思想史或法律哲学的研究中还在延续。在我看来,除了上述业已指出的将有关法律的认识从“制度层面”推进至“文化层面”的努力以外,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还对当时主张自给自足“法律观”的中国法学产生了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法律文化论”经由法律制度与“文化类型”关系的建构而达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法律制度实是它无法与之相分离的更为根本的文化类型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他看来,“这里强调的只是各部分间的联系,还不是研究的方法。因为,用部分说明部分,只能在互为因果的圈子里打转,却不能深刻地把握部分。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的背景中考察,才能跃上一个层次,一下子抓住本质的东西。这个整体就是上文所说的文化,也不妨称之为文化体,文化结构。”[94]我认为,正是经由这一努力,那些被假设为“自给自足”的法律制度又重新融入了与文化类型这个不加区分的整体之中。因此,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不仅为打破当时中国法学视法律制度为一种自给自足或自我评价的东西的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为人们采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法律制度的问题开放出了某种可能性的空间。
(二)“参照”向“判准”的转换与西方“文化类型”的移植
一如前述,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是一种以辨异为基本路径的“文化类型学”。在这里,决定着法律制度之根本精神的“文化类型”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同质性,在理论上讲,为具体的研究者至少开放出了两种针对“文化类型”的可能态度:一是如吉尔兹那样走向对“地方性知识”的同情理解,在物理性的和功能性的“文化类型”中注入“意义”的维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可能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论者对吉尔兹等人类学家所主张的“文化阐释学”的引介,而毋宁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类型”或法律制度所做的这样一种具体设问,即具有整体性或同质性的中国“文化类型”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中国法律制度,对于选择这种文化或制度并在其间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显而易见,这种设问是一种自主的理论自觉的结果。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极其关键,因为它有可能使论者提出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制度如何发展的问题,或者说,作为一种“意义之网”的法律究竟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可能使论者自觉地意识到法律除了其功能相似的一面以外还具有因“生活意义”的不同而不同的另一面。[95]
但是,梁治平却采取了第二种可能的态度,亦即对中国“文化类型”持一种彻底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不是象吉尔兹所主张的那样努力使自己融入进这种“文化类型”当中去理解或解释这种“文化类型”以及由其决定的法律制度这种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意义或价值。不容我们忽视的是,梁治平的
这一取向乃是以他的论述当中所时刻隐含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为根本依凭的:中国的一些法律制度因术语的相似而真的与西方法律制度相同吗?中国的一些法律制度为什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归根结底,中国的“文化类型”在这个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中国的“文化类型”在面对西方“文化类型”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毋庸置疑,正是上述问题的设定,在根本上规定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论”中的两个基本倾向:一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辨异过程中将西方“文化类型”这一比较意义上的参照转换成评价意义上的判准;二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辨异以后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就“参照”转换成“判准”而言,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认为,“谈论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能不加入关于西方法的考虑;讨论中国法的现代化问题,也必须在这一背景下展开。”[96]因为在他看来,“现在最急迫的工作恐怕是,在大家都高喊加强民主与法制的今天,能有更多的人冷静下来,先去弄懂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法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它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应该怎样,法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法制社会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等等。这些问题关系到一系列新价值的选择,关系到对于我们民族新、旧传统的反省和重新评价,也关系到各种社会-文化目标的最终确立。任何一个民族,在它没有真正完全这些工作以前,是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的。”[97]
因此,梁治平在其研究中反复指出,“中国古代法源远流长,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持久的法制之一。排列整齐的法典,卷帙浩繁的文献,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法典无一不是刑法典,其他各种形式的法律也几乎都带有同样的色彩。这种单一性与中国古代法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久远的历史、浩繁的文献恰成对照。……这种现象怕不能以文化不发达、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等理由来解释,这毕竟是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它的法律传统差不多也同样久远),一个在17世纪时依然强盛的东方大国。这个事实促使我们变换角度来观察问题。这里,着眼点不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而是文化本身的类型或形态。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类型或形态从根本上决定着文化各个部分的性质和发展程度。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法并非不发达的产物,就其固有形态而言,它是发达的。而所谓固有形态,实际就包含在它的现实形态之中,这个固有形态,简单些说,就是把法视同于刑。” [98]当然,他在对中西法律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指出,“古罗马法学家分法为公法、私法两部分,着眼点正是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而在中国,法只能是 ‘公法’,辄与国家利益有关,因而也总是以国家强制力——刑为其标志的。”[99]
姑且不论梁治平对中西法律的上述描述在事实上是否确当,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论述并没有如当时的一般法律比较研究那样停留在事实描述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推进到了价值判断的层面。比如说,他指出:
自清末引入西方法制,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了。今日之中国,来自西方的先进事物不可谓不多,能够贴上现代化标签的东西也不在少数。但中国在完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仍有一段艰难的道路要走。当年,孙中山的革命虽然了帝制,但远远末能使中国的老百姓意识到他们是有权作自由选择的平等的个人,因而也就没有能在社会关系的领域完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如果说,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可以在革命的狂飙中完成,那么,真正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改变相应的价值观念,则远非一日之功。正因为如此,近50年来社会关系领域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与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适应程度,尤其值得我们反省。[100]
他在另一个场合也明确指出:
中国古代法中没有“私法”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推重身份的社会里,“私法”的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的发达与完备也就无从谈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发达并不就是社会经济运动的简单记录。观念也好,制度也好,都是塑造社会的能动要素。古代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固然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人际关系的普遍的“身份化”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甚至可以说,这种“身份化”的社会状态正是中国的近代落伍的重要标志之一。 [101]
显而易见,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中,从“礼法文化”到“私法文化”、从“身份”到“契约”、从“同志关系”到“契约关系”、从“律法”到 “法律”、从“道德之治”到“法治”等等,都已经从事实描述层面的“文化类型”辨异,转向到了价值判断层面的“文化类型”判断。换言之,“私法文化”、 “契约”、“法律”或“法治”等比较意义上的参照指标,转换成了评价意义上的判准,仅就“契约”问题而言,一如梁治平所指出的,“如果说,古代社会的法律可以是身份化的法律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法律的一般原则是排斥身份观念的。问题在于,现实生活的逻辑往往不受法律条文的支配,与一般法律原则相左的观念可能依然流行,甚至颇为发达。我们社会中关于身份的观念就是如此。所以,不管人们意识到没有,也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正是要以契约取代身份。实际上,近年来所有真正的改革莫不与此有关。……表现于其中的陈旧观念,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种社会状态,实在是很不现代化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或者,换句话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还须作出更大的努力。”[102]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关键在于,梁治平将辨异的参照指标,不仅转换成了评价中国法律制度是否适合西方现代社会的判准,实际上还进一步转换成了评价中国法律制度在道德上优劣的判准,这在他的下述文字中表现得尤为明确:“考虑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与西方法律文化性质相去实在太远,强调这种结合便不能不特别谨慎。法律与经验的脱节固然应予消除,法律与经验的协调却也不能是使先进的制度屈服于陈旧的‘国粹’。传统的法律连同相应的观念、心志,在总体上必须要彻底否定,因为其结构功能完全与现代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上面谈的,可以说就是文化的解决。”[103]
最为重要的是,就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而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所谓的中国“文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根据西方的“文化类型”加以型构或评价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根据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法律文化指出,“古代中国,私法无由发达,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之‘法’,根本与权利无缘,其固有观念不能容纳‘私法’的概念。”[104]显然,梁治平在这里是用一种以“私法文化”为依凭的西方现代“刑民法国家结构”或者“公私法国家结构”对以“礼法文化”为依凭的中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结构”的审视和评价,结果,不仅中国的法律变成了“刑法” [105],而且对具有独特意义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理解”也根本无由产生。这里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还是我在前文反复强调的那个问题:中国的法律文化在几千年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究竟对选择这种“文化类型”并生活于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梁治平本人在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所撰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事后性解释”文字,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本书曾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中国古代的‘民法’问题。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民法的学说和理论具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影响,它们不仅模塑了西方古代和近代的法典,而且深深渗入到西方人的思想和思维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在西方文化和法律传统中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没有对应物。这意味着什么?以往的学者着眼于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典’以及古代法典中‘民事 ’规定少一类表层现象,或谓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或谓中国古代法乃是‘诸法合一’(一种经常用来概括早期法典特征的说法)。这种主要(通常是无意识地)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的作法,没有例外要遮蔽对象物的自主意义,从而导致其完整性的丧失。本书认为,就其固有形态而言,中国古代法业已足够成熟,而根据其内在逻辑,不但民、刑分立缺乏依据,私法之说更是一种自相矛盾。”[106]
当然,梁治平将辨异的参照指标转换成评价中国法律制度或中国“文化类型”之判准的做法,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以西方的概念或观念为标准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关于这个问题,上文的讨论已然揭示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为了论证序列的必要性,我不得不在这里继续征引梁
治平的下述文字:
结果之一就是传统法制的西方化。说它西方化,主要是指法的技术方面,即成文法的西方化(广义上还包括法学理论以及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方式)。在这方面,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化”的先后、程度也不同。不过,现今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无一例外是这种西化了的法律。至于说到法律意识,恐怕还是传统的占优势。因为,长久形成的观念、意识较之表面的制度更不易改变,转变的过程也更多痛苦。但是,这一关看来是非过不可的了,毕竟,技术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东西,它总是与某种观念有关。[107]
在由传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的当儿,中国人不得不采用西方的法律制度,但这就意味着,它也要承认西方人的法律价值观……。对于中国人来说,改变现在的法制是相对容易的,通过一场革新或者革命便可以做到,但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环境,创造一系列与这种新的法制正相配合的文化条件,却是极其艰难的。[108]
自然,这里无须多谈中国古代法的失败命运……。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去寻找它失败的原因。但有一点是最基本的,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那就是,就其自身性质而言(如以上所谈种种),中国古代法实在不能适应这个新世界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法的传统应予彻底的清算。如是,传统问题遂以现代方式提了出来。[109]
经由中西“文化类型”的辨异和评价,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认为,中国“文化类型”以及由其决定的中国法律制度必须予以彻底的清算和彻底的否弃。在他看来,第一,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之所以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实是因为中国“文化类型”对中国法律制度的规定性或法律精神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和要求;第二,中国“文化类型”的整体性和同质性又在根本上规定了它的不可通约性以及它的变迁或修正的不可能性。正是根据上述两种基本的规定性,梁治平得出结论认为,欲使中国法律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以西方的“文化类型”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类型”,换言之,在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仅仅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并非足够有效,还必须彻底地移植西方“文化类型”。
(三)对“文化类型”决定论的分析和批判
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类型”及其与法律制度间的关系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法律文化论”的基本品格。因为正是透过对它们的认识,梁治平不仅意识到了中国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法律制度的文化根源,而且也因此获致了探寻此一文化根源的理论可能性。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梁治平所建构的“文化类型”及其与法律制度间的关系做一番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批判。
(1)众所周知,梁治平的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学”研究乃是以强调不同“文化类型”的根本区别并以重视“差异最大化”为基本特征的 [110];与此同时,这种研究进路不仅是以“文化类型”的整体性和同质性为理论前设的,而且也趋向于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文化类型”这个原本是梁治平本人为了分析而建构起来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同质性。因此,这种探究整体性和同质性的“差异最大化”的进路,自然而然会主张一种中西“文化类型” 以及由其决定的法律制度“不可通约”的观点。显而易见,这种研究进路及其主张的观点,根本就不可能对文化的历史流变、尤其是文化间“互动性型构”的问题予以关注并给出回答。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梁治平的研究进路并没有使他止步于此。一如前述,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认为,不同的“文化类型”乃是因他所认为的这样一个事实而形成的,即“正好比文明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一样,从属于不同文明的法律也各不相同。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释世界,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不同,据以行动的准则,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行为模式也大不相同。由这里,……产生了特定的文化样式。”[111]梁治平有关“文化类型”发生学的这一判断可以说是意义重大,因为他在强调人类生活共同性以及人类理解、对待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态度和方式不尽相同的同时,实际上还预设了一个“事实”和一种与此相关的可能性。所谓“事实”,在这里是指他所认为的由人类不尽相同的理解、对待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态度和方式构成的“文化类型”是可以选择的;所谓与此相关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指梁治平在“法律文化论”中反复强调的对这种文化选择进行批判的可能性,甚至对这种选择的“文化类型”直接做出替代的可能性。
正是梁治平关于“文化类型”发生学的判断及其所隐含的上述预设,在其具体的中西“文化类型”辨异并且以西方“文化类型”取代中国“文化类型” 的论证过程中,使我们最终意识到,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以另一项并不为人们所意识的更为基本的预设为支撑的,即人们既可以选择不同的 “文化类型”,也可以选择相同的“文化类型”。这项基设在根本上意味着:至少存在着一种可以被普遍化的文化可供我们选择,甚至是一种普遍的在道德上可欲的文化可供我们选择。毋庸置疑,这项基设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法律文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类型”以及由其决定的法律制度受制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其他因素的可能性,比如说人口、气候、地理、耕作方式、疾病等;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它使得“法律文化论”在根据西方“文化类型”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类型”的同时,实际上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实体存在的“文化类型”的意义,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与“文化类型”相悖的主张,即文化本身是可以普遍化的,而这种可以普遍化的文化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中则显然是西方文化。
(2)一如我们所知,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在辨异中西“文化类型”的过程中,始终采用了一种他自己认为颇为有效的方法,亦即一种语词分析的方法。他在“法辨”一文中明确指出,“语言总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这便是明证。把这个结论作为起点,可以展开更有意义的探索:由某些字、词的产生,字形、字义的演变、确定来把握特定的社会现象,再由表现于这些社会现象之中的历史、文化特质反观这些字、词的内涵,提供新的解释。”[112]当然,梁治平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实是与他强调语言或语词与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法律制度之间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假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如他所言:“我假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假定一个民族的语词浓缩了这个民族的经验,以至人们可能沿着语词的轨迹追溯乃至再现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113]
的确,这种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梁治平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一种惟有文献记录予以支撑的极为明确的东西,而是一种必须经由对各种材料的不同层面的分析才可能认识或理解的极为复杂的东西,亦即一种“鲜活”的历史文化,而非一种“僵死”的历史遗物。因此,仅试图透过对“法”、“律”、“刑”、“治”“礼法”等语词的严格分析来揭示和把握这样一种具有几千年复杂的鲜活的历史文化,在我看来,其结果如果说不是大而化之的,那也是特别概念化的,因为这种研究进路——其他的问题存而不论——根本就不会去关注也不可能去关注被这些语词的字义演变所掩盖的那一场场活生生的争夺字义解释权的斗争,以及因斗争的成败而可能被淹没的或遮蔽的那些具有生命意义的文化;比如说,在我看来,梁治平“法律文化论”根据西方现代“一元”的治理理念所建构的中国国家“法”及其背后的中国大一统的“刑”文化,就完全淹没了或者说在根本上无视了中国民间习惯法的存在所赖以为凭的中国人有关中国政治治理结构的“二元性”理念。
显而易见,梁治平的这种研究进路,一方面,因为其语词选择本身受到了西方“文化类型”的规定而只能够看到中国法律结构的“单轨性”,即中国 “文化类型”所决定的那种以“刑”为根本的作为“大传统”的中国国家法,而没有也不可能洞见到我所谓的中国法律结构的“双轨性”:在设定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安排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县级以下的作为“小传统”的习惯法安排。其实,梁治平本人在多年以后所撰写的一段文字,在我看来,亦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本书虽然多次谈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和互动,并且认为这一类关系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实际上却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严格说来,本书关注的基本是人类学家所说的‘大传统’,即来自国家的、统治者的和精英的文化传统,而非大众
的和民间的各种传统。应该说,在诸如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文化中,‘大传统’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同样明白的是,单由‘大传统’入手又是不够的。在诸如‘民法’这样的问题上,这种认识尤其重要。因为自唐、宋以降,中国社会内部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生活方面,出现了许多民间的交往形式。进入明、清以后,随着社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方面的发展更加令人瞩目。这种情形与国家法(首先是作为一种符号体系)的相对不变形成鲜明对照。而这可能意味着,对这一方面社会要求的满足主要是在‘小传统’中求得。”[114]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梁治平的这种研究进路,不仅使他无力洞见到上述中国法律结构的“双轨性”以及其间的作为“小传统”的中国习惯法,更是致使他意识不到这种“双轨性”的中国法律结构深深嵌入于其间的并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型构、接受、修正和完善的中国自己的独特的法律文化。再者,由于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所关注的只是论证中国“文化类型”如何不如西方“文化类型”以及如何以西方“文化类型”取代中国“文化类型”的问题,又由于他所建构的中国“文化类型”乃是一种中国人在其间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私”生活或“经济”生活的文化类型,因此在其设定的“问题轨迹”中,他是根本意识不到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予以一种“同情理解”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对下述问题做出追问的: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梁治平认为必须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文化?或者说,一如前述,这种在梁治平看来必须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生活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115]
(3)当然,在我看来,梁治平所主张的上述研究进路,实际上是与其在“文化类型学”的研究中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所贯彻的另外两种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一是我所称谓的“基因决定论”,另一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梁治平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反复指出,西方法律的当下发展方向,早就在其最早的“胚胎”中就已经决定了;与此同理,中国法律发展的积累,并不能够改变其原本的性质,因为惟有彻底否弃其原有的胚胎、移植进西方文化这一新的胚胎,才能使中国法律制度的改革发生性质的变化。正如他所指出的:
的确,注重刑法,刑罚酷烈几乎是各民族早期法律发展中都可以见到的现象,希腊、罗马法律也不例外。但是,只要稍稍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相似只是貌合,它们内里的精神是很不同的。在诸如古代希腊、罗马法的例子里,刑法的相对发达和严酷,连同法律部门的混杂、法律的注重形式和僵化等现象,都只是表明了一个文化的界限,即当时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较低发展程度,以及人类极为有限的认识水平。在这个时期,法律是幼稚的,它的成长而至成熟尚需时日,不过,就是在它最粗糙的胚胎中,未来的成熟形态也已隐约可见。所需的只是时间,和使文明得以正常生长的必要条件。自然,历史慷慨地提供了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罗马文化,不会有作为它的骄傲的罗马法了。至于上文所说的胚胎,它的重要就在于,不管它多么粗糙、寒碜,它毕竟包含着某些重要的萌芽,比如,把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虽然,这类观念最初只能是朦胧的、幼稚的,但它具有的那种包容性却是它的生命之源。中国古代法缺少的正是这种。它只是刑,是镇压手段,暴力工具,这种狭隘性排除了它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用来调整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统治者,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法律所及之处,没有纯粹的私人事务,一切都与国家有关,也就是说,它只能是“公法”,不能是“私法”。这正是中国古代法与希腊、罗马法的根本区别之一。这种区别产生于这些法的诞生过程中,早在它们各自的初始形态中就已基本确定了。[116]
与上述“基因决定论”相勾连,梁治平在“文化类型学”中还始终认为,任何法律制度都有着一种唯一且确定的“本质”,而且它发展或改革的成败也完全取决于这个本质本身的变革,中国法律制度也不例外。“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西方法则不能不是西方文化的表征。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 [117]于是,惟有发现这一具有决定中国法律“传统”意义的本质并且彻底否弃这一本质,惟有发现并确定具有决定法律“现代”意义的本质,中国的法律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其步入现代化的目标。当然,在梁治平那里,这个本质就是他所建构出来的那种“文化类型”。据此,中国法律欲实现现代化,仅靠法律制度层面的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文化类型”的解决。一如他所指出的,“清末的法律改革是一场文化冲突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试图克服这场危机所作的一种努力。正因为如此,法律改革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法律问题最终变成为文化问题。于是,我们不再专注于某一项具体的改革方案及其成败,而是更关心作为整体的文化格局,文化秩序。我们不但自觉地把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放入这种整体性格局中去考察和评判,而且寄希望于一种崭新的文化秩序的建立。”[118]显而易见,梁治平“文化类型学”研究中透露出来的这种“本质主义”,[119]实是一种极其僵化、封闭或专断的思维方式。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在本体论上不是假定“文化类型”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这种“文化类型”具有着某种超历史的、普遍的本质,可以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存在;最为根本的是,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还在知识论上以一种极其专断的方式设定了以现象/本质即“法律制度”/ “文化类型”为核心的二元架构。
毋庸置疑,梁治平所持有的“基因决定论”和“本质主义”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把中国文化建构成了一种具有“固定本质”的实体,而这使他无法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和讨论法学理论或中国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而只是先验地假定那些与中国法律实践史不涉的“问题”及其“答案”,并且认为只要把握了中国文化类型所具有的那种“固有本质”,便能够探寻到中国法律制度无法成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命门。显然,这两种思维方式不仅使他看不到中国文化及其所影响的法律制度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根本的意义,实际上也更使他洞见不到法律制度在从其文化类型中生长出来并拥有其自身的“生命”以后所可能获致的自己的丰富的生命逻辑,当然也无法意识到法律制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偶然性以及其他因素在整个的历史进程中对法律制度之实践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比如说,自然条件、意识形态、人口因素、其他相应的制度安排、经济等因素。[120]
我认为,梁治平有关“文化类型”及其与法律制度之关系的分析以及他的“辨异”进路,虽说与其他法律史或法律文化研究相比,获致了一种表面上的深刻性,实际上却掩盖了意义本身在其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中的全面丧失,甚至致使他走上了一条反“文化类型”甚至是反历史的道路。因为在他看来,“文化类型” 一旦生成便已经定型且根本不可能存在内部的差异、矛盾和裂缝,仿佛从中可以概括出所谓永恒不变的“本质特征”。显而易见,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类型”只能是一个虚构的“实体”,这个意义上的所谓“本质特征”也只能是一种虚构出来的极其专断的权力话语。
(4)一如前述,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那些将西方法律制度或概念与中国法律制度或概念随意比附的1980年代法律史的研究来说也构成了重大批判。但是,就本文的论旨而言,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却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一样,也受到了我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正如他本人所言:“是什么使得这一巨大转变竟在短短数十年里完成?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文化的,较直接但是最有力的则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上文曾提到过的现代化。现代化虽然是遍及世界的运动,最初却是由西欧起始的。这当然与几百年前西欧(首先是英国)的社会条件有关,与作为西方社会之普遍秩序的法律在当日的状况有关。这就决定了日后的现代化运动常常带有西方文明的色彩。19世纪所有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无不以大量吸收西方思想、制度为其开端和基本内容,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但是我们可以确证,现代社会的法律必定是西方式的
。”[121]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方式,在我看来,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式,亦即在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同时,直接把经验层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或价值转换成具有评价中国法律制度功效及其道德优劣之判准意义的理想图景。当然,这种方式完全可以见之于他的下述文字之中:“以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它(指中国的法制——邓正来注)注定不能够传世。这时,接受西方的法制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虽然在一定限度内,这种法律的内容会因时因地而异,但是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基本形式是确定的,不容置换的。当然,形式法律本身也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是包含了特定价值在内的形式。一种可预见性很强,能够象一台合理的机器一般运转的法律秩序,不但可以有效地保护契约的履行,商业的发展,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122]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方式,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走得更远,因为他不仅主张把经验层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转换成具有评价中国法律制度功效及其道德优劣之判准意义的理想图景,甚至还一如前述,主张把西方的文化都移植到中国来。
当然,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因受“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或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幅我在前文所说的那种“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法律/法制发展之方向提供一幅作为判准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法律文化论”之所以不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做法,在严格意义上讲却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上述基本取向所致,而毋宁是因为“法律文化论”这一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学”经由语词与社会结构具有同构性的假定、“文化基因”决定论或“本质主义”等思维方式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反“文化类型”甚至是反历史的倾向,在根本上规定了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实,更无力将中国的现实世界置于当下的世界结构之中做“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而只能把它的法律文化研究界定在法律史的题域中——尽管这种研究除了处理的是历史材料以外很难说是一种历史研究。换言之,在我看来,根据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中国所有当下的现实,在本质上早都由他所建构的中国固有的那种“文化类型”之胚胎决定了,而且关于中国现实的“答案”也完全可以从对他所定义的那种“文化类型”胚胎的分析中获致。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梁治平以语词与社会结构具有同构性的假定、“文化基因”决定论或“本质主义”等思维方式为支撑的“文化类型学”看来,任何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经验、或者各种因素间反复博弈的现象、当下制度于现实中任何创新的可能性,都是无关宏旨的,而且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实也是毋需予以关注和研究的。
正是由于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与“中国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所以它虽说在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题域中发挥过而且肯定还会继续产生我在上文所说的某种作用,但是就中国当下“立法阶段”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言,这恰恰又从另一个角度确证了“法律文化论”未能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给评价、批判或捍卫中国法律/法制改革或发展之方向提供一幅作为判准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就此而言,以上有关“法律文化论”的各种问题,与“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一起,当然也与“本土资源论”一起,构成了本文所强调的中国法学在这26年中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就“法律文化论”这一理论模式在“现代化范式”这一规范性信念缺乏有效质疑或批判的情形下依旧影响着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或法律与文化关系之研究的意义上讲,它的存在本身可以说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法学的“范式”危机。[123]
注释:
[1]关于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与其他论者的研究之间的区别,我将在后文的讨论中论及。
[2]梁治平:“后记”,载《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3]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的,主要是指《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本文集,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1991年出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一书。关于它们对中国法学的具体影响,我将在后文中论及。
[4]实际上,1992年出版的《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是一本文集,而其间所收录的乃是梁治平在80年代下半叶发表的20篇文章。因此,严格来讲,《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一书的撰写时间要晚于《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
[5]我之所以把时间限定在梁治平于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以前,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下半叶以后梁治平的研究成果甚少;即使他发表的或编辑的有关法律解释、形式法治和公民社会的文字,在我看来,也已经离开了他自己在1990年代下半叶以前所划定的“法律文化”的研究题域,而且他本人也不再尝试通过“事后解释”的方式把这些努力与此前的“法律文化”题域勾连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梁治平在1997年以后所做的研究,可以被视作是一些独立于此前的研究。
[6]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本文4·2节中对苏力“本土资源论”所建构的两条基本论述逻辑。
[7]梁治平:“导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8]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9]参见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II-IV页。
[10]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1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7页。
[13]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I-III页。
[14]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15]同上,第16页。
[16]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7页。
[17]“文化类型”、“辨异”和“社会学”在梁治平的早期和后来的研究中所导致的结果的区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追问,即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梁治平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这些被认为是同样的方法或研究进路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说,这些不同的结果是由其他的因素(而非方法或研究进路)决定的,那么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很显然,梁治平本人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任何解释。关于类似于此的问题,我拟在后文中展开比较详尽的讨论。
[18]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19]同上,第150页。
[20]同上,第16-17页。当然,梁治平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类型也持与此类似的批判和否定态度,比如说,他在该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虽然有久远的传统,而且自成体系,但如果以‘形式的或者经济的’期待‘(expectation)来衡量,它却是不尽合理的’。更重要的是,一向决定着中国法律发展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中国古代法发展趋向本身,都是与形式法律的发展背道而驰的”(第360页);当然,他紧接着又指出,“的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清末的法律改革是一场文化冲突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试图克服这场危机所作的一种努力。正因为如此,法律改革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法律问题最终变成为文化问题。于是,我们不再专注于某一项具体的改革方案及其成败,而是更关心作为整
体的文化格局,文化秩序。我们不但自觉地把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放入这种整体性格局中去考察和评判,而且寄希望于一种崭新的文化秩序的建立”(第361-362页)。
[21]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7页。
[22]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V页。
[23]就公开发表的文字看,根据我的阅读范围,除了苏力所撰写的“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一文以外, 1990年代中期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曾经对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一文进行过讨论,但是与会的讨论者所关注的大都是这篇论文本身的问题,而甚少有论者就他的这项研究与其此前研究之间的关系做出过评价和讨论。我在此次讨论会上指出了梁治平研究中的从“大传统”向“小传统”转向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请参见 “中国法律史上的小传统及其意义”,载《中国书评》(强世功整理),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出版社1995年总第7期,第69-75页。
[24]参见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载《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9页。
[25]需要指出的是,虽说苏力在这篇文字的结尾处还论及了梁治平在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正如他所指出的,其他一些研究进路“比文化类型学模式更具有弹性并更多考虑了时间维度,因此也更具解释力。梁治平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一些问题,在其新近出版的《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一书中,尽管仍然坚持《法律的文化解释》中强调文化类型和大传统的支配地位,但他已经更多地转向考察民间生活的小传统,考察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互动,实际上也就是考察文化解释的竞争。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成为他学术旅程上的第三次反思和转折的开始”(第58-59页),但是我认为,这尚不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说苏力对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一书中的观点也做出了有根据的评论。
[26]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载《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27]参见同上,第42页。
[28]同上,第44页。
[29]参见同上,第45页。
[30]同上,第45页。
[31]参见同上,第45页。
[32]同上,第44页。
[33]同上,第43页。在该文中,苏力还对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中所收录的“法辨”和“礼法文化”这两篇文章还做了一些分析。比如说,他指出,《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中收录的“法辨”一文是一个概念辨析的范例。通过对中国文化中“法”这个概念的细致的历史辨析,同时以西方“法”的概念作为对比的参照系,梁治平指出,中西历史上的“法”概念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安排秩序的观念。尽管近代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以“法”来对应英文中的“law”,但这只是一种翻译、中西交流的必需和不得已。在历史上,中国的“法”并不等同于“law”,因为在这些概念背后所隐含的中西世界观、价值观和秩序完全不同,尽管它们在功能上可能有某些相似。因此梁治平认为,用现代的、西方的“法”来套用、理解古代的“法”,实际上是在按照西方观念重新改造已经成为历史的中国法律制度。关于“礼法文化”一文,苏力认为,这篇文章探讨了在功能上起到“私法”或“民法”之作用的中国古代的“礼”为何在文化层面上不能概括为——如同某些中国法律史学者所做的或试图做的那样——“私法”。在梁治平看来,关键在于“礼”所代表的或体现的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对秩序的安排,中国古人的这一“意义之网”与现代人的“意义之网”是不同的。
[34]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VII页。
[35]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36]同上,第280-281页。
[37]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
[38]参见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XI页。
[39]同上,第I页。
[40]同上,第II页。关于历史学的方式,梁治平认为杨鸿烈所著《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是代表作。请参见同上,第41页。
[41]关于社会学的方式,梁认为瞿同祖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 年版)是代表作。此外,他还认为,另一部关于清代法律的杰出的社会学研究是Sybille van der Sprenkel所著的〖WTBX〗Legal I nstitution in Manchu China.〖WTBZ〗(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2)]请参见同上,第42页。
[42]同上,第II页。
[43]同上,第III页。
[44]同上,第VIII页。
[45]同上,第VIII页。
[46]同上,第X页。
[47]梁治平:“自序”,载《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8]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49]同上,第127-128页。关于这个问题,另请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页,第53、57、58页。
[50]关于梁治平在撰写《法辨》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时还没有意识到文化阐释学和哲学解释学的问题,请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后文所设的“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第364-385页。
[51]诸如“大传统”、“小传统”、“文化解释”和“解释学”这些对于“文化阐释”极其重要的术语,梁治平只是在1997年再版《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时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才加以使用或征引,请参见该书的“再版前言”,第I-XI页;又请参见该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第364 -385页。
[52]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53]梁治平:“死亡与再生”,载《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页。
[54]梁治平:“后记”,载《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55]梁治平:“法律文化:方法还是其他(代序)”,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56]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页。
[57]梁治平指出,“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是个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富于弹性。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大概不下百种,但没有一种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可以为所有人接受。尽管这样,大家还是用它来讨论问题,可见,其中总有些共同的东西。”《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1页。
[58]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59]同上,第13页。
[60]同上,“自序”,第1页。
[61]梁治平:“法律文化:方法还是其他(代序)”,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3-4页。
[62]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4页。
[63]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64]同上,第7页。
[65]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66]尽管梁治平指出,“法律文化所要研究的,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和态度。它要问,人们如何看待法律?他们是否愿意通过法院来解决纷争?法官们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他们实际上怎样判案?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怎样,与道德的关系又怎样?法在整个文化中居于何种地位?它有何种社会功能?它对此一社会中的成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超出一般法律制度史、思想史乃至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它要通过文化来阐明法律,透过法律来审视文化。其结果,无论它所论及的法律在它们各自社会与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怎样不同,这种研究本身却是同等重要的”(梁治平:“导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最终的落脚点仍旧在“研究”本身,而非所研究的法律文化所具有的意义或价值。
[67]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68]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II页。
[69]吉尔兹:“深描说:迈向解释的文化理论”,于晓译,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第276页。
[70]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71]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页。
[72]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X-X页。
[73]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1995年9月总第7期,第74页。
[74]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75]强世功整理:“中国法律史上的小传统及其意义”,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1995年9月总第7期,第74页。
[76]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导言”的开篇,即以我提出的问题为其问题展开讨论的,参见梁治平:“导言”,载《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77]参见同上,第1-29页。
[78]同上,第27页。
[79]梁治平:“自序”,载《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80]梁治平:“导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81]梁治平指出,“所谓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以往,许多法学家不但主张这些是法律,而且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全部的法律。结果,一个可能更广大的领域被忽略了。事实上,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他还指出,习惯法对古代法典的补充,使得民间社会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经济生活)成为了可能:“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法律史上最可注意的一种现象,甚至早在《唐律》颁行以前很久就已经如此”(同上,第37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梁治平在80年代末依据社会学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却为什么没有洞见到这些最可注意的现象呢?
[82]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83]同上,第52页。
[84]同上,第43页。
[85]关于西方汉学家的社会史研究,梁治平在一个相关的注释中开列了这样一些文献:“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情况,参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四章,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利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华北农村调查所得即《中国惯行调查报告》所作的研究也可以代表这种注重社会史研究的趋势。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可惜的是,习惯法方面尚少这样深入的研究。”参见同上,第44页。
[86]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X页。
[87]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载《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88]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89]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梁治平本人在《法辨》中的下述这段文字最为明显地说明了他的当下意识(当然,所谓的“当下意识”实是与对中国当下现实进行研究是有区别的):“实际上,这些文章不但是以同一种方法讨论着同一个大问题,而且是透着同一种关切的。在我来说,所以要写下这样一组文字,不纯是为了满足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是为了对今天严峻的现实作出一种回应”(梁治平:“自序”,载《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90]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91]同上,第26页。
[92]参见同上,第58-63页。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我看来,是很牵强的。
[93]同上,第233-234页。
[94]同上,第3页。
[95]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吉尔兹的理论完全是为了理解文化的地方性意义。他在一部讨论现代伊斯兰国家宗教发展的论著中曾经对此做了很好的说明。他在题为“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一章里指出,他之所以在众多案例中单选出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作为比较的单位,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彼此对立的性质。他这样写道:“它们最显明的相似在于……它们同属一种宗教,然而这一点又是,至少从文化上说,它们最显著的不同。它们立于古典伊斯兰文明狭长地带的东西两端,这个起源于阿拉伯的文明沿着旧世界的中线延伸而把它们联接起来。处在这样位置上的这两个国家,曾以颇不相同的方式且在颇不相同的程度上参与了这个文明的历史,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它们都向着麦加躬身致敬,但是,这穆斯林世界的两极,它们朝着不同方向礼拜。”参见Clifford Geertz,Islam Observed: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isia.p.4.另请参见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3-171页。
[96]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97]同上,第57页。
[98]同上,第132-133页。
[99]同上,第148页。
[100]同上,第42-43页。
[
101]同上,第41页。
[102]同上,第44-46页。梁治平在此前还指出过:“长期以来,我们只承认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即同志关系。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平等关系,但其内容不像契约关系那样可以精确地度量,而且,它不受法律的调整,因为,同志关系并非法律关系,而是基于某种政治上一致的假定产生的合作互助(当然也包括大量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种关系尽管界限含混,却未必一定要排斥契约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关系只能是中国式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民族文化传习的烙印。这里,首先就是对于‘契约关系’的由来已久的厌恶。这种态度与上文提到的对个人主义的厌恶同出一源。从传统的角度看,‘契约关系’就意味着‘重利轻义’,甚至‘唯利是图’。它不讲亲疏,没有等差,置人情于不顾,把一切都算计得清清楚楚的本性向为君子所鄙夷。倒是‘同志式’的关系更容易与传统价值观产生共鸣。所以,对于‘同志式’关系的片面强调事实上与‘契约’的观念正相抵牾。如果我们在‘同志式’的互相合作关系之后看到的是大量基于身份产生的关系,那也不足为奇”(同上,第43页)。
[103]同上,第157页。
[104]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105]比如说,梁治平指出,“如果说,在这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化当中,总会有为数不多的神圣传统贯穿始终的话,那么,视法为刑就是这少数神圣传统中的一个。其结果,中国古代法只能是‘公法’而非‘私法’。更具体些说,它只能是刑法”(同上,第135页)。
[106]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VIII-IX页。梁治平还指出,“中国古代法自有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植根于文化,因此,法律应该首先根据它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的类型来把握。如果说,孕育了罗马私法同时又深受其影响的西方文化可以被恰当地称之为‘私法文化’的话,中国文化则可以在同样意义上被说成是‘礼法文化’,而在这种所谓‘礼法文化’里面,‘民法’或 ‘私法’自始便无由产生”(同上,第IX页)。
[107]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108]同上,第151页。
[109]同上,第55-56页。
[110]参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页。
[111]梁治平:“导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12]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关于这个问题,梁治平本人做过反复强调,即使在 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一书撰写“再版前言”时还指出,“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辨异往往从严格的语词分析入手”(同上,第IV页)。
[113]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V页。
[114]梁治平:“再版前言”,载《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X-X页。
[115]坦率地讲,梁治平在1997年所做的作为“小传统”的清代习惯法的研究,也没有意识到有必要以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我所谓的中国法律结构的“双轨性”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独特的中国法律文化。
[116]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4页。另请参见该书第84页、第98页、第133页、第146页、第151页和第233-234页。
[117]同上,第149页。
[118]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362页。
[119]关于本质主义,可以参见尼采、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的论著,而比较集中的则可以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20]众所周知,梁治平在阅读了伯尔曼的论著以后指出,“在最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法律正不断丧失其神圣性,日益变成为纯功利的东西。与此同时,西方的宗教也逐渐失去它的社会性,慢慢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去。正义与神圣之间的纽带开始断裂,它们正变成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然而,仅凭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够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虽然还不能说今天西方法律已变作一纸空文,但是诸如犯罪一类社会问题的存在,不也反映出法律的无能吗?至于宗教,没有组织,不依靠程序,它如何应付外部世界的压力,又如何有效地维护和传递自己的信仰?60年代于美国各地大量出现的自性地方团体如公社,不正是因为它们的反法律倾向而屡屡受挫,因此往往是一瞬即逝吗?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割裂法律与宗教所生的恶果。当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当说明原因的原因,说明人类经验中这两个基本方面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按照梁治平“法律文化论”所遵循的“基因决定论”或“本质主义”逻辑,那么他是根本没有办法回答西方法律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这个问题是。
[121]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社会类型论文篇(5)
如果说初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那么在听了沈关宝老师的课又得以重走费老的江村路之后,再读《江村经济》则打开了我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思考。在书中,中国的过去,农村的生活经过费孝通先生准确、坦诚、真实的演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很多精彩之处让人印象深刻。同时费孝通先生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客观系统的描述以及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等的准确定义也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确切的资料,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一、对《江村经济》研究方法的认识
《江村经济》被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研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①,可见,《江村经济》所开创的社区研究方法在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社区研究方法,最早由社会人类学家发明,马林诺夫斯基1922年发表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堪称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早期人类学者为了研究他们所谓的“野蛮社会”,选择当地的一个小型社区作为工作地,采取参与观察的方法,深入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一般需要一年以上)。然后重回“文明社会”,用自己的语言将当地的文化予以描述,书写民族志。这种“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在当时是与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相结合的,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直是西方人类学的主流。而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江村经济》,却打破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常规,不仅研究的是他自身所在的本土文化,而这种本土文化又是一个相对先进的文化。这种突破不仅为人类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为社区研究探索出了新的道路。人们将费孝通先生这种运用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进行社区研究的新门道概括为“微型研究”。
1.微型研究方法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起点,也可以说是微型社区研究的一个样本。②在《附录: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费孝通先生写道: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人数较少的社会或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所以,微型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深处,特别是用普通研究方法难以深入的地方,比如对人际关系的分析、对思想活动的把握等,只有通过亲自与现实社会接触,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区研究,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③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微型社区的深入研究而获得的。
费孝通先生这种从个别社区入手进而概括整个国情的方法也曾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以江村来说,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型”。我这种思考,使我进一步摆脱了责难。我认为有可能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收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型,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④《江村经济》中的 “开弦弓村”聚集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特点,让人能够从一个村庄中看到无数中国村庄的影子。那么对“开弦弓村”如此深入的观察研究就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2.类型比较法
如果仅仅通过“开弦弓村”特点来概括整个中国农村的特点,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社区,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文世界,它除了社会基层结构和经济活动之外,还应当包括文化、宗教、政治等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叙述和分析。所以,《江村经济》虽然勾画出了土地利用和农户家庭中的再生产过程,但从整体而言,它还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特点。所以,为了认识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费孝通先生提出类型社区比较研究方法,以区别于通过数量上的增加而取得的总体认识。那么何为类型比较法?在后来的《云南三村•序》中,费孝通先生这样写道:“把相同的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与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⑤
所以,在费孝通先生整个学术旅程中,江村作为一个开端,就有了类型学上的意义:(1)“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2)“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实地调查的场地”。(3)开弦弓村“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土运输的集镇系统”。⑥
后来,费孝通先生带领他的弟子们选定了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等不同的社区,与江村进行了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来认识中国的社会及发展,所研究的问题都是中国各地各种社区所共同遭遇的现代化变迁的过程。
3.功能分析法
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还大量地体现出了功能论、系统论的思想。他把江村的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细致的考察了其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例如,他认为人创造出文化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如果要改变一种文化,那必定是新的文化对他更加有利;他还认为如果要对文化进行改变,就会引起其他社会方面的连锁变化,而一旦这种连锁反应开始,就会持续到新的系统产生为止;在文中,他还提到,为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做的一些革新措施,诸如颁布新民法,给予女子与男子平等的继承权、禁止传统历与高利贷、抵制封建迷信使用新的历法等等,都无法有效地执行,就是因为这些传统文化的存在是有它们的作用的,不是一般的法律制度能够改变的。以上种种都反映了系统论、功能论的观点。
而最难能可贵的是,费孝通先生在继承了功能论、系统论思想的基础上,又对其做了突破,他摆脱了功能主义学派缺少对动态的社会变迁把握的缺陷,对处在暗潮汹涌的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开弦弓村做了更深层次的考察。表面上,开弦弓村的村民有条不紊地生活着,社会各个子系统正常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村庄发生着质的变化,传统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家庭手工业破产,被迫转让土地所有权,为了生存成为雇佣劳动者,纺织工业的发展……家庭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就在这样的过程受到冲击并加以改变,而这也不正是传统中国农村变迁的道路吗?
二、《江村经济》研究方法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微型社区研究方法,对我们进行相对宏观的研究时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讨论到一些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或涉及宏观研究时,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开展。其实,费孝通先生“微型研究”的方法就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指明了一条捷径。选取一个或几个熟悉的“典型”,对它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寻找出整个社会的共性,将结论推演到整个社会,这不正是让我们在探讨宏观问题的同时得以将其付诸实践的一种方法吗?与单纯的理论研究相比,微型社区研究更有说服力、更客观;与文献资料分析相比,研究者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可以有更加真实的认知;而与全面调查相比,微型社区研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结论有相当的代表性:可谓一举三得。但同时,这种微型研究方法也对研究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虽然在对自己熟悉地区进行调查时,有语言、获得对方信赖乃至前期准备工作上的优势,但它要求研究者必须拥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眼光,能够在融入当地人生活的基础上保持客观的公正性并毫无隐晦地揭示出问题的所在。最为困难的还在于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无法保证所在地居民免受观察者自身的影响。微观研究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这一要求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显而易见。此外,再典型的个别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体,因此我们在进行此类研究,尤其是从个体推演整体时应当慎而又慎,要注意到其中的差别。
注释:
①④⑥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商务印书馆
2001.
②⑤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社会调查自白(第10卷) [M] .群言出版
社.1999.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商务印书馆
2001.
[2]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社会调查自白(第10卷) [M] .群言出版
社.1999.
[4]丁元竹.农村社区研究:由类型比较到模式比较 [J] .农村经
济与社会.1994.2
[5]乔凯.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方法探析[J].黄山学院学报
2006.2
[6]韩蕾蕾.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
社会类型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6-0040-09
一、“社会转型陷阱”解读
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系统,它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遥远的未来,然而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通过无数“试错”才能得以开辟。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社会是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孕育着国家、政府、政党,国家、政府、政党也能动地反作用(正向、负向)于社会。社会也产生着“主义”,主义也能动地反作用或反哺社会。“社会”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由人的社会生活为核心内容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社会存在形式两部分有机构成的。社会存在形式会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存在、变化、发展而存在、变化和发展,由此形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诸种社会形态。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因为没有什么是必然的、精确预言的东西,而主要是由于人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增强并发挥其正向作用的缘故。据考证,古代汉语中的“社会”一词是带有祭祀意义的聚会,是“里社集会”的简称,又指群众结社组成的地方团体之意。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最早出现在民治年间,由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后被引进到中国。当“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1〕概念被引进或传送到中国以后,各路仁人志士,社会贤达,开始运用“问题”与“主义”来解释社会,重构国家 。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接受、运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代中国社会,建构现代中国国家,改变着中国的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践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性转型之使命。
转型是事物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总体上属于质的螺旋式上升的进步状态,表现为多种样态或情形。如果某事物已处于定型化的“成熟”或“物极”状态,那么,该事物面临的“转型”、“必反”就为期不远了,否则,该事物就不会转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关于“社会转型”一词现已成为使用频度很高的词汇,我国大陆学界现已发表和出版了海量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转型”的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或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类型,尤其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指西方早发型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广义性。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这些研究比较集中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及其标志方面,主要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等等。〔2〕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不无裨益。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些“拿来主义”的理论研究或探讨,把西方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经验当着普遍性的社会转型经验,硬套到我国的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实践中来,这就势必在客观上造成我国某种程度的“社会转型陷阱”。
“社会转型陷阱”关涉到社会转型是否适度、适当、成败、复辟、倒退等问题。“陷阱”本指狩猎者为捕捉猎物而人为设置的伪装物,也比喻设陷、害人的阴谋。同样道理,“社会转型陷阱”不是自然的而是与人为有关,如果不是设计者有心有意所为,就是执行者乏力无为驾驭或被外力牵引,随从者无意识盲从的结果。笔者坚持认为,1978年我国开启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种种陷阱,能否避免这种种陷阱,则要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智慧。30多年来,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三个比较大的陷阱:其一,是“现代化的陷阱”;其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其三,就是“社会转型陷阱”。其中,所谓“现代化的陷阱”,是因《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转轨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原名《十字路口的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一书而得名。正当不少人正陶醉、酣睡在改革的甜梦中时,该书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经济繁荣的社会后果,较强有力地证明:在中国,少数人的暴富并不必然会改善社会状况,也未必引导中国走向民主。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从特定意义上,与其说是“现代化的陷阱”倒不如说是“改革的陷阱”,如果改革在实际上走向预先设计的反面,就尤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先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根据世行的定义和标准,我国人民论坛杂志曾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此种陷阱的特征也困扰着我们国家,只是其性质有所不同罢了。所谓“社会转型陷阱”是一个创新概念,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其主笔的清华大学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有别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是指在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改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社会转型陷阱”,倒不如说是“改革的陷阱”更为确切。由此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所谓“社会转型陷阱”是“自设的”还是“他设的”抑或是某种“合谋”?这就关涉到非常复杂的政治生态问题。
“政治生态”是由“政治”与“生态”合成的概念,有别于“生态政治”。政治有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之分,本文侧重于广义政治。生态,本是生物学概念,一般解释为“环境”并与环境连用为“生态环境”。政治又可分为一般或普遍政治、特殊政治、共性政治、个性政治、动态政治、静态政治等。政治生态还可分为政治自系统的相对于某个政治主体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自系统以外非政治系统各要素所构成的政治生态环境两部分。本文论析社会转型陷阱的政治生态侧重于广义政治的“复合型”政治生态。
比较分析可见,“社会转型”、“社会转变”、“转型社会”、“社会形态转型”等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不做区分)。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社会转型的类型、动力、形式、方式、起点、路径、目标等等问题。就其类型来说,可分为:人类社会转型,西方社会转型,东方社会转型;宏观(大)社会转型;微观(小)社会转型等等,本文侧重于宏观的大转型。在我国,所谓“社会转型陷阱”可称为“连锁性陷阱”。它们“异症同源”,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是各有侧重,表述有所不同而已。或者说,“社会转型陷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消极的副产品,它们正危及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主产品。我们认为导致“现代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转型陷阱”的政治生态要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不就形式而就其内容来说则是共同的,就是把“现代化”、“分配收入”、“社会转型”等概念、命题过于抽象化、中性化、一般化,并在表象上进行价值剔除,去除相关的社会性质或制度性质,而在事实上确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性质,以便暗含设陷的玄机,以售其奸。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照搬西方国家社会转型的模式,拿来主义地套用,就势必导致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可能实际偏离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最高或顶层的、总体设计的理念,难以兑现最初向人民所许下的总体政治诺言。曾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从三个层面研究战争的规律问题,即: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现代化问题,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社会转型问题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中,就社会转型而言,如果我们从社会转型的普遍或一般,从社会转型的特殊,从社会转型的个别视角切入,研究社会转型、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就有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寻找“社会转型陷阱”形成的政治性成因,找到突破陷阱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转型的普遍性政治生态
社会转型原是西方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和基本范畴,它的原初含义是强调以社会自身结构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发展和结构性变动。社会转型的原初含义还可以具体化为“四个强调”:强调社会“自身”结构,不是“他者”;强调社会结构为“主体”,不是“客体”;强调社会“整体性”(“一盘棋”)发展,不是高度“统一性”、“集中性”或“局部性”、“碎片性”的社会发展;强调社会的“结构性”(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变动,不只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动能性的变动。与此同时,笔者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准确解读社会转型问题时,还不能离开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传统”。在解读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侧重在强调社会的先在性,强调社会主体性。与社会先在性、主体性理论传统对应的是“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至上性。另一个是基于社会的先在性、主体性,侧重于对社会进行“量态”而非“质态”(尤其是指社会性质或所有制关系)的分析研究。与此相联系的是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占居主流地位的价值观或理论传统。这两方面的学术传统事实上源于它的实际载体——社会的所有制传统亦即私有制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私有制转型”或社会“所有制转型”,即在社会进化的历程中,逐步扬弃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使其不断地趋向社会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这可能也是一种预设,一种并不是必然导致消极的“社会转型陷阱”的预设。至于假借以“社会转型”名义来诱致某种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非正常地落入引诱者预设的“陷阱”,此种情景则应另当别论。
为准确解读社会转型问题,还应当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列宁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3〕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笔者试列出以下图式,即社会科学——唯物史观——社会形态——所有制关系——生产力——人。笔者所思考的基本逻辑是:社会科学是三大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慎明同志主张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分类之一,社会科学的同义语是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社会形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由此决定着整个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最终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状况,生产力不仅仅是物,而且还在于人,是“人物”的有机结合,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如果说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那么,人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媒介。只有抓住了现实的人 ,才算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4〕。对于这个图式,我们着重从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社会形态)和社会与国家三个维度来解析社会转型问题的普遍性问题。
关于社会与自然。马克思论证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认为早期的人类处于自然界的绝对支配之下,生活资料主要通过体力劳动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得,此时的财产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自然的统治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背景下,劳动的统治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的统治,即积累起来的劳动的统治。这种统治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也造成了劳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以及社会再生产的中断,使自然界的物质代谢和循环发生紊乱。由此,资本与私有制的存在造成了破坏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体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5〕。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发表题为《增长的界限》研究报告,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议。此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提出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改变增长方式以及倡导低碳生活等等理念与措施,为处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与自然极限的矛盾,降解社会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与有效的对策。因此,从最宽泛意义上说,所谓“社会转型”首先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问题上的转型。基于大历史观,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经历三大历史阶段和两次转型。所谓“三大历史阶段”是:自然支配、统治社会——社会“改造”、“征服”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所谓“两次转型”即:第一次转型是从自然对人、社会的统治到人、社会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或对立),这次社会转型大体上“以资本来到世间”为标志;第二次转型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从人、社会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或对立)到追求社会与自然的“合一”与“和谐”。这既验证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也符合当今和未来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人类还将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之中。这是其一。
关于社会与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主要有三种划分方法。其一,根据生产关系或所有制性质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从所有制关系方面分为: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社会所有制。这种划分贯穿着线性进化论,所引起纷争的问题不在于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同中有异,甚至千差万别,而在于这五种社会形态在具体的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步性和非平衡性,以及由此产生常规有序性或次第展开性与非常规无序性或发展的不无条件的跳跃性。其二,根据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人对物的依赖性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们分别同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相联系,表现为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如果某种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是指它可以比旧社会制度所没有的高速度发展来弥补先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滞后性,但不可以随意跳跃或超越。其三,根据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其技术社会形态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它所展示的也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这三种划分关涉到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其统一性的程度关涉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如果社会质量高,社会就能够良好地自我运作和管理,解脱政府的重负,反之,政府就会陷入繁杂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政府太累。由于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要素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社会质量归根到底受制于人的质量,即受制于人的发展。因此,研究社会问题必须以研究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进而研究人与社会的价值互动。〔6〕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就是社会与人或人与社会关系的纵向或历时态的转型。如果基于大历史观,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或所有性质也经历三大历史阶段和两次转型。所谓“三大历史阶段”是:原始社会共有、公有制——阶级、国家社会的所(私)有制——未来社会的社会所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谓“两次转型”即:第一次转型是从原始社会共有、公有制解体向阶级、国家社会的私有制确立转型;第二次转型是从阶级、国家社会的所(私)有制向未来无阶级、国家社会所(公)有制社会的转型。确切地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这次社会转型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理论上,一般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在实践上,一般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变成现实。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还将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之中。这是其二。
关于社会与国家。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国家是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政治学角度看,社会与国家是对立面的统一。其中,对立面是侧重于国家的阶级性,表现为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大众利益的对立;统一性则是侧重于国家的社会性,表现为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中介人”的地位,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谋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把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投放到历史动态的长河中去认知他们并不构成两个对立的中心极,而是在互动中其重心不断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概括为:从社会国家化到国家社会化。前者,社会先在于国家,国家从社会母体中生成、发展、增长至极,国家赢得至上性甚至吞并社会,以致人们只知国家而不知社会,如封建社会的国家就是如此。后者,在社会自身动力和国家导向作用力的互动下,社会不断发育、成长、成熟,内部分裂与冲突的因素逐步消除。一方面,国家开始自律,即在国家权力、能力、权威方面的自我限制,逐步还政于社会;另一方面,社会随之要逐步收回曾经让予国家以及被国家掠夺取得权力,直到社会获得自主性,社会逐步不再需要国家,实现社会自治。虽然这种情景距离我们还相当遥远,然而这的确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大趋势。这种大趋势大体上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最终确立以后。〔7〕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纵向或历时态互动所经历的三大历史阶段和两次转型。所谓“三大历史阶段”是:社会产生国家或社会国家化——国家与社会共存互动——国家社会化或国家回归社会。所谓“两次转型”即:第一次转型是社会向国家转型,亦即社会产生国家或社会国家化;第二次转型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日益成长,国家日益趋于社会化,国家逐步还政、还权给社会。人类还将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即国家与社会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是其三。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转型是多种多样的,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表达法。究其社会转型的普遍性或共性、一般性而言,任何民族国家都会直面一个该社会与自然、该社会与人、该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们都有一个历时态的或纵向的从前者到后者的社会转型或社会过渡问题。如果从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性进程来说,当今人类社会还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即: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 ,从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向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的转型;在社会与人的关系上,从私有制社会向社会所有制社会的转型;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从社会国家化社会向国家社会化社会的转型。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这种总体性社会转型,是一个不断社会转型与阶段性社会转型相统一、历时态社会转型与共时态社会转型相统一的历史过程。由于具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及其演变、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各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背景迥异,具体处在何种历史方位或何种历史发展阶段,则是千差万别的,它们应当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就涉及到社会转型的特殊性问题。
三、社会转型的特殊性政治生态
人类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寓于具体民族国家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之中。对人类社会转型普遍性来说,社会转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早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一类是后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前者,通常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后者,通常是指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由于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早发型民族国家社会转型所走过的道路、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后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与示范作用。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转型总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分类。一般说来,可以以三个时间点为参照系:其一,以1840年为界,是由传统中国开始向现代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8〕社会转型,虽然早期有不同的社会价值选择,但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同质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大转型”;其二,以1949年为界,是由旧中国开始向新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从半殖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型,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异质性”的不同发展历史类型的“中转型”;其三,以1978年为界,是由新中国开始向新新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后新民主主义社会〔9〕转型,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同质性”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小转型”。其实,严格说来,根据笔者对“转型”的解说,所谓大转型、中转型可属于同一种历史类型的社会转型,因为它在社会性质及发展取向上开始着质的变化。而所谓小转型,其社会性质尚未定型化到需要根本转型的程度,尚需要自我调适与积极建构,由此应该警防“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性质的蜕变(陷阱)绝不是多余的。可见,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其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特色之一,是社会转型的独创性。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在于,她历经五千年绵延不断地存在与繁荣,昂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传统文明的特征主要有: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以血缘网络与地缘网络为两翼,并借助众多经济共同体及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大一统文明;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局限与弊端也源于此。根据上文对“转型”的解说,中华传统文明是“成型”的。由此,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也是自然的。主要表现在:以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指导,以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为两翼,整个社会经济正经历着全面的转型;大一统国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实际上统领和决定着整个社会转型进程,并在这一转型中自身也在转型;知性上升至主导地位,整个社会正在走向知识化;正在转型中的古代、近代、现代文明将长期并存共生。经过几代人的上下求索,峰回路转,终成社会转型的基本路径,以解决无法回避的三大问题,即:外铄与内生相悖和对立;大一统国家权力全能化、绝对化和人的普遍自主自立相悖和对立;人的异化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相悖和对立〔10〕。这些独创性是总体性的。这些总体性的独创性特色正在进行时,就具体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之中。
特色之二,是社会转型的“天人合一”性。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核心命题之一。其主旨认为“天”是世界的本原和法则,“人”在宇宙中居于特殊地位,自然、社会和人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天”或“道”、“理”又是这种统一性的抽象。这种思维方式使“天”成为自然观与社会观、哲学思辨与政治思维的混成物,以致无论主张以天合人还是以人合天,其主旨都是论证一种理想的社会与理想的人生,其中心论题是政治。在古代文献中,“天”的内涵主要有三类含义:其一是自然之天;其二是义理之天;其三是主宰之天〔11〕。本文的天人合一之“天”取自然之天之义,亦即引申为自然界;本文的天人合一之“人”与“社会”同义。这样,“天人合一”就成为“自然与社会合一”或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在极其漫长的自然支配、统治社会或人的历史岁月中,为了彰显人的实践主体性,古代中国智人还奉献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命题,成为后来人们通往现代化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渊源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落后势必挨打”、“赶超发展战略”等驱使下,人们为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向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由此,我们干了不少蠢事。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也继续干了不少蠢事,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会比我们更有公论。自《增长的极限》敲响了人类生态危机的警钟以后,为了体现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自觉,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先后提出“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理念,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等一系列举措,成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转型的重要历史标识。1994年3月,中国政府颁发了《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部级《21世纪议程》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中国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等理念。这些理念是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智慧的当代版。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社会转型所谋求的不是“先发展后治理”,更不是“发展自己污染别人”,而是“边建设边治理”,或“建设与治理并举”,甚至生态文明建设先于环境治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特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她将为保护地球这个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当代新贡献。
特色之三,是社会转型的多质态性与包容性。一般说来,一种常态社会内涵过去社会的遗迹、现实社会的基础和未来社会的萌芽三种质态,当今中国社会也不例外,尤其是转型期的社会质态更加复杂多元。首先,表现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上文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期法,以及原始公有制——阶级、国家私有制——未来社会所有制三大历史阶段的逻辑建构,只是一种理论抽象,至今的人类现实社会中找不到按此理论进阶的实践范例,以致有人主张否定和放弃这种理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现实中既没有清一色的私有制,也没有清一色的公有制,而且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有其多种实现形式,尤其是私有制。比如,同样是私有制,就有奴隶社会私有制、封建社会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同样是封建社会私有制,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同样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有私人资本、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等等。在历史实践层面上,1840以前封建的中国没有转型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中国,“外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官资”—官僚资本、“民资”—民族资本,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城乡小手工业构成就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旧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其中,反帝,争得中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反封建,争得人民民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或目的已经完成或达到。与此同时,在没收和剥夺“外资”和“官资”基础上,创建了带有社会主义成分或因素的“国有经济”(长期以来人们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很值得商榷的,一方面,它部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道共同构成新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我曾称之为“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构成的命运共同体,犹如一对龙凤连体胎儿〔12〕。它们成为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中主要的经济成分。后经“三大改造”,“消灭”了非社会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历史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重构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验证我国“改造”、“消灭”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合理性。这种验证过程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调适”、“自我修正”过程。当然,如果这种自我调适和自我修正过程“失度”,正所谓矫枉过正,那么,势必会出现反复,就会有可能落入“转型陷阱”,虽然这种陷阱不一定是预设的。其次,表征在生产力方面。多质态的社会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归根到底所有生产力性质和状况决定的。生产力主要包括物的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两部分。作为物的生产力主要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工具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指示器。人类社会生产工具先后以石器-铁器-铜器-机器-电子等为标志,人类社会有此经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作为人的生产力主要是以人的发展程度为标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人的发展经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与此相关联,人类社会大体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社会及其相应的所有制关系发展的历史阶段。根据目前我国生产关系所有制现状,检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参差不齐的现实,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与生产力的多质态共存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处于某种“混合”的或“混沌”的状态。笔者曾经将此情景比喻为犹如人类社会的“大熔炉”和“活的历史博物馆”〔13〕。对此,我们似乎很难在是公有还是私有、是计划还是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左还是右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与抉择。但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笔者以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提倡“亦此亦彼”的社会包容性,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需要一种大历史观,需要一种至上的大智慧,当然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特色之四,是社会转型的国家主导性。社会转型决定国家转型,国家转型主导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伴随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自从社会产生国家以来,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不是“自行”或“自发”的,亦即社会转型不“自传”,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社会自己的事。此情此景,古今中外不会有例外。不过,古老的、后发外铄内生型的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转型尤其如此。社会是一个巨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子系统。社会发展就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和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就包括:社会经济转型,社会政治转型,社会文化转型和作为子系统的社会转型。社会各子系统的发展和转型,各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按照各自的规律发展和转型,它们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社会各子系统的发展和转型都应有相应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就其功能而言,社会的经济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基础性作用;社会的政治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关键性作用;社会的文化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导向性作用;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整合性作用,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中,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又可细分为社会政治发展、转型和国家政治发展、转型两类(政治可分为社会政治和国家政治,这两种政治不能视同〔14〕。笔者坚持认为,凡国家的都是政治的(但凡政治的不一定都是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转型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文化发展、转型。国家政治发展、转型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转型,并进而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文化发展、转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转型,而社会政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治转型,而国家政治转型主要是从“全能政治”(垄断包括社会政治在内的政治)向“有限政治”(专司国家政治)转型,从必要的“权力集中”向对“集中权力”进行自身的和社会的有效制约转型,从“社会国家化”向“国家社会化”转型……笔者把国家政治的这些转型称之为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主导性,以倡导重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鉴于我国政党与社会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与其说是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主导性,还不如说是社会转型中政党的主导性更为确切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当然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值得展开深入的研究。
四、中国社会转型向何处去?
中国现在何处?通过社会转型向何处去?这依然是一个有待小心求证的大胆设问。
社会转型是一个真问题。人类社会的转型问题,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看都是客观存在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转型问题的一种表达法,具有“普遍性价值”,但不是“普遍主义的”。一方面,人们对于传统与现代等相关问题的争讼尚无共识,由于传统和现代的多样性,决定着通向现代社会不只是先发国家的“华山一道”,硬要后发国家削自己之足以适先发国家之履这本来就不是文明之举。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的普遍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实现形式的差异性、实践路径的多样性是“复合统一”的。这种复合统一不是对普遍价值之一般拿来主义的“克隆”和对特殊价值之个别保守主义的固守,而是一种“有机化合”的创新。本文认为,人类社会转型的普遍性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与自然关系、社会与人特别是所有制关系以及社会与国家关系方面。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价值显然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转型普遍性价值发展的文明大道。
我国社会是从什么型转到什么型?怎么转?转型能否成功?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与众多论述“社会转型”问题的学者不同,刘德厚先生率先提出和论证了“双重转型”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面临双重转型:既要加速实现现代化,又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基本内容是: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化=社会“双重转型”。新型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人民民主国家制度=新型社会主义〔15〕。刘先生的创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比较令人信服。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们认为,基于大历史观来审视人类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是:从传统封建社会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转向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亦即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路径则是:从传统封建社会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亦即从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该思维路径表明,我们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只唯实。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起点是1840年前的封建社会,转到什么社会呢?在西方,是直接转向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再转向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是在中国,则既不是直接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直接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未来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真实国情的。我国社会还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笔者曾经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土特产,是加进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在我国,我们能够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和转型,我们就可能不犯或少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条主义、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尝试的教条主义以及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我们就可能少一点传统与现代、公与私、姓社与姓资,左与右等等的纷争,我们就可能远离社会转型的陷阱。
今日之中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中国,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中国;同样,如果没有适度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的中国,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中国。是为本文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1〕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58-84.
〔2〕李培林.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研究〔J〕.哲学动态,1996,(2);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J〕.哲学动态,1997,(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基础研究报告〔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乔耀章.“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5〕李龙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与生态文明思想——从合统一性角度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2).
〔6〕〔7〕乔耀章.政府理论〔M〕.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44-145,148.
〔8〕〔9〕〔12〕〔13〕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乔耀章.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8,(1).
社会类型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1)02-0066-04
类型学(typology)的研究历来不被重视,以往很多教材不是对此语焉不详,含混不清,就是避而不谈。但是,随着国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它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任何比较文学者都不能再对其视而不见,或绕道而行。国内外很多比较文学教材或专著之所以对类型学避之不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资料搜集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类型学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各人的视角与理解不同,因而要对它下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确实很难。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迄今为止对类型学下过定义、将其纳入编写范围的屈指可数。在这些不多的对类型学的定义中,又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以卢康华、孙景尧为代表的草创阶段;第二是以孙景尧、陈等人参照苏联的并不断修订的阶段;第三是以曹顺庆领衔的改革阶段。
一、类型学的类同研究
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卢康华、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导论》对类型学下了自己的定义:“对比研究不同国家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等”,并进而介绍,在港台类型学翻译为典型学,而“在苏联比较文学上,‘典型学的’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指的是将文学要素依某种特征分组,例如那些属于同一文学类型或文学‘运动’的作品归为一组”。并进一步阐发,“我们觉得这一术语可用来指类同的作家作品、形象、情节甚至包括技巧、语言、意象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对类型学的定义在主观上一开始就意在与苏联比较文学研究方法遥相呼应,因为包括类型学在内的比较文学几乎都属于“舶来品”,国内学者基本上靠借鉴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当然,该书似乎对该定义也没把握,秉着严谨的态度,在一注脚下声明“由于缺乏苏联的资料,这里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也许与其涵义不一”。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类型学的定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者自己也不清楚是否与苏联的类型学相符。
两位编者之一的孙景尧先生在时隔4年后单独出了《简明比较文学》,在获取有关苏联比较文学的有关资料后,对类型学下的定义似乎就要有底气得多了:“这种不求实证、不查影响,而是用对比和分析等方法,并从社会、经济、心理、传统、历史等方面来对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艺术技巧等文学要素或文学运动,依某种标准将其归类所作的比较研究,就是本学科范围平行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类型学。”接下来把国内的“类型学”与苏联的“类型学”作了区分;“苏联的‘类型学’是包括了广泛的本学科平行研究课题在内的,同我们在此所说的本学科平行研究之一的类型学并非是一码事。我们这儿所说的类型学,是指比较研究文学中的具有某些共同或类似特征的现象,包括了人物形象、作品、方法、技巧以至创作方法与文学运动等。”。从以上解释中可以看出,该书把苏联的“历史类型学”看做是与平行研究大致相同的一个概念,而国内的“类型学”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只是平行研究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这里仍然没有真正将国内的类型学与苏联的类型学区别清楚,所谓的“人物形象、作品、方法、技巧以至创作方法与文学运动等”,实际上范围依然很大,还是让读者很难分辨。
不过这一定义最大的作用是明确了类型学是属于平行研究范畴,以后教材中提及类型学的,大部分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如刘介民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方汉文主编的《比较文学基本原理》、陈悖、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等教材,基本上就都承继了孙景尧先生1988年出版的《简明比较文学》中对类型学的界定。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类型学研究限定为寻找不同时空的文学现象的类同,从而得出文学的通律。本文把这种类型学的研究称为类同研究,以区别后面曹顺庆教授提倡的类型学的异质研究。
二、类同研究与苏俄历史类型学的差异
那么,苏俄的历史类型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寻求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类同呢?答案是肯定的。苏俄的历史类型学研究确实也强调寻找不同时空的文学现象的类同,并把这种类同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文学现象的类同是不同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类似造成的,并称之为“历史类型学的类同”。如日尔蒙斯基在《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的报告中说:“在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其中包括作为对现实的形象认识的文学,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同一阶段,会出现大量的类似。这种类似的特点,不管是普遍的或是特殊的,在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情况下,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类型学的相似或者契合。”尼・康拉德也认为:“比较类型学的研究的任务,也可以是从事发现彼此独立地兴起的各现象所具有的类型共同性。例如,依我看来,就可以证明西欧文学中的骑士小说和日本文学中的‘军事记’、欧洲启蒙时代的讽刺小说和中国19世纪的暴露小说之间的类型学的相似。”尼・古德济主张:“借助于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对比同类的或相似的文学事实与现象,而不问其是否有同源关系或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往来而产生的借用、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但是,苏俄的历史类型学并不是像国内大多数学者以为的只是一味地强调类型学的类同研究,它也重视不同文学的差异性,也曾呼吁过对异质性的重视。如日尔蒙斯基在其被国内学者广为引用的文章《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中开篇就说:“比较并不取消所研究现象(个人的,民族的,历史的)的特性,相反,只有借助于比较,也就是判明异同,才能正确判明其特性之所在。”“同时,正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重要的、更具个别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由历史过程的地域特点和由这些特点造成的民族的、历史的独特性所引起。对这些特点的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确定在社会制约中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确定作为比较对象的各种文学的民族特性。”“对于任何历史比较的研究文学讲,有关差异和它们的历史制约性的特点问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类似的问题。”马尔科夫在《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中也说:“文学的比较研究,要求判明被比较的现象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民族的独特性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并没有失去它所包含的普遍的特征。在分析相似的现象时,经常
地和必然地要去考虑到民族的独特性。”
赫拉普钦科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一书中明确表示:“认为类型的共同性包含着一些同样的现象,这种共同性‘剥去,并排除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的每一个文学思潮内部的这些流派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是千差万别的。这一点也牵涉到这一或那一民族文学中文学思潮内部的各个流派。”“遗憾的是,人们对各种不同文学思潮的内在差异的研究很不够。例如在浪漫主义中,通常认为有两种流派: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我认为,这种划分把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图式化了,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可以看到更加复杂得多的内在差异。”
很明显,日尔蒙斯基、马尔科夫和赫拉普钦科等人对不同文学间的差异性是很重视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苏俄学派的历史类型学的理论接受,大多数只注意到其对类型学相似研究的追求,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对不同文化之间异质性的强调,导致国内相当多学者误以为类型学只研究类型的相似,从而在用其指导实践中只研究中西文学中的类似,而不重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国内有些学者即使注意到苏俄学派类型学对差异性的呼吁,但是也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梁工、卢永茂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观》说:“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相异,加上作家的创作个性不一,文学现象之间除了存在着类型学的相似之外,必然存在着重要的、‘更具个别性的差异’。”书中虽然也认识到日尔蒙斯基对差异性的关注,但并未深入探讨。所以在给类型学下定义时虽然提到了“平行比较不同文学类型的异同”,但并未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
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也提到:“类型学并不以追求对文学的共同性的解释为其惟一的目标。各民族文化之间虽然有其阶段性的相似特征,但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经历,常常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所经历的封建阶段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要反映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反映在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中。对不同民族文化、文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的理解同样是类型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类型研究还面临如何处理同一类型的文学现象之间的相同、相似与差别、相异的问题。”但是,该教材也认为,“同一类型内部的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明显没有对这种差异性的重要意义表示出应有的重视。
三、类型学的异质研究及与苏俄历史类型学的差异
面对此种现状,正如有些学者所警告的,“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就很可能使异质性相互遮蔽,而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而这种忽视中西文学异质性给中国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带来的弊端大致说来有两种,“一是一度颇为流行的被称为‘X+Y式’的东西文学的浅度比附”,二是“把西方文学思潮流派或文学理论中一些特定的类型学术语牵强生硬的套用来阐发中国文学”。
而这些弊端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给一些西方的学者以怀疑和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口实。韦斯坦因认为“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他还表明自己“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犹疑不决”。这种看法代表了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普遍态度。以此态度来审视中国当下比较文学界所开展的类型学的类同研究,大多数是类似《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王熙凤和福斯泰夫》之类的发生在中西之间的文学比较研究,而这些正好是韦斯坦因等西方学者所不认可的。如果不直面韦斯坦因的这种质疑、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很多类型学研究实践都是“不合法”的,都是没有学理依据的。
面对这种挑战,面对类型学的类同性研究的左支右绌的困境,一些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学者经过认真思索,决定另辟蹊径,探寻另一条通向目标之路。曹顺庆先生从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高度出发,提倡类型学异质研究。以往的类型学类同研究关注的是不同国家文学现象的类同之处,这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能揭示、概括出一定规律性的问题。但是类同研究找出这些相似之处后往往就此结束。然而,这只是类型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再对其进行异质研究,探求类同现象下有何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曹顺庆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对类型学进行了具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特色的定义与阐释:“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类型学(typology)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这一定义与以往的诸多定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最后的那句话,即类型学研究的目标既要寻求文学通律,但是也要发掘不同文化的差异,即彰显不同文化的异质性。
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是指不同于以往的只重视类型学的类同、追求文学的通律,而是更加重视类型学相似表象下的深层的异质性,以彰显各民族文学的特性,达到对世界文学和文学规律的丰富性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是在曹顺庆先生提出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背景下而得以突显的,它其实是属于中国学派所提倡的异质性研究大背景下的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所以有必要先回到对异质性的重要性的探讨。
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曹顺庆先生认为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理论大厦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中西“异同比较法”。而“异同比较法”在进行“‘异’与‘同’的比较辨析”时,“它更注重‘异’的探讨”。之所以要强调异质研究,是因为,“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因此曹顺庆先生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东西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所谓的异质性,就是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学话语上是从根子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学则是生长于同根的文明)。”“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多元文化的视野,从既成的文化形态出发,把异质文化各自的基本价值范式作为评价自身文化现象的基础,强调辨‘异’的重要性。”
当然,这一定义包含的研究范畴,与苏俄的类型学也是有差别的。曹顺庆先生提倡类型学应该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
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彰显民族文学的异质性。这是对苏俄历史类型学求同存异的研究思路的回归,但是又与之不完全相同,而是更偏重于寻求不同文化的异质性。苏俄历史类型学是既求同,也求异的,但是,相对来讲,更偏重于求同,而对异质性不是那么重视。如日尔蒙斯基在论及文学思潮的差异性时,就说过:“文学思潮之间虽有某些差异,但我认为并不重要,它们的这种发展序列已为欧洲文学史家不同程度地公认,只要他们不执著于唯名主义的观点看待一般历史的和文学史的概念(封建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并倾向于区分个别事实之后不再注意联结这些事实的共同规律和思想。”
四、结语
对异质研究,许多学者表示了认同与赞赏,如孟昭毅编著的《比较文学通论》就认为,中国学派“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融会之中提倡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尽管它显得有些保守和狭隘,但矫枉过正,可以用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其实,这些评价并不太确切。诚然,异质研究理论确实能为以往被排挤在外的中国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争取入场券,驳斥对中西之间类型学研究的怀疑和否定,取得理论的合法性。但是,异质性研究并非是曹顺庆先生的心血来潮,或者说是故意要特立独行,或者说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和诉求,异质性研究其实也是历史类型学理论中的应有之义。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既是还原对历史类型学的认识,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跨文明语境下开展类型学类同研究陷入困境时的一种努力,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做出的睿智的选择。类型学异质研究不仅有利于重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话语,而且对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维护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3]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558.
[4]方汉文.比较文学基本原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74.
[5]陈悖,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05.
[6]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M].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9:68.
[7]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8]赫拉普钦秤.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M].满涛,岳麟,扬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9]粱工,卢永茂.比较文学概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10]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16.
[12]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3]乌尔里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恿,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6.
[14]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J].中国比较文学,1995(1):18-40.
社会类型论文篇(8)
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是研讨犯罪与文化关系时不能逾越的一道理论屏障。随着犯罪文化学研究的深入,随着对中国本土犯罪问题和有关犯罪学理论的不断重视,我国学者已不满足将认识仍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塞林根据美国国情所提出的文化冲突理论上。为深入体察中国的犯罪问题,文化冲突理论需要进行合理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既需要继承原有理论的精华,也需要理性反思原有理论的分析限度,本文以文化规范性的视角结合当代中国犯罪实践和社会情势进行犯罪学与文化学的跨学科研究。
一、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及其分析限度
(一)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内容与意义
文化冲突理论较早地受到了犯罪学家的青睐,尤其是美国学者塞林创立了解释移民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1939年,他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深入分析了移民犯罪的发生原因,并系统地提出了文化冲突理论。塞林主张,作为文明生长过程的一种副产品,社会中必然存在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同社会价值、利益、规范和文化准则的冲突。因而,文化冲突易造成个人行为规范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是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过实证调查,塞林认为:“当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区域的规范移入另一区域或与另一文化区域的规范相接触时,文化冲突在所难免。”“文化冲突主要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这些文化准则在毗连文化区域的边界接触、碰撞时;第二,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法律规范延伸到另一文化群体的领域时;第三,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迁移到另一文化群体中时。”“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社会变迁导致产生无数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生活情景都有自己的定义,对社会关系也各有各的解释,而对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却全然无知或每有误解。”[1](P129-136)
塞林结合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的特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分析美国移民犯罪的现状,解释为什么移民更容易实施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他认为移民犯罪常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第一,新旧文化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第二,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第三,从组织良好的同质社会迁移到无组织的异质社会。”[1](P151)塞林的研究一方面将文化冲突与犯罪问题联系起来,意味着犯罪的发生也受文化冲突的支配,标志着文化学的文化冲突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还可在犯罪学中获得新的阐释,并为今后的犯罪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塞林将文化冲突论与当时美国的社会转型和变迁相融合,使文化冲突论对现实犯罪问题的分析具有较强地解释能力,他的某些观点至今仍对当今的犯罪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可以说,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在犯罪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具有开拓先河的学术地位,从此学界对犯罪的文化分析不再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泛泛之谈,开始注重对文化学基本理论与智识思想的汲取,开始注重对特定社会场景、结构和情势变更的体察与反思。
(二)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应该说,任何一种理论均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适用空间和效力范围,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理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尽管具有诸多的积极意义,但在客观上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分析能力也存在一定的限度。
从社会背景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转型与犯罪现状基础之上的,该理论适用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但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尽管当时美国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均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变迁和犯罪浪潮冲击,但由于历史、宗教、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当时美国社会的犯罪情势、综合原因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差异。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新教伦理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的矛盾;而中国当代文化冲突则包容了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计划经济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等多元文化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塞林的文化冲突论能够解释美国的移民犯罪,但却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犯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从犯罪类型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主要是针对美国移民犯罪而衍生出的理论模式,所以,该理论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其他犯罪类型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尽管移民犯罪比较严重,但这也仅是诸多犯罪类型中的一种。塞林的理论对移民犯罪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对犯罪、青少年犯罪、白领犯罪以及大量个别实施的传统型犯罪(如人身和财产型犯罪)的研究恐怕就难以胜任了。
基于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应该说,为了开展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研究,我们需要汲取塞林理论的精华,注重文化规范对犯罪产生的影响,沿着塞林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但我们更应清醒认识塞林理论的分析限度,立足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现状,将塞林的理论中国化,从而逐渐发展出关照中国犯罪问题的文化冲突理论。
二、文化冲突论:中国化的场景与视角
有关中国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形成,需特别考察两个前提:其一,是对当代中国犯罪发生的基本社会场景进行分析;其二,是为文化冲突论选取适当的研究视角,毕竟“知识在本质上是视角性的”[2](P414)。这样研究场景和研究视角共同构成了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思维起点和知识基础。
(一)中国场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文化冲突发生于人类历史的转型时期,社会剧变孕育了它。对犯罪之文化冲突论形成背景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
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就是追求现代化。“现代化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方面的转变。”[3]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先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社会转型之路。社会转型是一个既熟悉又复杂的范畴,它能够导致社会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社会转型与社会常规时期相对应,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中断;社会转型也是人们实践活动方式的根本改变;社会转型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变化;社会转型更是文化模式的变迁。”[4](P21-25)
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所言:“现代化所伴随的是人类业已看到的巨大灾难……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举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5](P37)中国的现代化也存在错位现象,即传统文化因素瓦解速度很快,而现代文化形成的速度则相对迟缓,社会易形成各种制度真空和价值规范真空。
同时,从社会结构上看,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逐渐嬗变为多元性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发育,市民社会不断成熟,横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农民工),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社会分层中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不同阶层间的诉求出现冲突、利益形成对立。这样中国社会逐渐嬗变为由不同亚群体和社会阶层组成的多元社会。不同阶层、亚群体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主张,不同阶层、亚群体之间逐渐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不同群体亚文化的冲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就蕴涵在由追求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构成的当代中国场景中。可以说,离开这一中国场景,对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分析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总而言之,在这种中国场景中,日渐多元的社会酝酿了大量的矛盾和混乱。这些混乱与矛盾在文化上造成了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催生了各种犯罪亚文化,形成了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中国场景决定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是我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
(二)研究视角:文化的规范性
文化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6](P19)文化具有规范性,能够影响、制约个人的人格和行为,文化规范性是社会内在的运行机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本质。中国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将文化的特征分为四种,即规范特征、艺术特征、认知特征和器用特征。他认为:“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或应迫,就是规范特征。伦理和道德是规范特征的总汇。宗教有很强烈的规范层面。该种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等展布出来。与文化的其他特征相比,规范特征常为主宰特征。不同的文化之核心差别乃规范特征的不同。”[7](P59)受殷海光先生上述论证的启发,本文归纳与提炼出文化的规范性作为研讨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研究视角。
文化规范性是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规范性广泛存在于各种主文化、亚文化甚至是犯罪亚文化中。从根本上看,文化的规范性主要体现为主文化所要求的文化规范,文化的规范性发挥作用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这种社会控制拥有法律、道德、宗教、习俗等广泛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文化规范性出发,不同文化间存在冲突的根源在于:每一种特定文化均对特定群体具有规范性,规范性要求人和社会遵从特定文化所要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在转型的多元社会中,一方面,传统的主文化从总体上已开始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逐渐失去效力、走向瓦解;但传统主文化的某些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依然存在,并发挥指导生活、规范行为的部分效力。而新的主文化仍然在形成之中,新的主文化中的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并未确立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转型社会中的人们不断地受新旧两种文化的规范、影响与控制,人们突然发现自身不知所措,社会出现了主文化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不同亚群体受不同亚文化的影响,犯罪亚群体受亚文化极端表现形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同时本身并不确定和稳固的主文化还要普遍地指引人们的行为,这样,在特定群体中出现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和对抗,冲突的实质是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从文化规范性的视角来看,文化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三、文化冲突: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开始重视、检讨和反思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的适用及与中国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开展了反对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8](P211)。将国外文化冲突理论中国化,就符合中国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并有助于构筑专属于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文化冲突论的理想图景。在我国,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主文化的文化危机
文化冲突始于文化的危机,文化危机是文化冲突的第一个环节。所谓文化危机,是指文化遇到巨大的挑战,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主体的文化认同发生动摇,致使现有的文化不再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引发人们对该文化的怀疑。[4](P125)在一般意义上,一个社会的文化危机主要指该社会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当代中国的主文化是国家和主流社会所信奉的一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复合、多元、变动的体系。因此,想准确界定其本质含义颇为困难,本文仅指出它包含的大致内容。我国主文化包括现行的主文化和曾经的主文化。现行的主文化包括新中国建立后提倡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曾经的主文化是指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所形成的文化。①追求现代化和实现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代价就是主文化面临深刻危机,我国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形成与完善阶段;而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文化和价值观念仍然对个人和社会发挥着现实的影响。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已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该种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心高度政治化、道德化。习惯于从政治和道德角度看问题,搞泛政治化。二是价值主体的单一化和价值运行机制的单向化。国家是全社会计划的决策者和代表者,是社会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主体。”[9]而体现上述文化特征的政策和措施在实践中还时有发生,这个曾经的主文化依然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由于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完善之中,传统文化快速瓦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主文化未得到彻底清除,所以中国现行的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
其次,由于现行主文化尚未完全成熟,受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不断减弱,个人与社会对主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在降低。
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十分广泛的情况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发性,决定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有优势,除在经济、科技领域需要向西方学习外,在思想和理念方面我国也仍需借鉴其有益成果,如法治精神就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舶来品。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必须在政治等领域保留自身的特色,而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糟粕须值得我们警惕。在社会转型中,西方文化的各种因素全面涌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并对我国本土文化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我国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西方文化的冲击势必影响、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激进思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的不合理因素对我国构成了污染和侵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也对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形成了挤压之势。于是,我国现行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遭到削弱,个人和社会对主文化的认同感受到影响。
最后,由于社会转型期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在文化层面出现了主文化的真空与文化认同的混乱。
为了满足新的需要,人们功利地抛弃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全面退却。传统文化的瓦解速度是空前的,而与传统文化过于迅速的瓦解相比,其他主文化的成熟不能一蹴而就,这往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样,在主文化中制约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出现了真空地带。主文化的真空意味着在文化认同上混乱的出现。各种西方文化、封建文化、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文化迅速占据了主文化遗留下的真空地带,造成了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混乱。于是,人们要么漠视各种规范、要么在生活压力下止步不前;人们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但更有可能接受不良文化的指导,实施社会越轨行为。文化认同混乱的出现看似是由于道德失控与教化不力造成的,但实际上源于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更源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开展。在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为诸多阶层,贫富分化凸现出来,转型的不平衡导致现代化大多停留于城市之中,并形成现代化的孤岛,城乡间差距由此拉大。这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致使社会趋于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出现断裂,致使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形成,导致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城市与农村分享迥然有别的生存方式,并加剧了主文化的危机。
(二)犯罪亚文化的滋生
人是文化的创造物,也是文化的拥有者和创造者。犯罪亚文化是犯罪亚群体所拥有的生存方式。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犯罪亚文化影响特定犯罪亚群体,对犯罪亚群体的分析有助于透视犯罪亚文化的滋生和蔓延。犯罪亚文化构成了犯罪滋生的温床。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的嬗变将导致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嬗变;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一旦形成又对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产生影响和制约。
经过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国已由计划经济变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僵化的社会结构发展为流动性与活力较强的社会结构,由封闭的社会变化为开明、开放的社会,由同质性超强的一元社会发展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多元、多样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广泛形成,并开始发挥着指引内部成员的作用;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开始逐步收缩,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由、自治成为趋势。于是,萌发、孕育亚文化的社会条件成熟了。一时间亚文化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如企业亚文化、大学生群体的校园亚文化、青少年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官员群体的官场亚文化、商业亚文化、监狱亚文化、民族民俗亚文化、农民工群体的农民工亚文化等。
犯罪亚文化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改革开放以来,犯罪亚群体拥有的犯罪亚文化开始在我国滋生与蔓延。具体说来,犯罪亚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犯罪亚文化与亚文化一样均来源于主文化,它们并不是与主文化完全隔绝的孤立部分,犯罪亚文化至少包含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如同树叶、树枝和树干的关系一样,只有树干的光秃秃的树木缺乏生机和活力,树木需要树叶和树枝的点缀;但任何树枝和树叶都源于树干、离不开树干所运送养料的支撑;同时,树枝和树叶也不能过分旁溢斜出、妨碍树木整体的健康发展,对影响树木整体成长的树枝和树叶,只能对其施以合理的修剪。因此,我国犯罪亚文化是随社会转型从主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分支和余脉。虽然犯罪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但犯罪亚文化也不是反对主文化的每一方面,而仅反对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和部分规范。如在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中,青少年人可能会反对主文化所认可的权威(如家长、老师),反对主流教育方式对自身束缚;但他们决不会全盘否定主流社会的一切,他们不会反感对财富与成功的追求,尽管他们可能采取犯罪的方式来获得成功,其实他们更渴望通过努力获得主流社会认可。
其次,与主文化不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通行于各个社会阶层和亚群体中;与一般意义的亚文化不同,犯罪亚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于其拥有不良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包含某些意识。
与主文化广泛流通于主流社会相比,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在特定群体内适用,这是构成特定亚群体的显著标志。犯罪亚文化专属于犯罪亚群体和潜在犯罪人,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些犯罪亚群体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犯罪组织等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包括一般的犯罪团伙和违法人群(群体、吸毒群体),还包括非组织性的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如农民工犯罪中的农民工),等等。
犯罪亚文化为犯罪亚群体成员提供在意识基础上缔结成的身份认同。作为犯罪亚群体的精神基础,意识“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而暴露和宣泄的根本对立于社会的精神现象的综合体,主要包括悖逆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主导文化的病态抗拒心理和犯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三要素。”[10](P240-241)作为犯罪人之犯罪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意识能对犯罪亚文化成员的行为方式、身份认同、人格与思想产生影响,能催生犯罪的发生与蔓延。在意识推动下,犯罪亚群体成员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一致的行为规范、价值规范、语言符号系统和亚群体专有的禁忌和仪式。这些犯罪亚文化因素构成了犯罪亚群体成员区分我们与你们、我们与政府的根本标准,是犯罪亚群体成员的身份标志,并促成了犯罪亚群体内部的稳定和身份认同。因此,犯罪亚文化能以意识整合犯罪亚群体,影响内部成员的人格、思想和行为,促使群体成员遵循犯罪亚文化而实施犯罪。
最后,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为犯罪亚文化的沉渣泛起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则为犯罪亚群体的滋生提供了现实条件。
犯罪亚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极端的亚文化形态,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在特定区域、群体中,犯罪亚文化的兴起往往意味着主文化的失效或部分失效;主文化在法律、道德、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充分体现和渗透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对犯罪行为的控制。主文化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规范层面的真空、混乱,这为犯罪亚文化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封建文化、暴力文化、色情文化、享乐文化、官本位文化等各种影响犯罪发生的不良文化因素,囿于上述不良文化因素的影响,犯罪亚文化的形成条件由此成熟。同时,社会分层、分化导致与主流社会相对应的亚群体陆续出现,主流社会信奉主文化,亚群体往往信奉亚文化甚至犯罪亚文化。信奉犯罪亚文化的群体主要由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团伙、各种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构成的社会底层群体等社会群体组成。各种犯罪亚群体是犯罪亚文化的现实载体。
(三)文化冲突的本质
在中国场景中,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表现为犯罪亚文化通过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违背、破坏主文化及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主文化通过法律等手段否定、制裁由犯罪亚文化催生的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因此,犯罪是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文化冲突的产物。这种文化冲突的本质属性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具有附随效应,该种文化冲突附随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并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冲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文化冲突是文化学中的文化冲突,即人类社会宏观层面新旧文化模式的更替,在我国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催生了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转型。在犯罪学中,文化冲突嬗变为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并继承了文化学文化冲突的普遍性、持续性、内在性、间接性、客观性、全面性等特性。所以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也可称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不能脱离一般意义文化冲突的影响,而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是基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对抗和矛盾;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强调通过文化转型使新的文化模式获得完善和成熟,进而催生社会的主文化,而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重视对主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关注文化对人和社会的规范作用,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注重犯罪亚文化和主文化对个人、社会的规范。故此,没有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就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也就没有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犯罪学的文化冲突是人类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在犯罪学中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一种附随产品。
其次,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发生于主流社会与犯罪亚群体之间,并直接表现为价值观念、心理及人格的对立,间接表现为犯罪与犯罪治理的博弈;该种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对立。
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还表现为主流社会和犯罪亚群体的矛盾;但在根本上,持主文化的主流社会和持犯罪亚文化的犯罪亚群体的矛盾和对立还是关于人之思想和行为的冲突。
最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由综合因素促成,在特定阶段人类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人类理性的态度是在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和完善日常性社会治理的前提下,维护主文化的权威和稳定。
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代价,只要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等因素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冲突就会长期影响犯罪问题。囿于冲突的长期性,文化冲突是无法通过人为手段加以消灭的。对待文化冲突的策略主要应放到对其的合理控制上来。其实,犯罪亚文化的存在也并不仅意味着混乱和威胁,亚文化存在的本身就是主文化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标志,主文化的长期稳定易形成僵化、迟滞的局面,所以主文化在应对犯罪亚文化冲击的过程中,需不断反省自身、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与犯罪亚文化的互动中求得发展与创新。
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既是相对的又是互动的,没有亚文化就不存在所谓的主文化,没有主文化也无法界定犯罪亚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完善,某种犯罪亚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会随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瓦解而自然地减弱和瓦解。但犯罪亚文化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因为造成犯罪亚文化的深层社会因素在某种犯罪亚文化源泉干涸的同时,马上又开辟了新的源泉和新的犯罪亚文化。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就是犯罪亚文化以及文化冲突存在的深层社会因素。为维护主文化及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日常性治理措施和策略合理地控制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将犯罪亚文化和文化冲突作为我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在日常性治理、法律制度及社会控制的框架下应对文化冲突。
四、余论: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与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存在特定理论限度一样,本文所论述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也同样存在分析限度。只有明确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才能有的放矢的应用该理论研讨犯罪问题,发挥该理论的最大效益。
犯罪的文化冲突论属于针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场景而发展出的理论模式,该理论主要研讨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故此,在社会类型上,该理论适宜分析主文化与亚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转型社会的犯罪状况,如当代中国社会;但对分析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的犯罪状况却明显不适宜,如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的犯罪问题就缺乏解释力。在犯罪类型上,该理论对分析处于各种犯罪亚文化影响下的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犯罪现象是适宜的,如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农民工犯罪、职务犯罪、白领犯罪等;但对较少或不受亚文化影响的群体或个体所实施的犯罪显然是不适宜的,如偶发性犯罪、激情性犯罪、精神病人犯罪等。在犯罪学体系中,文化冲突属于犯罪原因范畴,是犯罪综合性原因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冲突出发,有助于解释、分析特定类型犯罪的形成原因。根据社会类型、犯罪类型和学术体系方面的限定,本文所强调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主要适用于分析转型社会中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特定类型犯罪,并侧重于对上述类型犯罪进行原因性探究。
总之,在中国场景中,影响犯罪的文化冲突是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与矛盾。文化的规范性能扩展为犯罪亚文化的规范性和主文化的规范性,引申为对具体犯罪的规范性和对具体犯罪人、潜在犯罪人的规范性。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蕴涵在不同文化以其规范性影响和制约个人、群体并相互竞争和互动的过程中。这种犯罪的文化冲突论能够合理地呼应中国当代主流社会与各种亚群体并立的社会结构,能够揭示影响中国犯罪状况和犯罪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而形成一种分析中国犯罪问题的有力工具。
注释:
①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统文化的精华记载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这均属于主文化。实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文化作为存在了三十几年的文化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文化作为一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保持其稳定性和惯性,消除计划经济文化的不良影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美]索尔斯坦·塞林.犯罪:社会与文化[M].许章润,么志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何传启.什么是现代化[EB/OL]./html/Dir/2002/08/21/4717.htm.2007-5-25.
[4]李庆霞.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5][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社会类型论文篇(9)
一、问题提出
职业倾向是一个人的职业愿望,是对职业的一种自我表现概念,是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取向。它一般由人的知识、能力、性格、兴趣等主观因素决定。Holland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职业兴趣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可以划分为六种人格类型,即现实型(Realistic)、研究型(Investigative)、艺术型(Artistic)、社会型(Social)、企业型(Enterprising)和常规型(Conventional),与六种人格类型相对应有六种环境模式。环境的性质是其所属成员典型特征的反映,它提供了其相应人格类型个体发挥其兴趣与才能的机会,并强化其相应的人格特质,该理论将职业兴趣划分为六种类型,简称为RIASEC理论[1]。其中现实型(R)指喜欢有规则的具体劳动和需要基本技能的工作,但缺乏社交能力。适应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熟练的技能性职业(如修理工、司机、农民)和技术性职业(如制图、机械装配等);研究型(I)适宜科研和实验等工作,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工程师等;艺术型(A)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对艺术创作充满兴趣,喜欢通过艺术作品来表现自我。但不善于事务性工作;社会型(S)对社会交往感兴趣,关心社会问题,愿为社会服务,有教导别人的能力;事业型(E)适宜管理、决策方面的工作;常规型(C)喜欢系统而条理的工作任务,讲究实际,习惯按照固定的规程、计划办事。
人格的具体成分较为复杂和微妙,主要表现为一定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气质、性格 [2]。McCrae和Costa提出了 “大五”人格模型[3],即人格的五个因素,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公正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
外向性表示热情、自信,有活力,还具有幸福感和善社交的特性;宜人性表示利他、友好、富有爱心;开放性指对经验持开放、探求态度;公正性表示克制和严谨,与成就动机和组织计划有关;神经质主要依据人们情绪的稳定性和调节情况而将其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某处。刘继亮和孔克勤(2001)指出,个体在连续性人格变量或人格维度上存在差异,即人们之间的基本差异是量上而非质上,特质研究就是探究构成人格的基本特质的内容和数量,这与绝大多数特质论者的观点趋于一致,即人格的基本结构由五大因素构成 [4]。 McCrae & Costa编制的“大五”人格问卷NEO-PI,许多心理学家都根据自己的研究,重复得到了类似的因素,但在命名上存在差异。张建新等人(张建新,周明洁,2006)根据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了修订,提出六因素假说[5]。大五人格特质模型是对人格结构的一种良好描述,可以用于解释个体人格的差异性。
关于人格特质与职业倾向的关系,冯艳丹和张利燕(2007)指出:神经质与经营型存在正相关,与常规型存在负相关;外倾性与经营型存在负相关,与常规型存在正相关;开放性与研究型、艺术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社会型存在负相关,与常规型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宜人性与社会型存在十分显著的负相关;责任心与现实型、社会型和经营型存在负相关[6]。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许多研究集中在职业倾向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和中学生的专业选择等方面,结论也各有不同。本文立足于大学生,并以宁夏大学学生为样本进行研究是由于目前就业形式日趋严重,许多学生面临着职业选择的困境,了解大学生人格特质与职业倾向的关系,以期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指导。
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选取宁夏大学不同院系的270名学生,共发放问卷270份,回收问卷247份,有效问卷201份,回收有效率为74.3%。被试基本信息如表1。
表1 被试基本信息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性别 男 89 44% 教师 24 12%
女 112 56% 公务员 33 16%
专业 文学 52 26% 父母职业 商人 27 14%
理工 97 48% 工人 38 19%
经济 29 14% 农民 62 31%
艺术 23 12% 其他 17 8%
总数 201 100% 总数 201 100%
2.2 研究工具
2.2.1 “大五”人格量表
“大五”人格量表,Oliver P. John编制,后经黄希庭等于2002年翻译并修订。问卷用于测量人格的五个维度:神经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谨慎性。该量表的分量表及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均在0.75~0.9之间,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测量人格差异的有效工具。#p#分页标题#e#
2.2.2 Holland职业倾向量表
Holland职业倾向量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应用心理发展中心于1990年修订,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在0.72~0.86之间,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感兴趣的活动”、“擅长的活动”和“喜欢的职业”三个部分来测量被试的职业倾向。
2.3 数据处理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偏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3.1 职业倾向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性别大学生的职业类型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2:
表2职业类型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M±SD)
男(N=89) 女(N=112) t
实际型R 7.66±6.623 5.73±5.744 0.879*
艺术型A 7.63±5.151 8.21±4.028 -1.367
调查型I 6.96±6.131 5.93±3.977 5.138
社会型S 9.93±5.196 13.91±5.759 1.95**
事业型E 8.43±5.145 9.82±4.949 -0.406
常规型C 6.04±3.686 5.83±3.751 -2.176
注:* p<0.05 ** p<0.01
t检验结果显示:实际型R和社会型S这两个职业倾向类型在不同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艺术型A、调查型I、事业型E、常规型C四个职业倾向类型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3.2 职业倾向在专业类型上的差异比较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文科类、理工类、经济类和艺术类四个不同专业类型上的职业倾向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3:
文学(N=52) 理工(N=97) 经济(N=29) 艺术(N=23) F
实际型R 3.02±3.681 10.09±6.758 5.14±2.083 1.70±1.428 30.886**
艺术型A 6.87±4.059 7.35±4.407 7.00±3.798 14.17±1.193 21.192**
调查型I 3.25±2.589 9.21±5.483 6.24±1.864 1.74±0.689 35.047**
社会型S 13.65±5.372 12.48±6.245 11.07±5.331 8.70±4.226 4.478**
事业型E 10.38±4.348 9.08±4.825 10.14±7.530 5.87±0.344 4.866**
常规型C 3.85±2.173 7.82±2.997 6.76±4.549 1.57±1.441 39.228**
表3 职业倾向在专业类型上的差异检验 (M±SD)
注:* p<0.05 ** p<0.01
结果显示六种职业倾向在四个专业类型上的差异均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实际型R这一职业类型上除文学类和艺术类没有显著差异以外,其他各组之间差异均显著;在艺术型A上艺术类和其他专业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其他专业之间差异不显著;在调查型I上,文科类、理工类、经济类和艺术类各组之间差异均显著;在社会型S上艺术类与文学类,艺术类与理工类的差异显著,其他各组均不显著;在事业型E上艺术类和其他三个专业之间差异显著,而其他三个专业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在常规型C上除理工类和经济类这一组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各组之间的差异均显著。
3.3职业倾向在父母职业类型上的差异比较
对六个不同父母职业类型的大学生的职业倾向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4:
表4 职业倾向在父母职业类型上的差异检验 (M±SD)
教师(24) 公务员(33) 商人(27) 工人(38) 农民(62) 其它(17) F
实际型R 12.33±8.928 3.85±2.36 5.07±3.540 5.11±1.590 9.23±7.291 2.35±2.029 14.743**
艺术型A 7.13±1.513 10.64±3.16 10.85±5.134 7.95±4.119 6.52±4.605 10.41±4.988 5.348**
调查型I 10.08±4.680 3.55±2.373 13.41±7.329 6.37±2.889 8.48±6.388 2.35±1.320 12.768**#p#分页标题#e#
社会型S 14.75±5.479 11.45±3.410 4.30±3.635 14.03±5.375 10.18±5.779 10.82±6.376 3.927**
事业型E 11.42±2.062 7.88±4.878 7.19±6.077 9.00±6.994 8.23±4.178 10.06±5.018 2.605*
常规型C 8.63±2.618 2.76±2.208 3.52±2.622 7.68±3.111 6.97±3.324 1.88±2.497 21.761**
注:* p<0.05 ** p<0.01
结果显示,职业倾向在父母职业类型上的差异均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实际型R上,父母职业类型的教师组与农民组、公务员组、商人组、其它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农民组与公务员组、商人组、工人组;工人组与白领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其它各组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在艺术型A上,公务员组与农民组、教师组的差异显著、其它各组之间均不显著。
在调查型I上,教师组与公务员组、商人组、工人组之间差异显著,公务员与农民组、工人组之间差异显著,其它各组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在社会型S上,农民组与工人组、教师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其它组与教师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其它各组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在事业型E上,教师组与公务员组、农民组之间差异显著,其它各组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在常规型C上,教师组与公务员组、商人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公务员组与工人、农民、其它各组差异显著,其它组与工人、农民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其它各组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3.5 人格特质和职业倾向的相关分析
由于性别、专业类型和父母职业对职业倾向也有影响,因此以人格的五个因子和职业倾向的六个类型作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大五人格倾向和职业倾向相关系数矩阵(Partial Correlation) (N=201)
实际型R 艺术型A 调查型I 社会型S 事业型E 常规型C
外向性 0.005 0.421** 0.033 0.294** 0.42** 0.215**
谨慎性 0.152* 0.303** 0.257** 0.242** 0.146* 0.143*
宜人性 0.437** 0.132 0.245** 0.141* -0.061 0.079
神经质 -0.075 -0.157 -0.006 -0.346** -0.253** 0.028
开放性 -0.185** 0.584** -0.126 0.178* 0.068 -0.223**
注:* p<0.05 ** p<0.01
结果显示,外向性和艺术型A、社会型S、事业型E、常规型C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外向型和实际型R、调查型I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谨慎性和六个倾向类型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宜人性与实际型R、调查型I 、社会型S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其与艺术型A、事业型E、常规型C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神经质与社会型S、事业型E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和实际型R、艺术型A、调查型I、常规型C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开放性与实际型R、常规型C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和艺术型A、社会型S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调查型I和事业型E不存在显著相关。
四、讨论
4.1 职业倾向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
在实际型R和社会型S两个职业倾向上,t检验的结果表明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石丽(2004)的研究也表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实际型、社会型和常规型上存在差异[7]。霍兰德职业类型理论认为实际型得分高的人,往往喜欢摆弄和操作工具,机械,电子设备等具体有形的实物,不喜欢和人打交道的活动,厌恶从事教育性,服务性和劝诱说服性的职业,并且表现出看重具体事物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男生在动手操作能力上要优于女生,女生善于倾听,在了解别人、社会交往、亲和力等方面优于男生。因此男女生在这两个类型差异显著,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4.2 职业倾向在专业类型上的差异
根据表3,发现六个职业倾向在不同专业类型上的差异均显著。差异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专业的学生所学课程不同,学校对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要求及培养模式有很大的差异。理科类的学生所学的课程偏重于实际操作和研究;而艺术类学生则更偏重于审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塑造;文科类课程多倾向于书面及口头的表达能力的培养;经济类的课程则更多是对处事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塑造。
各专业类型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实际型R上,文学类和艺术类没有显著差异,这是由于这两个专业所开设的课程的性质有相似性,都注重审美能力和感性认识的培养,而不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在艺术型A上艺术类和其他几类专业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其他专业类型之间差异不显著。因为对艺术类学生的艺术能力要求高于其他学生,而其他专业类型之间在艺术能力上没有差异;在社会型S上艺术类与文学类,艺术类与理工类这两组的均值差异显著。从这三个组在社会型S上得分的均值来看,文科类和理工类在社会型上的平均分明显高于艺术类,这是由于理科类和文科类所受的专业训练与社会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而艺术类学生平时专注于艺术创作,在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上都相对弱于文科类和理工类。在事业型E上艺术类和其他三个专业之间差异显著,而其他三个专业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原因是艺术类的学生所学的专业专业性强,专业技能单一,在职业选择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事业型上得分低于其他两组。#p#分页标题#e#
4.3 职业倾向在不同父母职业类型上的差异
由于父母的职业特性不同所营造的家庭氛围不同,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也有所不同。受父母职业类型的影响,子女在职业倾向上会呈现出差异性。杨琴(2007)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拥有高的学历或渊博的知识,及良好的兴趣品质,如对美术、音乐、文学等擅长或感兴趣,孩子将从小受到良好的影响,知识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并可能继承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或所感兴趣的职业[8]。本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倾向在父母职业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研究具有一致性。
4.4 人格特质和职业倾向的相关关系
4.4.1 外向型人格与职业倾向
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与社会型和事业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张忠豪(2006)的研究也表明,外向性人格倾向与社会型和事业型职业类型之间存在较好的匹配性[9] ,原因是外向性人格得分高的人多表现为热情自信,善于交际。而社会型和事业型得分高的人则表现为对社会交往感兴趣,具有支配、劝说和使用语言的技能。因此外向性人格特质得分高的人,倾向于选择社会型和事业型的职业。
本研究发现艺术型A和常规型C与外向型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审美和生活品位的追求也逐步提高,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大部分人都会乐器,舞蹈等艺术类活动来丰富课余生活和精神世界。同时,受到宁夏就业现状的影响,大部分学生都倾向于从事常规型这样稳定的职业,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会选择考公务员,去做这样有规律且又稳定的工作。
4.4.2 谨慎性人格与职业倾向
本研究结果表明,谨慎性与常规型C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已有的研究也发现谨慎性维度上得分高的人,责任心强,做事有条不紊,高标准、严要求,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10]。同时,谨慎性和实际型R、艺术型A、调查型I、社会型S、事业型E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多是由于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大学生有较高的社会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因此谨慎性的人格特质对各个职业倾向类型的影响都很显著。同时也不排除被试在进行问卷调查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社会赞许性反应倾向,影响了问卷的得分。
4.4.3 宜人性人格与职业倾向
研究发现,宜人性人格与社会型S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因为宜人性表示利他、友好、富有爱心,得分高的人乐于助人、可信赖和富同情心,注重合作而不强调竞争。而社会型S得分高的人喜欢与人打交道,善于表达,喜欢倾听和了解别人,喜欢社会交往,亲和力强,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关心社会问题,有教导别人的能力,其典型的职业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因此宜人性人格特质往往对这样的职业类型比较感兴趣。
宜人性与实际型R、调研型I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究其原因,宜人性人格的个体为人和善,喜欢与他人合作而不喜欢竞争。而实际型R和调查型I这两个职业类型是竞争性相对较小的职业类型,因此大部分宜人性人格得分较高的个体就对这两个职业类型有更多的兴趣。
4.4.4 神经质人格与职业倾向
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个体感觉灵敏,感情脆弱,情绪不稳定,容易体验到心烦意乱的感觉[24],不适合从事与人接触的工作,适合做一些需要感性思维的工作,比如艺术创作。本研究结果显示,神经质与社会型S、事业型E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与理论假设是相一致的。
4.4.5 开放性人格与职业倾向
本研究显示,开放性与实际型R、常规型C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和艺术型A、社会型S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根据大五人格理论,开放性人格得分高的对经验持开放、探求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人际意义上的开放。这一纬度的特征包括活跃的想象力、对新观念的自发接受、发散性思维和智力方面的好奇。对于规律的,固定的,甚至呆板的活动表现出排斥态度,而更喜欢有创造性参与的活动。因此本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具有一致性。
五、结论
5.1 性别、专业类型和父母的职业类型对大学生的职业倾向有影响。
5.2外向性人格与艺术型A、常规型C事业型E、社会型S之间呈正显著正相关;
5.3谨慎性人格与人职业倾向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5.4宜人性人格与社会型S、实际型R、研究型I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5.5神经质与社会型S、事业型E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5.6开放性与实际型R、常规型C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和艺术型A、社会型S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参考文献:
[1] 方俐洛, 白利刚, 凌文铨. HOLLAND式中国职业兴趣量表的建构[J]. 心理学报, 1996, 2(28): 113~119.
[2] 张文新. 青少年发展心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35~66.
[3] McCrae, R. R., & Costa, P. T.,Jr.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Wiggins’ circumflex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6: 586~595.
[4] 刘继亮, 孔克勤. 人格特质研究的新进展[J]. 心理科学. 2001, 3(24): 294~296, 289.
[5] 张建新,周明洁. 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J]. 心理科学进展,2006,4.
[6] 冯艳丹, 张利燕.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职业兴趣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7, 2(15): 126~128.#p#分页标题#e#
[7] 石丽. 当代大学生职业兴趣研究[D]. 硕士学位论, 文苏州大学, 2004: 19~25.
社会类型论文篇(10)
两阶段论的形成
所谓两阶段论,即把古代奴隶制的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古代东方是早期的、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罗马是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它形成于30年代,是当时苏联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的产物。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一些年代里,由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尤其是反动的循环论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试图折衷地将马列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概念同循环论的观点相调和,急于断定古代东方为封建社会。有的学者甚至“发现”,古代两河流域的乌鲁卡基那时期是封建关系解体的开始时期,汉谟拉比统治时的古巴比伦王国是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国家,而新巴比伦王国则是大银行资本统治的时代①。因此,当20年代末苏联开始进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大争论时,史学界对于古代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的认性质问题,认识相当紊乱。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争论(第一次大争论)主要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进行,但持续到整个30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
① H.M.波斯托弗斯卡娅:《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1917—195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77—78页。
1929—1932年为第一阶段。这是争论最剧烈的阶段。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东方社会是否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当时,对于古代东方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问题,有三种说法: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封建制说和奴隶制说。奴隶制说是BB斯特鲁威提出来的。他原先也曾主张过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封建制说,后来经过对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史文献的研究,于1932年在苏联国这物质文化史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认为古代东方阶级压迫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奴隶制度,其主要支持者有 A.米舒林和B.阿甫基耶夫等。以上三说通过第一阶段的争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被否定了,苏联史学界确立了以下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能看作是独立的、区别于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否则就否认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法则,承认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在这个阶段,两阶段论尚未出现。
1933—1936年为第二阶段,争论主要在古代东方封建制说和奴隶制说之间进行。封建制说的主要代表者H.M.尼科尔斯基、H.M.卢里叶和A.H.久梅涅夫等。主张奴隶制说的最活跃者仍为斯特鲁威。他在1933年作了题为《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问题》的报告,1934年发表了大学教材《古代东方史》,系统地阐明古代东方社会是奴隶制社会。1937年,《历史家——马克思主义者》杂志编辑部组织《古代东方史》一书讨论时,写道:“斯特鲁威关于古代东方社会奴隶制性质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苏联专家压倒多数和承认和支持。”①通过第二阶段的争论,古代东方封建说也被基本否定了,奴隶制说开始得到公认。但是,主张古代东方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中也有分歧,斯特鲁威认为古代东方存在着发达的奴隶制,而米舒林和阿甫基耶夫则批评他没有区分古代东方和古典奴隶制社会的不同特点。米舒林在其为斯特鲁威《古代东方史》1934年版所写的前言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古代东方社会早期奴隶制性质的论点②。他说,“原始奴隶制形式”是古代东方国家奴隶制的典型形式,是“奴隶制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早在公社所有制尚未衰亡时就已开始形成;由于‘原始奴隶制形式’正好在东方国家中显得最富有生命力,于是阻碍了这种奴隶制变形的发展,使它不能达到古代奴隶制的更高形式”③。阿甫基耶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于是,这个阶段开始出现了两阶段论。
1937—1939年为第三阶段,争论集中在古代东方是否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争论中,关于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有了发展,并渐居上风,斯特鲁威也表示赞同。他在其《古代东方史》1940年第二版中,把古代东方史解释为原始的奴隶制社历史,而把古代希腊罗马解释为古代世界发展的最高阶段。阿甫基耶夫谈到两阶段论形成的过程时说:“从1933年起,与斯特鲁威同时,其他的苏维埃历史学家在古代东方史的专著中也提出并证明了下面的一个原理:在古代东方各国,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之上产生了奴隶制社会,但是
————————
① H.M.波斯托弗斯卡娅:《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1917—195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105页。
② H.M.波斯托弗斯卡娅:《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1917—195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1111—112页。
③ 转引自A.H.卡札玛诺娃《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克里特的奴隶制》,《奴隶制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50页。
这个社会里,奴隶制度并没有达到像在古希腊和罗马那样巨大的充分的发展。”①两阶段论在这个阶段获得了普遍的承认。
由此可见,关于奴隶制社会发展的两阶段论,是在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争论中,在苏联史学界摒弃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封建制说的同时,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对当时苏联史学界批判反动的循环论,反对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是有着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两阶段论把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对立起来,说古代东方社会的发展极其缓慢、停滞和落后,这说明它仍然受着西欧中心论的影响。
关于两阶段论的形成问题,史学界有种说法,认为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是在1938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斯特鲁威为适合斯大林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而“费尽苦心”想出来的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斯特鲁威是第一个提出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并断定其为早期奴隶社会的人,甚至把关于五种基本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当作他的发明而大加宣扬③。
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两阶段论形成的实际过程。两阶段论的形成不是始于1938年之后,而是在这之前;最早提出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观点的是米舒林,斯特鲁威后来加以赞同并详加论证。后一说还歪曲了历史,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确立,并为列宁所充分肯定的,怎么能归之于斯特鲁威的“发明”?首次明确肯定亚洲古代社会为奴隶制社会的,也不是斯特鲁威,而是恩格斯。恩格斯早在1887年就指出,在亚细亚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④。
二、两类型论的产生
所谓两类型论,即把古代奴隶社会划分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两种发展道路不同的类型。它产生于50年代,是针对两阶段论而提出来的。
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在苏联世界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两阶段论占据了统治地位,但随着古代世界历史研究的深入,两阶段论的模式和愈来愈多的新发现的史料相唐突。于是在50年代,开始有人对两阶段论提出怀疑和批评。
批评首先来自30年代主张古代东方封建制说的一批学者,他们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一次大争论中,曾先后表示放弃古代东方封建制说,而接受奴隶制说。然而,这个学派并未完全放弃其原有的学术倾向。“如果说,斯特鲁威学派主要集中研究和分析奴隶制的结
————————
①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第15页。
② 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年第1期。
③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24卷,1976年,第596页;B.H.尼基福罗夫:《东方和世界史》,转引自《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第17页。
④ 《马恩全集》第21卷第387页。
构,那么封建概念的拥护者则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研究处于公社形式中的自由农民经济。”①例如,尼科尔斯基这个被认为是古代东方封建说的最顽固的拥护者,在“表示信服1933—1936年讨论的基本结构的正确性,即关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性质的原则”之后,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租税、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占有制②。
50年代第一个提出两类型论观点的是卢里叶。他在30年代曾激烈反对古代东方奴隶制说,直到1939年仍认为古王国的埃及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后来,他虽同意古代东方是奴隶社会,但并不同意两阶段论。他在1952年和1953年写的关于《世界通史》一、二卷大纲的评论中指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不是相互交替的发展阶段,而是两个并存的奴隶制社会类型③。
系统地论述两类型论的是久梅涅夫。他曾是古代东方奴隶制说的最初反对者之一。在放弃古代东方封建制说之后,他致力于研究楔形铭文,阐明两河流域南部对于劳动力的特殊剥削形式。1956年,久梅涅夫发表了《古代苏美尔的国家经济》一书,认为在苏美尔各国,奴隶制的剥削是对国内基本居民(自由民劳动者)的剥削交织在一起的,初步表达了两类型论的观点。次年,他发表《近东和古典世界》一文,全面阐述了两类型论。他认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在社会制度及命运上的差异,不能归结为发展阶段的先后,而是发展道路本身的不同。他说:“在古代东方和古典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奴隶占有制的两个连续发展阶段,而是各具特点的两种奴隶占有制社会类型。”④久梅涅夫直到1959年6月去世之前,还撰写了几篇论文,重申并发展了这一观点⑤。
久梅涅夫的《近东和古典社会》发表之后,两类型论在苏联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由苏俄教育部核准、B.H.狄雅可夫和C.H.科瓦廖夫主编的师范学院历史系教科书《古代世界史》,其1952和1956年版,均按两阶段论编写,但1962版却批评了两阶段论,而接受了两类型论。该版古代东方部分的前言中说:“在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和国家具有某些专门的特点,这些特点同建立于希腊罗马领土上的古典奴隶制社会和国家,形成了对比。”⑥
————————
① ю.M.卡里斯亚查:《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苏联《历史问题》1966年第2期第95—96页。
② 《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第104、112页;阿甫基耶夫:《苏联对古代东方史的研究》(1917—1957年),《史学译丛》1958年第2期第23页。
③ 苏联《古代史通报》1952年第4期第172—173页,1953年第2期第233页。转引自苏联《历史问题》196年第11期第67页。
④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译文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2、3期。
⑤ и.д.阿姆辛《A.и.久梅涅地院士著作中的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载《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问题》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版,第14—17页。
⑥ 狄雅柯夫、科瓦廖夫主编:《世界古代史》,莫斯科1962年版,第60、80页。
两类型论虽是50年代提出来的,实际可溯源到30年代。久梅涅夫早在30年代的手稿中,就涉及到后来两类型论的部分观点①。两类型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30年代古代东方封建制说的拥护者。两类型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古代东方封建制说与奴隶制说两个学派长期调节器合的产物。它吸收了奴隶制说关于古代东方是奴隶制社会的基本主张,同时又保留了封建说关于自由农民是古代东方社会生产劳动主要承担者的观点。
应该承认,两类型论的提出,对于冲破两阶段论的陈旧历史模式,促使人们具体研究古代各国、尤其是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它又搞了一个新的历史模式,强调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走着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实际是向历史的二元论、朝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倒退了一步。无怪乎在6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二次大争论中,苏联一些主张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的学者,几乎一致抨击斯特鲁威而称赞久梅涅夫。我国主张古代东方封建说的同志,也肯定两类型论“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古代东方三是走着与古典世界大不相同的发展道路”②。
————————
① и.д.阿姆辛:《A.и.久梅涅地院士著作中的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载《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问题》一书,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63年版,第1417页。
② 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62页。
转贴于 三、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异同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之间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两阶段论认为,古代东方存在着双重的剥削形态:第一种是原始的家长制的剥削形态,其方式是由国家向农村公社的农民居民征收租税;第二种是奴隶制的剥削形态,这种形态是主导的、进步的,但它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大体上停留在家内奴隶制阶段。因此,古代东方社会是半奴隶制半家长制的社会,可称之为原始奴隶制社会,或早期奴隶制社会。而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奴隶制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充分的繁荣,因此,希腊罗马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便分属前后相承的两个奴隶制社会。
两类型论认为,古代东方经济基础的特征是,除了剥削奴隶劳动外,同时也极广泛地剥削当地居民——农村公社成员的劳动。后者是国内基本生产者,他们遭受奴隶制国家和奴隶主贵族的剥削,其残酷程度不下于对奴隶的剥削,这就是所谓的“普遍奴隶制”①。他们和战俘奴隶融合为一个共同的阶级,其间没有鲜明的界限。而在古代希腊罗马,一开始便走着发展私人占有制田庄的道路,剥削战俘奴隶即所谓最纯粹形式的奴隶制占绝对优势,而奴隶和自由民之间有一条鸿沟。因此,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是彼此相异的两种类型的奴隶制社会。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对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分析,而在于对古代东方社会的分析。对古代东方社会的分析,关键又在于如何理解古代东方自由民劳动者(农村公社成员)的地位问题。两阶段论把对这种劳动者的剥削解释为原始的、家长的剥削,它虽接近于奴隶制的剥削,但并不等于是这种剥削。由于这种原始剥削形式的存在,使古代东方一直处于早期奴隶制社会阶段,而未发展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两类型论认为奴隶制度之有别于其他剥削形式,不在于它的剥削对象的不同,而在于他们是怎样被剥削的。既然在古代东方,奴隶主对自由民劳动者的剥削不下于对奴隶的剥削,那么就应把这种剥削解释为奴隶制的剥削,将这种剥削制度称之为普遍奴隶制。希腊罗马则是剥削战俘奴隶的纯粹奴隶制。所以,两者的发展道路不同,奴隶制的类型不同。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具体研究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对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叙述时,却发现它们在基本的方面却是一致或者接近的。例如:
在土地关系方面,双方都认为古代东方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土地国有,而在希腊罗马,农村公社彻底瓦解,土地私有。斯特鲁威说,古代东方原始奴隶制社会与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原始公社制度残迹与家长制关系成分的保留,表现在农村公社之长期存在及其发展缓慢而停滞的状态”②。阿甫基耶夫也说,古代东方社会制度最重要的突出特征,就是它长期地保存了古代的农村公社③。久梅涅夫也认为,古代东方国家“占有全部被灌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将这些土地的大部分直接作为国家田庄,即充作王室和寺庙的田庄,而只把承袭占有权留给公社”④。
在阶级关系方面,双方都认为古代东方纯粹奴隶制不发达,战俘奴隶数量少,直接生产者主要为农村公社成员。不过,斯特鲁威等认为农村公社成员只是实际处于奴隶的地位,而久梅涅夫则把他们看作是普遍奴隶制度下的奴隶。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双方都认为发达的奴隶制或纯粹奴隶制在这里占优势,基本生产者是战俘奴隶或纯粹的奴隶,自由民被排挤于生产劳动之外。
在政治制度方面,双方都认为古代东方从一开始就是东方专制制度,希腊罗马则是城邦共和制度。斯特鲁威说,古代东方“部落领袖的权力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执政者的权力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古代阶级社会的原始专制制度”⑤。久梅涅夫也说:“在两河流域,氏族制度的瓦解以及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确立是在氏族贵族同专制政权作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随着专制制度的胜利,国家确立的过程也告完成。”而在希腊罗马,古典城邦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从来不加改变”。因此,久梅涅夫认为,古代东方“表现为东方专制制度形式上的上层
————————
① “ 普遍奴隶制”是借用马克思的话,见《马恩全集》第46卷第493,496页。其实,马克思使用“普遍奴隶制”只是一个比喻,说明在所有制的亚细亚形式(公社所有制)下,单个的人不有成为所有者,就好比被剥夺了财产的奴隶似的,并非说明东方奴隶制的特征。
② 斯特鲁威:《古代世界史选读》序言,见华东师大函授部编《世界史论文选辑》,1950年。
③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4页。
④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⑤ 斯特鲁威:《奴隶占有制度崩溃与封建主义形成的问题》,《史学译丛》1957年第1期,第161页。
建筑”,“必然估发生与古典城邦截然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作用”①。
在思想文化方面,双方也都认为古代东方的文化受宗教束缚,较古代希腊罗马落后。阿甫基耶夫说:“东方的文化比起希腊罗马的文化也同样是较为原始的,……由于宗教魔法世界观在古代东方占着统治地位,所以在那里只产生了科学底最初萌芽。在希腊和罗马,我们看到了科学和那想摆脱宗教桎梏的世界观都有进一步的大发展”②。久梅涅夫也说,在古代东方各国,“除要实行肉体压迫外,还要实行精神压迫,麻痹群众的思想意识。因此,这里的思想体系的发展没有超出旨在提高和建立专制政体的神圣威望的宗教思辨范围”。而在希腊罗马,“要保证对奴隶的统治,单是实行直接的肉体压迫就够了:监工的鞭子排除了对奴隶的心理进行任何思想影响的必要性。这种情况解放了希腊哲学家的思想”③。
以上种种关于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古典社会的差别的原因何在?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双方都首先而且主要归之于自然环境的不同。斯特鲁威认为,古代东方社会之所以和古典社会不同,是由于“主要的东方民族有以灌溉为其经济基础的缘故”。例如,“各公社加强团结以从事灌溉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产生了那形成东方专制制度形式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前提”④。久梅涅夫也认为:“在河流文化的国家里,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必须建立要求所有居民全都参加的庞大灌溉系统的建设。”⑤看来,无论两阶段论或两类型论,都是主张自然条件决定论的。
通过对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一系列共同点的分析,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二三十年代的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两阶段认和两类型论坚持人类社会五种基本经济形态的理论,坚持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性质的主张,这是和特殊形态论的观点根本对立的。但是,它们关于古代东方社会上述种种共同特点的看法,却和特殊形态论很相类似。
30年代的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者认为,从原始社会瓦解到近代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的社会是一种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这种社会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还用一种永佃制度转佃给人民,地租采取一种赋税的形式;
第二,全国分成无数的公社,公社都是各自独立的小社会;
第三,国家和官吏是社会事业的承担者,水利的掌管者,统治着那些各自独立的小社会,专制政权便由此而形成。⑥
特殊形态论者也是自然环境决定论者。他们说,东方社会的地理条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划出一个分水岭,水是亚细亚社会的主要基石,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也可称之为“水利社会”。
从水利灌溉事业之必需出发,导致古代东方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土地国有、东方专制制度,这些,无论是两阶段论或两类型论,都与特殊形态论相吻合。因而,30年代形成的两阶段论,虽然排斥了特殊形态论,但却不能真正从理论上和史实上驳倒特殊形态论;50年代提出的两类型论,尽管仍然认为古代东方是奴隶制社会,但朝特殊形态论倒退了一步。
————————
①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②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9页。
③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④ 斯特鲁威:《古代世界史选读》序言,见华东师大函授部编《世界史论文选辑》,1950年。
⑤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⑥ 参见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第8页。
四、关于古代东方的共同特点
从以上的比较可知,两阶段认和两类型论都认为古代东方社会具有和古典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即:农村公社长期存在,没有土地私有制,奴隶制(或纯粹奴隶制)不发达,东方专制制度,文化落后等。对这些所谓共同特点的具体分析,分别构成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基础。然而,历史事实却与这些“共同的特点”出入很大。
古代东方各国都长期保存农村公社,从而土地国有,没有出现土地私有现象吗?事实并非如此。农村公社是原始氏族公社晚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出现的社会基层组织。农村公社之内实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结合,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统一体是比较牢固的。进入文明时代后,它继续残留到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中。世界上许多地区和国家,如印度、爪哇、俄国、爱尔兰、苏格兰、德国、瑞典等,农村公社的部分残迹一直保留到近代,直至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彻底摧毁。但是,农村公社毕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①,它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和私有并存的两重性。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公有制必然走向瓦解,只不过由于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其瓦解的速度和程度有差别。如果认为古代东方各国农村公社都长期保存而不解体,那是片面的。相反,关于古代东方各国农村公社解体、土地私有的材料,日益大量地被发现。古代两河流域,早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苏美尔就出现了土地买卖,拉格什之王恩克格尔用铜、大麦等购买了土地150布尔(1布尔合6.35公顷)计952.5公顷②。阿卡德王朝的国王玛尼什吐苏在四个地方买了八项土地,其中七项(一项数字缺漏)总计合3158公顷③。加喜特时期的文物“界碑”,在当时是国王对其臣民颁赐土地的凭证,拥有界碑的所有者都是世袭的大地产所有主④。这些都说明了农村
————————
① 马克思:《给维·拉·查苏里奇的复信和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② G.A.巴尔吞《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室铭文》,转引自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页。
③ 贾可诺夫:《苏美尔》第71—79页,转引自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
④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0页。
公社土地公有制的被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到古巴比伦王国,村社份地基本上已是私有土地。两河流域奴隶主制订的一系列法典,都有严格保护土地私有制的条文。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纳姆法典》新发现的一条断片,就是处罚非法占有他人田地的①。在埃及历史上,买卖土地的最早记录是《梅腾自传铭文》,其中先后两次提到梅腾“他用酬金从许多尼苏提乌(国王的人)那里获得二百斯塔耕地”②。用酬金获得,即购买之意。被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作为土地国有典型的古代印度,也不乏有关农村公社瓦解和土地和私有的材料。《乔达摩法经》曾提到:“人通过继承、购买、分配、侵占或发现成为所有者。”③《政事论》中也有关于买卖土地的记载:“亲属、邻居、富人应依次购土地和其它财产。”④印度孔雀帝国时期,作为份地归各家耕种的农村公社土地,可以继承、出卖,自然基本上已是私有财产了。
古代东方的奴隶制主要是原始的家内奴隶制或所谓普遍奴隶制吗?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奴隶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文明时期后发展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古代各国皆然。奴隶制关系在各国也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之不同,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往往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特点,如有完全被剥夺财产、不能组织家庭、由奴隶主配给口粮衣物的所谓“纯粹的”奴隶,也有可领取份地、组织家庭及掌握少量财产的希洛特式的奴隶。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奴隶数量大量增加(来源于战争俘虏、债务奴役和海盗掠夺等),奴隶劳动日益深入各个生产领域,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却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时期,即苏美尔奴隶制城邦全盛时代,各城邦大都已经形成了奴隶制大经济。拉格什在乌鲁卡基那改革前夕,据и.М.贾可诺夫的估计,自由民人数与奴隶人数之比为3:1,而在神庙经济范围,则自由民与奴隶约为2比1,成年男子人数之比,则自由民与奴隶相近,神庙经济中的奴隶超过自由民⑤。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奴隶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王家经济系统的奴隶制农牧场和手工业作坊。古巴比伦王国也有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经济,而亚述帝国则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战俘出身的农业奴隶。在古代埃及,陆续发现大量关于战俘奴隶和奴隶制田庄、作坊的材料。如古王王国斯巴弗鲁曾“击破尼西人的境土,获男女俘虏七千,大小牲畜二十万头”⑥。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一次远征叙利亚,即俘虏十万一千多人为奴隶⑦。由于获得大量的战俘奴隶,新王国时期的奴隶制获得空前发展,奴隶劳动应用于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农业。印度的孔雀帝国时代,奴隶劳动不仅用作家内仆役,而且大量用于农业、畜牧业和酿酒、
————————
①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编《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5页。
② 《古代东方史文选》,莫斯科1963年版,第27页。
③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1页。
④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14页。
⑤ 贾可诺夫:《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国家制度》第37页,转引自《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160页。
⑥ 日知选译:《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第8页。
⑦ 《古代东方史文选》,莫斯科1963年版,第98—99页。
榨油、纺织、建筑、采矿等。史料表明,印度同样有使用大批奴隶的私人奴隶制大田庄,其中的一个稻田农庄,面积达一千迦梨沙(一迦梨沙近似一英亩)①。
古代东方一开始就是君主专制,而希腊罗马始终是城邦共和政体吗?非尽然。在两河流域,约当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一些苏美尔城市国家,即奴隶制城邦。城邦的首脑EN,尚不是国王,而是执政,此外还有人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因此这些城邦最初并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贵族共和国。有的城邦如乌鲁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由人公民男子组成的人民大会,因此可能接近于奴隶民主共和国②。苏美尔城邦的历史长达约千年,经阿卡德王国的过渡阶段,到乌尔第三王朝才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原来的城邦成为地方单位。在埃及,古王国之前有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州”(城邦)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也并存在什么东方专制主义,贵族统治是基本的政治形式,直到古王国时才开始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在北部印度,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其中大的有十六个。小邦大多是共和国,和希腊城邦很相类似,其余为君主国,可能也是由小的共和国发展而来③。同样,希腊罗马也经历了由城邦发展到帝国、由共和制发展到君主专制的过程。马其顿统治时的希腊、恺撒独裁后的罗马,都是专制制度。因此,专制主义并不一定产生在东方,城邦共和制度也不一定限于希腊罗马。地域概念和政权形式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列宁说,最初出现的奴隶制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起来的”④。两河流域的城市国家,埃及的“州”,或者希腊罗马的城邦等,就是这样的国家。最初的奴隶制国家机器,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的机构脱胎演变而来,因而往往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残余,表现为自由民内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原始民主制的色彩,政权形式具有共和制的特征。后来,随着奴隶主对外征服扩张,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奴隶主阶级逐步抛弃各种形式的民主外衣,采取赤裸裸的奴隶主君主专制。如果仅把专制制度当作古代东方的特征,而城邦共和制度当作希腊罗马的特征。岂不是截去了两河流域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城邦历史,砍掉了希腊罗马数百年之久的帝制时期!
至于古代东方的文化,是否如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所说的那样“原始”、“落后”,科学知识仅有“最初萌芽”?回答也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人类最早的太阳历产生于埃及,太阴历产生于两河流域,零的符号最早出现在印度,字母文字最早出现在腓尼基。无论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科学领域,古代东方都有着巨大的成就,对世界文明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学方面,两河流域有可与希腊罗马史诗相媲美的长篇叙事史诗《吉尔伽美什》,印度的大型诗篇《腊玛延那》和《玛哈帕腊达》更是闻名于世。
————————
① E.B.考埃尔主编《佛本生经》第4卷第175页,转引自《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405页。
② 据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译文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31—37页。
③ 参见《古代印度和印度文明》,伦敦1951年版,第88—93页。该书英文版译自法文。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48页。
虽然,古代东方有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受宗教的影响较大,但也不是没有出现“想摆脱宗教桎梏的世界观”。就说宗教势力特别强大的古印度吧,其列国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国家,曾出现过如同雅典古典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有所谓六大师、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学派或教派)。其中,顺世论哲学主张世界由地、水、风、火四大元素组成。该学派用物质来解释人的形成和意识的存在,否定了一切宗教和唯心论哲学所主张的灵魂独立存在等谬论,从而根本上打击了宗教的造业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教,反映了人民大众的世界观。它和婆罗门教、佛教等唯心论宗教哲学是根本对立的。而在希腊和罗马,奴隶主对奴隶也并不限于肉体压迫,同样要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宗教)实行精神压迫,麻痹奴隶们的思想意识,以维护其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把基督教变为国教,就是一个例子。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还以大河流域的水利灌溉为出发点,把古代东方与希腊罗马区别、对立起来。可是,他们所谓的古代东方的范围,却不仅包括大河流域,而且把大片非大河流域地区包括了进去。他们所谓的由于灌溉事业所需而产生的专制制度,也出现在非大河流域的希腊罗马;而类似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共和国,也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恒河和印度河等大河流域的文明初期出现过①,其经历的时期甚至比希腊罗马的城邦更长久。他们所谓的大河流域地区公社长存、土地国有、奴隶制(或纯粹奴隶制)不发展等特点,正为日益增多的史料所否定。可见,以地理条件决定论来区别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是行不通的。
古代世界各国奴隶制社会,遵循着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经历了产生、发展、繁荣和衰亡的过程,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虽然其中的某些地区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在这样那样的方面出现相似之处,但在整个所谓古代东方,并不具有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所认定的为早期奴隶制或东方类型奴隶制社会的那些共同特点。古代东方地区的农村公社已经逐步解体,土地私有制出现了而且有了发展,奴隶的劳动不但使用于奴隶主的家务,而且日益广泛地使用于各个生产领域,包括使用于私人大田庄。古代东方许多地区在专制主义形成之前,也有或长或短的城邦共和时代,其文化并不都具有宗教神学色彩。因此,如果像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那样,把古代东方看作是和古典世界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或发展道路不同的两种类型,显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
① 近来有些研究者认为,古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着城邦共和制度,如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五、关于古代世界的二分法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在分析古代世界历史时,采用的都是“二分法”,即把古代世界分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或则作为两个阶段,或则作为两种类型。
古代世界的二分法,是西欧和俄国史学的传统。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渊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希腊人首先把自己作为西方的代表者,而与东方相对称。最初,希腊人所说的东方,仅指波斯,后扩展到所有位于希腊以东的地区。罗马人沿用东方、西言的术语,拉丁文"Oriens”,意为“日出处”,转义为“东方”;与它相对称的"Occidens",意为“日没处”,转义为“西方”①。对罗马人来说,东方是指所有位于意大利以东的地区,其中包括希腊。此后,东方与西方的术语便渐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西方通常指欧洲,但主要是指西欧;东方通常指亚洲和北非,但有时也将东欧包括进去。
到了近代,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掠夺的加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历史家为适应殖民主义的需要,把西欧说成是世界的中心,人类命运的主宰,而东方则被说成是一贯落后、停滞、野蛮,理应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于是,对他们说来,历史就是解释两个仿佛根本冲突的文明——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自身无能发展的东方。他们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出发,只看到当时亚非地区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的一面,而故意抹煞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古代先进文明,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起,才开始了真正的历史”②。显然易见,西欧资产阶级的世界二分法的核心,是西欧中心论。黑格尔正是从西欧中心论出嫁,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四种王国: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日尔曼的。在黑格尔那里,古代世界被分为二个部分:东方和希腊罗马。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把古代世界二分为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世界。俄罗斯东方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BA图拉耶夫1913年著有《古代东方史》大学教程,把古代东方史的编年范围一直叙述到“希腊化时代”的后期。
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学家继承了西欧和俄国的这种传统,不过把古代东方的范围逐步扩大了。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古代东方史主要指近东各国古代,即所谓“古典东方”的历史,印度和中国古代史一般不包括在内。苏联的历史学家开始把印度和中国纳入古代东方国家范围之内。几十年来,尽管古代世界各国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展,他们则只是将古代东方所包括的地理范围,由小亚扩至外高加索,由伊朗扩至中亚,由印度扩至中国,希腊罗马以外的古代世界几乎都被囊括进古代东方的地域概念之内,从两阶段论到两类型论,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一次大争论到第二次大争论,都丝毫未能触动这种二分法。1979年苏联出版的大学教材《古代东方史》,其序言中仍然把古代世界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两大部分,并且继续认为古代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缓慢,经济停滞不前,劳动分工不深入,奴隶制关系深度和广度不及希腊罗马等,基本上还是两阶段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本来是继承西欧和俄国关于古代世界二分法的传
————————
①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第19卷,1978年,第174页。
② 德国赫尔达(1744—1800年)的观点,见《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1980年第2期第157页。
统,但其首倡者却力图指导它们说成是马克思的主张,甚至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根据之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他们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即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看作如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那样,是社会经济形态先后演进的二个时代,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奴隶制社会的先后两个阶段,或并列的两种类型。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他在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表述①,其中心内容是所有制的亚细亚形式,即农村公社公有制。它不中一个地域性概念,而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②。因此,把马克思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未必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根据之二是,马克思曾在一些著作中谈到过东方社会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专制主义等特点。他们认为,这些特点也就是古代东方早期奴隶社会或奴隶制社会东方类型的特点。然而,这些特点,马克思主要是从东方封建社会归纳出来的。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它们是否是东方社会的特点,或则产生怀疑,或则予以否定③。例如,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但在同月十四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印度的土地国有制已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印度克里什纳以南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马克思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多次提到印度有私人土地所有制,事实上否定了印度的土地国有制④。因此,把上述特点说成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是缺乏根据的。
我们在前面讲到,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不赞同特殊形态论,却又在一系列观点上和它相雷同,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采用西欧和俄国史学的古代世界二分法的传统,并把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后来自己已经怀疑或者予以否定的关于东方社会的一些提法当作古代东方社会固有的、不变的特点,加之于除希腊罗马以外的古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是,特殊形态论将东方社会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分割出来,认定它是既不同于奴隶制,也不同于封建制的特殊的亚细亚形态的社会;两阶段论则把所谓亚细亚社会的特点,当作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特点,两类型论也只不过把它解释为东方类型的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所以,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不可能真正摆脱特殊形态论的影响,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它。
————————
① 参见詹义康《从历史发展阶段的三种提法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争鸣》1981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③ 参见马克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看法》,《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④ 《马恩全集》第28卷第256,272页;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第35—36页。
当前国内外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一些人的基本观点和二三十年代的特殊形态论相同。有的人则走得更远,如意大利梅洛蒂教授加进了一个马克思没有提到过的新成分——实行所谓“普遍农奴制”的“官僚集体主义”。他认为在一些所谓亚细亚或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埃及等,只有经过“官僚集体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为“官僚集体主义”制度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古代世界历史的二分法传统,从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古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特点的具体研究,并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以尽可能得以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而不是先验的结论,这样,才能有力地用历史事实来反驳特殊形态论。
社会类型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68-03
一、社会变迁理论的研究脉络
国外对社会变迁理论的研究,就社会转型道路而言,大致经历了一元论、怀疑一元论、多元论三个阶段。[1](P40-41)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进入到工业社会,人们开始关注社会转型问题,包括转型的道路、模式和机制等基础理论问题,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和摩尔根。他们倾向于类比生物体的进化,认为社会转型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混沌到有序的上升运动;其转型道路是一元的,在不同社会只有快慢之分,没有因果序列之别,具有统一的转型模式;转型因素可以是宗教、道德或技术的,但最终社会发生整体、全方位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认为每种文化类型各不相同,其转型道路也并非是一元的,对欧洲中心主义一元论提出挑战,建立了多元文化史观;另一方面,为了寻求对经典一元论的支持,怀特、斯图尔特、萨斯林和塞维斯试图在承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寻求内在本质上的同一性,研究转向了古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编纂学等实证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停滞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转型的本质。史蒂文瓦戈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变迁意味着某种特征的改变。汉斯·格兹和怀特·米尔斯认为,社会变迁是指一段时间内,角色、制度或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的出现、发展和衰落方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2](P2,6,8-9)
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3](P32-33)可以看出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的变动视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
在国内,李培林较早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转型问题。[4]他认为,社会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型变动,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它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它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三是指它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 [5](P42)陆学艺在总结西方学者有关社会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将我国社会转型概括为“六化”。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二是社会转型即城市化;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制;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动机受宗教或情感的因素支配转化为遵循普遍的理性原则。
二、价值观意义上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