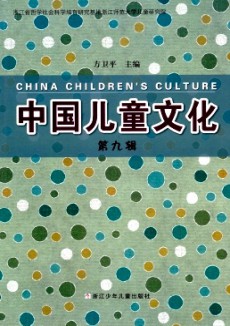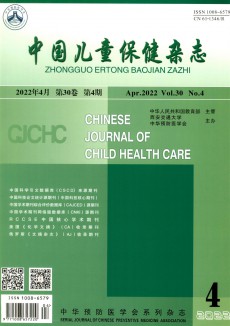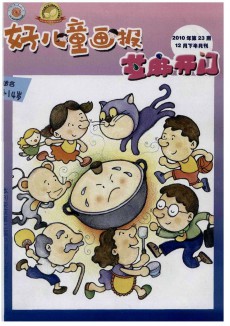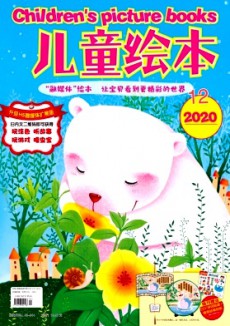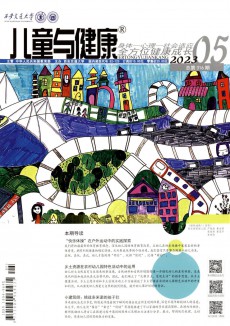儿童安全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7 16:40:50
篇(1)
2结果
2.1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不同性别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与心理韧性的得分差异
留守儿童在心理安全感的确定控制感、人际安全感及总体安全感各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P值均<0.05);留守儿童在心理韧性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等因子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P值均<0.05);在积极认知因子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在目标专注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上,留守男生得分低于留守女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其余维度或因子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2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与其心理韧性得分相关性
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中确定控制感、人际安全感及总体安全感各维度得分与其心理韧性的各因子得分均存在显著相关(r=0.123~0.397,P均<0.05)。见表2。
2.3留守儿童心理韧性与心理安全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与其心理韧性的关系,以安全感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心理韧性的个人力、支持力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enter法),结果发现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和支持力对确定控制感、人际安全感及总体安全感均有显著回归效应,Beta值(绝对值)在0.121~0.440之间,解释因变量变异在21.5%~23.5%之间(P均<0.05)。
3讨论
3.1遵义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及心理韧性水平令人堪忧
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总分以及确定控制感、人际安全感维度上得分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结构缺失、亲子关系分离,留守儿童与其父母缺少沟通和交流的机会,进而无法体验到父母的爱和家庭的温暖。霍妮的基本焦虑理论认为,从小缺乏父母的爱和家庭的温暖的儿童,就会产生不安全感。本研究还发现,留守儿童在心理韧性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等因子及个人力和支持力因素得分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父母,迫于生计,往往很少有时间与其子女沟通交流,加之中学阶段的儿童恰好刚进入青春期,各种身体内部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均有可能导致其心理变化,亲子关系分离、临时监护不力、学校补位不足,以及社会教育的缺乏等内外环境现况难以满足留守儿童支持性资源的需求,这从根本上阻碍了其心理韧性特质的发展和形成及心理安全感水平的提高。
3.2留守女童较留守男童在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上水平更高
留守女童目标专注水平之所以较留守男童高,可能与不同性别个体心理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从心理发展上看,女生较男生心理发展水平更快,心理相对更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讲,心理越成熟越有利于个体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朝着目标前进。本研究还发展,留守女童的积极认知水平较留守男童更高。CKMalecki等的研究认为女童可以知觉到更多来自朋友的支持;辛自强等的研究也发现,女中学生所知觉到的社会支持要高于男中学生。当然,这同样与个体的性别差异关系密切。
篇(2)
一儿童病区定期开展小组活动
2013年,社工部在为患者组织小组活动时,确定了活动的目的类型:支持型和教育型,在活动中让患者之间获取心理支持,同时获得健康教育的知识。在社工们近一年的摸索中,小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几乎所有的社工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小组活动主要覆盖在成年患者身上,而儿童患者群体中却缺少类似的项目,即使儿科也有由社工组织的活动,但大多集中在六一联欢会、不定期的游戏上。如何在儿童病区定期开展小组活动,活动内容的选题又该如何选择,这个问题摆在了社工部的面前。亚心医院是一家大型的心脏病专科医院,开放床位达788张,其中儿童病区床位111张,主要收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这些患儿大多集中在0-10岁之间,多数孩子来自农村,父母在外地打工,其中不乏留守儿童;而心脏病患儿的疾病特点、手术方式及术后恢复等让其住院时间在7-20天左右。社工们通过分析患儿的家庭特点、年龄特点,同家长们积极进行交流,同时征求病区医护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将活动的内容定在儿童安全教育上。但社工们日常的工作十分饱和,专门开展此项活动有一定的难度,于是,她们想到了和志愿者团体合作。经过积极的对外联络,社工部与武汉英中学校的“1+1”志愿者社团取得了联系。社团成员均为16-18岁的高中生,而他们志愿者服务的项目之一正好是由国际儿童安全组织支持的“儿童安全教育”项目,项目内容涉及:溺水安全、交通安全、高空坠落、触电安全等。他们将知识做成小品、拼图和幻灯,每周六的下午,在9楼儿童病区里,社工们提供活动场地、多媒体播放,指导志愿者们招募患儿及家长参与活动。他们们绘声绘色的表演,夸张捧腹的肢体动作,让患儿及家长们在娱乐的同时获取了知识;活动中,志愿者们邀请患儿们一起拼“安全拼图”,看安全画册,进行安全知识提问,对回答正确者发放小礼品,极大地鼓舞了患儿及家长参与安全教育的积极性。
二因地制宜进行儿童安全教育
通过几期活动的摸索,社工部对活动内容进行了分类式创新。“1+1志愿者社团”为患儿们所提供的安全教育知识,大多是生活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而在医院里,医护人员所关心的安全问题与生活中又有所不同。于是,社工们带着相机走进病区,在医护人员们的建议下,拍摄了一套适合院内安全教育的图片。如坠床、跌倒、烫伤、服药安全等,图片中的设施、场景均为患儿及家属熟悉的病房,辨识度极高。而在志愿者的选择上,则利用医院附属的护理学校资源。护理学校的代课老师大多为亚心医院护士长兼任,她们对医院环境、安全的管理非常熟悉。社工部将图片制作成幻灯,老师对学生志愿者们进行培训,结合儿童病区现场观摩见习,每周对住院患儿及家长们进行安全教育,既丰富了患儿们的住院生活,学到了安全知识,同时也帮助临床护士们减少了一部分的宣教时间。自2013年年底至今,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达50余次,惠及住院患儿及家长近900人次。一直以来,许多观点都认为儿童安全教育应由家庭、学校(幼儿园)为主,社会支持层面大多是邀请交通、消防等部门到学校进行宣传讲解。然而,通过我们一年多的尝试与摸索,发现对于儿童聚集程度较高、停留相对时间较长的住院儿童病区来说,根据疾病诊疗的周期特点,由医务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携手,共同进行儿童安全教育的方式值得尝试与实践。
作者:任军 单位: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社工部
篇(3)
依恋是儿童早期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关系,它对儿童身心发展尤其是社会性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依恋的研究一直受到发展心理学家的重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流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依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一、依恋概念的提出和依恋发展的阶段
1.依恋概念的界定
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贝(J.Bowlby)于1969年最早提出了依恋(attachment)这一概念。①所谓依恋指的是抚养者与孩子之间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联结。在这里抚养者主要是指母亲。杨丽珠提出,依恋是指婴幼儿对其主要抚养者特别亲近而不愿意离去的情感,是存在于婴幼儿与其抚养者(主要是母亲)之间的一种强烈持久的情感联系。②近年来,张文新又提出,依恋一般是指个体的人对某一特定个体的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系。③可见,依恋的主体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可以是儿童,也可以是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看护者;依恋的客体或对象一般是能形成对主体的情感呼应并与之建立强烈情感联结的特定个体,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群体。在发展心理学中,依恋特指婴儿与成人(父母或其他看护者)所形成的情感联结。
2.依恋发展的阶段
儿童依恋心理的发展同其他心理现象的发展一样,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许多研究者依据对儿童依恋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依恋发展的阶段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谢弗和爱默逊(Schaffer & Emorson)提出的阶段模型及鲍尔贝的依恋阶段论。
谢弗和爱默逊从儿童依恋对象的选择性,即依恋行为的指向性发展的角度,将儿童早期依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非社会性阶段(O~6周)。该阶段儿童只能发出哭、笑等无定向的信号。(2)无分化的依恋阶段(6周~7个月)。该阶段儿童会对任何入发出信号并从中得到安慰与关注。(3)具体依恋阶段(7~11个月)。该阶段儿童的依恋集中指向特定的个体,依恋行为的组织也更具有选择性。④
鲍尔贝根据儿童行为的组织性、变通性与目的性发展的情况,把儿童依恋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前依恋期(0~3个月)。这期间婴儿对人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他喜欢所有人,最喜欢注视人的睑。(2)依恋关系建立期(3~7个月)。这期间婴儿对母亲和他所熟悉的人的反应与对陌生人的反应有了区别。婴儿在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出更多的微笑、啼哭和咿咿呀呀。对陌生人的反应明显减少但依然有反应。(3)依恋关系明确期(7个月~2岁)。这一时期儿童对特定个体的依恋真正确立,出现了分离焦虑与对陌生人的谨慎或恐惧,出现了对人的持久的依恋情感,并能与人进行有目的的人际交往。(4)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2岁以后)。这时,婴儿开始考虑母亲的愿望、需要和情感,认识到母亲的离开是暂时的,并不是抛弃他,母亲是爱他的,并与之建立起双边的人际关系。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婴儿在1岁左右都能与抚养者形成某种依恋关系。
二、依恋形成发展的理论
对依恋的实质及依恋作用的心理机制,发展心理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依恋理论,主要有精神分析的依恋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的依恋理论、习性学的依恋理论、认知学派的依恋理论。
1.精神分析的依恋理论
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依恋起源于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婴儿的喂养,喂养时母亲与婴儿相处的方式决定着婴儿的依恋性质,健全的依恋来自母亲给予的温暖、宽容和充满感情的照料。依恋就其实质而言,是儿童对能满足其生理需要,为其提供快乐与舒适的抚养者的一种情感联结。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较早期弗洛伊德主义者更强调入的社会存在性,认为婴儿与身边重要他人的关系决定着依恋的质量,如果缺乏这种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儿童将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社会化。但他们都强调儿童的生理因素在依恋建立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都认为父母对儿童生理需要的满足是依恋的起源和基础。
2.社会学习理论的依恋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虽接受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某些观念,也把喂养看作依恋确立的决定因素,但是它摈弃了本能力量在儿童早期亲子关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注重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突出亲子双方社会经验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学习论者看来,依恋实质上是指母亲满足儿童基本需要而获得的二级强化行为。也就是说,母亲反复与婴儿的生理需要满足相联系,减少了婴儿的基本内驱力,于是母亲的在场、微笑、声音获得了二级强化的性质,母亲就成了婴儿的依恋对象。
3.习性学的依恋理论
鲍尔贝是一位深受习性学影响的精神病学家,他在习性学的基础上整合了精神分析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精神病学理论,创立了自己的依恋学说。他系统地论述了依恋产生的生物基础、依恋的阶段性发展及其内部机制,还对依恋的主要特征作了分析。他指出依恋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生物根源。鲍尔贝在解释母婴依恋形成的机制时假设:人类进化过程中使婴儿产生了一种先天的倾向,即婴儿具有在无力照顾自己时发出信号(哭、笑、依附等)以吸引成人接近,从而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倾向,同时成人也具有对这些信号作出适当反应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依恋。在习性论者看来,依恋是一套生物学上的本能反应,它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其作用在于保护幼小,为他们提供一种心理安全感。习性学依恋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内部工作模型”来解释依恋的内在作用机制。鲍尔贝指出,儿童在与他人交往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型”,其实质是儿童对自我、重要他人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种稳定认知。此外,习性学依恋理论还看到了依恋作用的双向性,改变了传统上只重视婴儿对成人的依恋而忽视成人对婴儿的依恋的倾向。
4.认知学派的依恋理论
认知学派的依恋理论并不重视需要满足的作用,而是强调一些认知能力(如观察力、辨别力、记忆力等)对依恋发展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要想形成依恋,儿童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必须学会区分环境中不同的人,若缺乏这种能力,儿童既不会形成对特定对象的依恋,也不会产生怯生心理;二是必须具备认知永久客体的能力。认知心理学家卡根(P・Kagan)采用“图式”的概念来解释依恋的形成机制。⑤卡根设想,婴儿在交往中会逐渐形成一些人和物体的图式。当与图式相似的刺激物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出现时,婴儿会表现出愉快的情绪;当与原先图式不同的刺激物出现时,婴儿会产生兴奋、好奇或害怕的情绪。婴儿在6~9个月时已经形成对抚养者的专门图式,因此产生了特定的依恋。
三、依恋的类型
关于依恋类型的确定,美国心理学家艾恩斯沃斯(Ainsworth)⑥的工作最具有经典意义。他创设“陌生情景”,通过观察和分析婴儿在陌生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将婴儿的依恋分为三种类型:(1)安全型依恋(ecure attachment)。这类儿童在母亲在场时能安逸地游戏和探索,母亲离开时情绪出现困扰,但母亲回来后很快又恢复平静。他们对陌生人的反应比较积极,能顺利地与陌生人交往。(2)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这类儿童母亲在场或不在场影响不大,母亲离开时也并不表现出分离焦虑,实际上这类儿童并未形成对人的真正依恋。(3)抵抗型依恋(resistant attachment)。这类儿童似乎离不开母亲,母亲离开时极度痛苦,但母亲返回后又表现出矛盾心理,既想寻求与母亲接触,又在母亲亲近时生气地拒绝和反抗。后经研究表明,回避型依恋的儿童易成长为具有性和攻击的个体,抵抗型依恋的儿童容易表现出退缩。
1990年,有的学者提出依恋的第四种类型,即混乱的依恋或不安全一解体型依恋(djsorgamzedattachment)。这类儿童在陌生情景中表现出杂乱无章和缺乏组织的行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对抚养者表现出恐惧、过分任性。这类儿童容易发展成为精神障碍患者(Main & Solman)。
在日常生活中,儿童与主要抚养者在亲密的联系中尽量形成安全型依恋,有利于其人格和社会性的健康发展。要避免形成不安全型依恋,以免使儿童形成不健全的人格和精神障碍。
四、依恋的评估方法
我们怎样知道依恋已经形成?如何考察依恋的不同类型?
1.“陌生情景”法
美国心理学家艾恩斯沃斯及同事1969年首创了“陌生情景”法。他们利用儿童对分离的反应以及儿童在中等压力之下接近依恋目标的程度和由于依恋目标而保持安静的程度,设计了七个情节(见表1)。
通过观察婴儿在陌生情景中的反应和行为表现,艾恩斯沃斯将母婴依恋的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抵抗型。
2.儿童依恋行为的分类卡片
我国学者通过修订沃斯特一迪因(Waters &Dearies,1985)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Q―Set,并进行信度检验,制作了适合中国儿童依恋安全性指标的分类卡片。Q―Set分类卡片共有90个条目,有些项目描述的行为是安全依恋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表2中的前3条),有些项目描述的行为在安全依恋中很少出现(表2中的后2条),另外一些项目描述的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通过吴放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Q―Set分类卡片适合中国儿童依恋类型的检测。Q―Set分类卡片使用方便,一般了解儿童行为的成人只需经过简单的训练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到目前为止,Q―Set分类卡片已被广泛地运用于评价儿童与母亲的依恋行为,并开始被用来评价儿童与保教人员之间的依恋关系。
五、依恋研究的新进展及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依恋研究向纵深推进,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从认知、人格、神经生理等方面深入考察了依恋的心理机制;二是对依恋类型的分布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三是依恋在精神病理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研究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依恋类型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差异。依恋在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儿童成长环境中的高危因素;二是关注不安全依恋与儿童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依恋对儿童心理和精神发展的影响,对儿童家庭教养和儿童精神治疗都有一定的实践作用。
综观前人对依恋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众多研究范围狭窄;对依恋机制探讨不足;研究方法缺乏生态效度,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扩大研究范围,探讨依恋的作用机制,指导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Bowlby J.Attachment and Loss.V01.1,Attachment,New York Bassic books,1969
[2]杨丽珠.幼儿社会性发展与教育,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劳拉・E・贝克.儿童发展.吴颖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Kagan J.,Snidman N.Temperamental Factors inHuman Develop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46:856~862,1991
篇(4)
我觉得他对“当代意义”的关注,有一种超越“当代”的意义。比如他谈“任溶溶的意义”、谈“安徒生的当代意义”等等,他的心中似乎充满更多的激情。在《任溶溶的意义》这篇精短论文里,他是那么动情。他认为,任溶溶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任溶溶对中国幽默儿童文学的重大贡献;二是任溶溶对汉语语词功能的创造性运用;三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今天,不要说整个社会,就是儿童文学界,对任溶溶这样的儿童文学大家,也还缺乏应有的尊崇和深度研究。这是不是也和当年人们并不知道安徒生的“当代意义”一样呢?那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安徒生是童话大师的今天,人们是不是又认识到安徒生的“当代意义”了呢?并不见得。
篇(5)
一年来,我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契机,采取集中学习、自学、座谈会、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组织骨干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学习xx同志在八次文代会和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精神,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学习心得交流,使会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二、工作扎实有效,活动丰富多彩
一年来,我会开展了对外交流、班子建设、举办比赛与讲座、创作研讨、发展队伍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我市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1)2月7日,创建“瑞安儿童文学”博客,设有作家介绍、会员新作、文学评论与学会信息等栏目,扩大会员交流与对外联络。
(2)2月22日,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听取上一届工作报告与财务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
(3)3月25日,创办《瑞安儿童文学》报。年内共编印三期,赠送给全国各地有关儿童文学作家和我市各中小学(含8所校园文学创作基地)。
(4)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以我会老作家张鹤鸣名义设立“童彤杯”张鹤鸣寓言戏剧奖,已向全国征稿。本会做好组织发动和瑞安市赛区的评奖推荐工作。
(5)联合举办全国第二届“乾有杯”校园寓言童话大赛,做好瑞安赛区的组织发动和评奖工作。
(6)加强对“校园文学创作基地”的联络工作,《瑞安儿童文学》报分别刊登红旗实验小学与万松实验学校作品专版。
(7)协助市文联举办文学事业发展研讨会、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聘请《少年文艺》主编任哥舒来瑞安指导,对会员作品进行点评。了解儿童文学创作新形势,探索新路子。
(8)鼓励儿童文学作家进校园,举办儿童文学讲座 8 场。
(9)继续发展壮大会员队伍,特别是优先发展中小学文学社团辅导老师,把热爱儿童文学创作的新人吸收到学会中来。本年度,共吸收新会员 8 名,小会员 4 名,并对部分会员进行重新登记发证。我会已经拥有在册会员143名,未登记老会员50多名。
三、会员努力创作,收获硕果累累
一年来,我会鼓励会员深入生活,努力创作,作品发表、出版、获奖硕果累累。《文艺报》《浙江日报》《温州晚报》等多家媒体介绍我会的发展与成绩。
(1)会员洪善新主编的《张鹤鸣儿童文学评论集》1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2)会员叶美红的个人儿童文学作品集的《怀梦草》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3)会员张鹤鸣主编的《小学生学会与人分享的80个好故事》6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4)会员雷本科编著的儿童文学作品集的《作文历程—我与学生一起写作文》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5)会员林新荣主编的《瑞安市小学生优秀作文选b卷》5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6)张鹤鸣任编选顾问,冰子、谢尚江任主编,多名学会骨干任副主编与编委的《创新作文选》由6月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7)本年度会员在《中学生读写活页》《寓言故事》《小学生学习报》《快乐童话故事》《小学生拼音报》《童话寓言》《小学生阅读》《学生·家长·社会》《开心幼儿画刊》《青年文学家》《语文报》《作文大世界》《新作文》《浙江日报》《儿童世界》周刊、《齐鲁少年》《儿童大世界》《意林》《中外故事》等报刊发表儿童文学作品190余篇。
(8)30多篇入选《2011中国最佳故事》《2011中国儿童文学年选》《中国经典童话》《2011小学生珍藏寓言》《小学生成长必读》丛书、《浙江儿童文学60年精品选》等权威选本。
(9)全国“牛年写牛”寓言擂台赛中,评出优秀作品奖10篇,本会冰子和洪逸梦的作品榜上有名;全国“双羽杯”童话寓言赛前赛中,评出优秀作品奖10篇,本会虞瑞超和洪逸梦的作品获奖;谢庆朋获第二届“新视野杯”全国文学征文优秀奖;谢尚江获第五届“作家杯”全国儿童文学写作大赛一等奖。
(10)本会有10名会员加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张鹤鸣当选为理事。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做好全国第二届“乾有杯”校园寓言童话大赛(瑞安赛区)的组稿和评审工作。
2.做好全国首届“童彤杯”张鹤鸣寓言戏剧奖(瑞安赛区)的发动推荐工作。
3.做好新会员的发展工作。
4.加强与创作基地的沟通,促进校园儿童文学的发展。
5.继续办好“瑞安儿童文学”博客,不定期刊出《瑞安儿童文学》报。
篇(6)
我国的儿童安全教育问题已被多次讨论,并在一些地方开始付诸实施:每年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被定为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安全知识得到进一步普及。这些措施显然很具有吸引力,但笔者更支持能够提供真正保护的方案。当今,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可以为儿童安全教育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息与服务。特别是儿童上网比例的增高,更为儿童安全教育网络形式防护儿童安全提供了可行性方案。2013年7月25日“首届中国(北京)儿童文化产业论坛”的《城市儿童生活形态(2012-2013)研究报告》显示,4-16岁儿童少年中,13-16岁的孩子上网比例最高,约有93.2%的孩子上网,4-6岁的孩子上网比例最低,但也有52.6%。7-9岁和10-12岁孩子的上网比例分别达到58.6%、77.1%。由此可见,儿童安全教育网站完全有条件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角色承担防护儿童安全的责任。基于这一职责要求,如何吸引儿童受众、如何控制儿童受众视线,让儿童安全教育知识得以传播、应用,从而真正做到防护儿童安全,是网站设计者及建设者不懈追求的目的。
1 视觉引导控制儿童受众视线
以儿童为受众的儿童安全教育网站,当图形、文字、视频、音频等内容吸引受众视线之后,如何通过视觉引导使受众认可该网站呢?
孩子们在收看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幼儿节目《天线宝宝》时,当出现小喇叭的声音,孩子们就会屏气凝神,充满好奇的等待着什么。在心理学中,这一现象称之为“刺激驱动捕获”,发生在刺激的特征――环境中的物体――自动抓住人们的注意时,它不依赖于知觉者当时的目的。
在网站设计中,立即吸引受众关注的视觉内容是通过刺激驱动捕获完成的,吸引注意力的内容也许是某处创意特别的动态效果,也许是突出的色彩,也许是形态别致的图标或文字……“”是美国一家儿童安全教育论坛,它主要通过音频、动画、游戏等形式传播消防、、枪械等儿童安全防护教育。进入网站,立即会被右上角的大斑点狗卡通形象吸引,它摇头摆脑,口吐人言,用可爱的形象、动态的效果和柔和的声音吸引受众的视觉关注。
网站界面关键的视觉关注点不宜过多,一般由一到三个视觉关注点组合成一个视线运动规律。如按照视觉关注点的图形的醒目程度依次进行视线运动,或视觉关注点版面的边框或围绕图形外轮廓进行运动,形成对版面或图形的形态认知。视线运动规律中应关注受众的心理反应,有规律、有秩序的进行信息强化和传播。这样的设计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视觉运动,产生视觉舒适感,轻松而无视疲劳,这对儿童受众尤为重要;产生视觉运动秩序,形成层次感和节奏感,营造趣味氛围才能使教育信息能被潜移默化的传播;产生视觉美感,保持视觉的均衡,给受众愉悦、快乐之感,延长受众关注时间。
2 合理运用界面设计中的视觉要素
儿童安全教育网站的界面设计应以儿童受众的视觉感受为根本,在设计中尽量减少儿童认知负担,帮助儿童建立“幻想园地”和“真实记录”。可以通过文字、图形和色彩等视觉要素构建出儿童可认知的“幻想园地”;用模拟训练的交互方式真实记录儿童进行安全教育的互动体验。
对于儿童来说语言的理解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网站中过多的文字会造成厌烦感,可以用趣味的字形,结合呼应的图形,搭配富有情趣的色彩,综合呈现信息。这样以组合的方式运用视觉要素,可以让儿童受众运用创造力和想象力构建自己的“幻想园地”。
观察和体验是儿童获取信息,感知世界的重要手段。在儿童的观察与体验中进入视野的图形会产生丰富的联想。在构成学上常提到形态本身具有的性格特征,如几何形体具有规整、秩序、严肃、稳定、单纯等性格特征,有机形体有着勃勃生机、膨胀、优美、弹性等性格特征,而无规则形体则会有着具有人情味、温暖感、情趣性等性格特征。
色彩鲜亮、丰富、纯度高、对比强的颜色儿童识别力和对其吸引力更强。以儿童为受众的网站应避免大面积的白色运用,用有情感表达的文字和趣味的图形丰富色彩表现空间。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儿童安全组织,提供儿童安全教育计划活动,页面采用了活泼的插画式标识、文字样式和色彩,很容易使儿童融入网站营造的氛围中。
儿童不喜欢成人的浏览方式,他们更容易被图片、声音、视频或其他非文字的形式所吸引,儿童安全教育类网站更应该在交互体验视觉要素上进行关注。
3 结论
儿童安全教育类网站的内容性质和受众特征决定了网站界面设计中视觉引导规律和视觉要素的重要性。网站的建设应该运用视觉引导规律使其产生舒适感、秩序感和美感;将视觉各要素合理的运用,使其卡通化、趣味化、多彩化、情感化;进而实现将教育性内容潜移默化的传达给儿童,使儿童有更广阔的儿童安全防护知识体验空间。
[参考文献]
篇(7)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16-0008-04
近年来,灾难时有发生。这些重大灾难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不仅短期内会给灾民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使之出现急性应激反应,而且往往持续数月或数年,甚至终生,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适应障碍[1],尤其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完整家庭”和“完整躯体”的儿童[2]。对唐山地震孤儿30年后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孤儿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孤儿[3]。这表明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生理上的伤痛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而丧亲这种心理上的创痛却不可弥补。因此帮助丧亲儿童面对以后的人生是很重要的课题。
据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透露,汶川地震一共留下了650名孤儿,实际被收养的只有12例,另外630多名孤儿由民政管理的儿童福利机构来管理。从长远来看,对灾后丧亲儿童的安置工作是一大难题,目前的主要安置方式包括福利机构、家庭寄养以及家庭收养。国内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寄养模式优于福利机构模式[4],而且国外研究表明被收养的儿童比在福利机构长大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紊乱型依恋(Vorria et al,2003)[5]。据此可以推测,收养模式可以帮助儿童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对儿童将来的社会适应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收养是一种更有效的干预方式(Juffer &Van IJzendoorn,2006)[6]。
灾后收养儿童具有双重身份同时也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是灾后儿童,面临的困境是“灾难事实”,可能会出现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7];另一方面,
他们是被收养儿童,面临的困境是“收养事实”,收养暗示着分离、丧失、中断以及与新的父母之间依恋关系的重建(Bowlby,1982)。[9]以往的研究也揭示了收养儿童与收养家庭之间的依恋关系存在其特殊性,此外,收养还意味着风险(被安置前的缺失)以及保护(来自福利机构以及候选养父母的照顾)[9]。在灾难突发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儿童被安置在各种福利收容机构,因为客观原因,常常要面临安置点的变更,这种变更对儿童的依恋关系重建也是有影响的。本文从依恋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灾后收养儿童的心理重建。
一、依恋理论的相关研究
(一)依恋的定义
依恋最早由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比(Bowlby,1968)提出,他把依恋定义为“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它能为个体提供安全和安慰,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与纽带”。这种倾向虽是先天的和普遍的,但是表现在依恋的质量上仍然存在个体差异。根据儿童在面对压力情境下采取的依恋策略,可以把儿童分为安全依恋型、不安全依恋型和依恋紊乱型。安全依恋型儿童在感到不适时更愿意寻求依恋对象的帮助,而且更容易被安抚;而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则会表现出抗拒和回避(Ainsworth et al,1978)[10];依恋紊乱型是被认为最不安全的一种依恋,因为这类儿童在面对压力情境时表现出了前后的不一致性(Main & Hesse,1990)[11]。
(二)依恋和母婴互动
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根据对儿童在陌生实验室情境中对母亲依恋行为的观察,把儿童划分为A、B、C三种类型(焦虑—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安全型依恋、焦虑—反抗型依恋)和八种依恋亚型。
依恋理论有三个假设,它们是依恋理论的核心,包括敏感度假设、能力假设和安全基地假设(Rothbaum & Weisz et al,2000)[12]。敏感度假设是基于母亲对婴儿信号的反应能力;能力假设强调安全依恋的儿童将来的社会功能和情绪调节能力优于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安全基地假设深深植根于鲍尔比和玛丽·安斯沃斯认为儿童把他们的母亲当作探索外部环境的并且在害怕和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可以寻求安慰的基地。
二、收养儿童的依恋研究
收养在依恋建立方面面临明显的挑战,是因为它加入了特殊的情境,例如婴儿与血亲父母依恋纽带的断裂,以及与收养母亲依恋纽带的重建(Portello,1993)[13]。
一项跨国收养的研究表明(Marcovitch et al,1997)[14],收养前的经历对依恋关系影响也很重大,仅仅只是收养不一定必然导致儿童与收养家庭之间依恋关系的阻碍。
一项关于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元分析显示,收养年龄小于一岁的儿童与抚养者建立安全依恋的比例和同龄儿童相当,而一岁后被收养的儿童相对普通儿童则表现出较少的安全依恋,出现更多的紊乱型依恋(Vanden Dries,Juffer,VanIJzendoorn & Bakermans-Kranenburg,2009)。收养儿童在建立安全依恋方面存在风险,追溯原因可能是他们在福利机构的成长背景或者被虐待以及忽视的经历造成的。在一项对收养儿童的依恋关系的元分析中,研究者采用了两种评估方式:观察评估以及观察评估和自评相结合,综合比较了收养儿童与原生家庭儿童以及寄养儿童在依恋关系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原生家庭的依恋关系优于收养儿童,寄养儿童的依恋关系最差。这提示我们对孤儿的安置方式最理想的是家庭收养,被收养的儿童比在福利机构长大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紊乱型依恋(Vorria et al,2003)。
三、影响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因素
(一)收养前的因素
1.灾难对儿童依恋关系的影响
儿童与父母或者养育者之间能否发展出一种安全的依恋关系对儿童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Cassidy & Shaver,1999)。尤其是经历过重大创伤的特殊儿童。创伤儿童中断的依恋历史会使他们处于矛盾之中,既期望进入到新的关系中享受温暖,又害怕新的关系不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同时难以从过去的创伤经历的阴影中走出。严重童年创伤的幸存者常常无法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即无法直接获得对自己的正性感觉。这类困难大部分都被认为是生命中的最初几年发展成型的,这个时候亲子的依恋关系会因为养育者的攻击,某种程度的矛盾、忽视而受到损害(Alen,2001)。儿童以一种被动和怀疑的态度面对新的看护人,这无疑给养父母带来了挑战。
2.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Rutter与Coloert等(2007)的研究显示了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依恋行为的影响:无机构寄养经历的收养儿童、经历机构寄养时间为0~6个月及6~42个月的收养儿童,显著脱抑制性依恋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2%、4%、23%,儿童收养前的不良经历与依恋行为有着显著相关。
在收养的例子中,儿童不能选择他们的优先养育者,而是从福利院或者孤儿院被安置到其他合适的家庭。鲍尔比(1952)的研究指出福利机构的照养对依恋的不良影响。在他的研究中,那些孤儿常常一天更换几个照料者,这些照料者对他们的照顾往往只限于婴儿床上,很少有情感联系。然而,对许多六个月到九个月时被收养的婴儿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只要给予他们足够多的母爱,早期损害的影响可以大大减少。
3.安置点对儿童的影响
灾后儿童一般都会经历从福利院进入收养家庭的这个安置点的转换过程,经历过安置点中断的儿童大多有行为和情绪问题(Robin,Reilly,Luan & Localio,2007)。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关于安置点的转换对依恋关系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从收养家庭得到的数据不足以支持假设,但是从对收养儿童日后的发展来看,这个因素还是值得重视的。Daniel(1993)认为让收养儿童向他们在福利院的养育者和伙伴道别,在情感上作一个结束是有利的。最好的方式是采取渐进收养的策略,即让收养父母花几周时间了解他们的孩子,在福利院的养育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远远地观察孩子,然后逐渐和他们互动。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逐渐地适应这种安置点的转换。
安置点的类型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收养儿童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国际收养的案例比国内收养的案例要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和心理健康的疾病(Juffer & Van IJzendoorn,2005)。另一方面,在自尊方面二者却没有表现出差异(Juffer & VanIJzendoorn,2007)。至于依恋关系方面,由于早期的分离和丧失经历,原籍收养和异地收养孰优孰劣还有待考证。
(二)收养后的因素
1.养父母的养育方式
在早期的依恋研究中,非亲生父母被看作是代替品,他们缺乏与收养子女建立依恋关系的能力。但是安斯沃斯在一项对乌干达母亲的研究中发现,母亲对婴儿的日常照料和社会互动才是建立依恋的关键(Demo & Cox,2000)。正如罗伯森(Robertson)所说:“无论一个母亲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还是寄养母亲或者养母,只要她是儿童早期的照料者,那么她就是儿童的客体,也就是儿童依恋的对象”(Robertson & Robertson,1989)。例如,安斯沃斯发现母亲抱孩子的次数和时间不是建立安全依恋的关键,关键是当孩子寻求母亲的时候母亲是否抱着孩子以及对待孩子的方式,并确保这种反应是即时和敏感的。这会让他们觉得安全,因为母亲的形象随时随地都会满足自己的需要。尽管她的研究是基于血亲母亲和婴儿的关系,结果仍然适用于收养关系。
对婴儿敏感一致的反应是建立安全依恋关系最重要的养育方式。敏感一致的养育方式包括四个维度:(1)温暖或抚育;(2)期望或要求;(3)规则的明确性和一致性;(4)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Bee,1992)。基于这四个维度,可以把父母的养育方式分为三种,宽容型、独裁型以及权威型(Baumrind,1966)。尼尔和福瑞克(Neal & Frick-Horbury,2001)发现,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儿童的依恋类型有显著相关,父母的养育方式是民主型的被试92%属于安全依恋型。泰晤奇(Tavecchio,1999)也发现类似的关系,安全依恋型的儿童感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而不安全依恋型的儿童则感受到更多的控制。
2.收养家庭的子女状况
已有的研究在收养家庭的子女状况对收养儿童的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影响方面的结论上并不一致,贾弗和罗森博姆(Juffer & Rosenboom)在1997年对斯里兰卡、南韩和哥伦比亚的收养儿童和非收养儿童的研究结果表明:收养家庭有无子女对母婴的安全依恋不存在影响。但是该项研究的对象被收养时的年龄都相对较小,对于收养时年龄大于六个月的情况,结论是否能够推广还有待商榷。
3.社会支持
克罗克伯(Crockenberg,1981)提出对收养家庭的社会支持是收养儿童各个方面发展的保护性因素,他发现社会支持和依恋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社会支持是安全依恋的最佳预测指标。社会支持有三种来源:父亲、家庭中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和其他人(包括亲属、邻居、朋友和专家)。
马克文奇(Marcovitch,1995)在与罗马尼亚的收养家庭的父母和养子女的访谈过程中发现,他们提到最有效的社会支持是儿童发展工作坊和支持团体。工作坊提供一些儿童基础发展和养育的知识,收养家庭的成员包括父母和孩子共同构成支持团体。
(三)其他因素
1.收养儿童的年龄
对影响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潜在因素的元分析结果显示:被安置的年龄是收养儿童与养父母之间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如果在一岁以前,儿童能够得到养育者温暖和敏感的照料,他们一般会发展出最基本的信任。多项研究的确证明,如果儿童在他们生命最初的几个月内被收养的话,他们通常会发展出正常的依恋关系(Juffer,Bakermans-Kranenburg,Van IJzendoorn,2008);相反,如果晚几年收养,他们发展出不安全依恋的风险会大大增加(Vorria et al,2006)。罗伯森提出年龄较大的儿童与收养家庭的依恋关系更弱,可能和年龄较大的儿童经历了更多的分离和丧失有关,收养时的年龄越大,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2.收养儿童待在新家庭的时间
收养儿童与养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更容易从原先遭受过的创伤当中恢复过来。贾弗和范(Juffer,Van IJzendoorn,2005)的元分析显示,那些与养父母生活超过12年的收养儿童在行为问题方面,比与养父母相处时间更少的儿童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可以推测,收养家庭与儿童相处得时间越长,越利于儿童安全依恋的
建立。
四、依恋重建的方法
(一)对收养家庭的干预
对收养家庭进行干预主要是对收养父母进行敏感性训练和授与依恋巩固的技术(Juffer et al.,2008)。一项对干预技术的元分析表明,这些干预对敏感性的提高、安全依恋的建立以及不安全依恋的降低的确有效(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2003)。
预防性干预主要针对养父母进行依恋理论、养育技能等各方面的培训,以帮助养父母与孩子从一开始就能够向安全依恋的轨道发展。这主要基于依恋理论的重要假设:依恋质量是由母亲对婴儿发出的寻求亲近和接触信号的反应的累积结果。
(二)对不良依恋儿童的干预
矫正性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在收养过程中出现的较大的问题,即儿童出现了依恋障碍(attachment disorder)。治疗的基础假设是,儿童压抑了阻碍依恋形成的早期消极经验的愤怒,临床干预主要是帮助儿童释放这些愤怒,并让儿童信任新的父母是可以信任的看护人。治疗师通过努力鉴别和打破儿童的心理防御机制,给予强制性支持和抚触来打破破坏性循环,重建儿童的信任。使用的具体方法包括游戏治疗、家庭治疗等。治疗的实施过程一般持续两周共30小时,治疗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帮助父母学习有效的养育技巧上,使父母知道如何对孩子予以关爱,正确对待与养育孩子,使孩子健康成长。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本,王学义,孙贺祥等.唐山大地震对人类心身健康远期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
200-202
[2]李磊琼.地震后儿童心理干预与转变过程探索[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6):526-528.
[3]王丽萍,张本,姜涛等.唐山地震孤儿30年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23(8):558-563.
[4]崔丽娟,扬志勇.家庭寄养对孤儿社会成长作用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2,25(1):37-39.
[5]Vorria,P.,Papaligoura,Z.,Dunn,J.,vanIJzendoorn,M.H.,Steele,H.,Kontopoulou,A.,et al..Early experiences an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of Greek infantsraised in residential group care[J].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03,44:1208-1220.
[6]Juffer,F,& Van IJzendoorn,M.H..The Emanual Miller memorial lecture 2006:Adoption as intervention.Meta-analytic evidence for massive catch-up and plasticity in physical,socio-emotional,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06,47:1228-1245.
[7]郑毅.汶川地震对儿童的心理影响及救助措施[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8,34(9):519-521.
[8]Bowlby,J..Attachment and loss (Vol.2)[M]New York:Basic Books,1982.
[9]Rutter,M..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In J.Rolf,A.S.Masten,D.Cichetti,K.H.Nuechterlein,& S.Weintraub(Eds.),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pp.181-214)[M].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0]Ainsworth,M.D.S.,& Blehar,M.C.,Waters,E.,&Wall,S.Patterns of attachment:A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M].Hillsdale,NJ:Erbaum,1978.
[11]Main,M.,& Hesse,E..Parents'unresolved traumatic experiences are related to infant disorganized attachment status:Is frightened and/or frightening parental behavior the linkingmechanism?InM.T.Greenberg,D.Cicchetti,& E.M.Cummings(Ed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Attachment in the preschool years:Theory,research,and intervention(pp.161-18)[M].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12]Rothbaum,Rothbaum,F.,Weisz,J.,Pott,M.,Miyake,K.,& Morelli,G..Attachment and culture: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American Psychologist,55(10):1093-1104.
篇(8)
94-142公法确立了非歧视性的鉴定、个别教育计划、最少受限制环境即根据儿童障碍程度确定不同的教育安置形态的等级特殊教育服务体系(TheContinuumofSpecialEducationServices,包括普通班、巡回教室、资源教室、自足式特殊班、特殊学校、医疗机构等)等原则。全纳教育思想是在回归主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全纳教育并非回归主流的自然延伸。相反,全纳教育是在批判、反思回归主流教学实践失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krtic,1991)。这些批判集中于94-142公法中与特殊儿童鉴定程序相对应的等级制安置体系。例如,全纳教育的倡导者W.Stainback和S•Sta-inback(1984)对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隔离、各自平行发展的双轨制体系(dualsystem)提出明确的批评,认为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应该“重新组合、建构、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教育体系以满足所有儿童的学习需要。”(p•102)。
美国教育部前助理行政长官,Will(1986)也指出回归主流存在着:1、不科学的鉴定与障碍类别的划分导致特殊教育效率低下。2、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各自平行发展,二者不能很好地协调以满足学生的需要。3、等级制服务体系中儿童容易被隔离、歧视。4、家长和教师经常对儿童的教育安置,即儿童应该在哪一等级中受教育,见解不同,容易造成冲突。可见,回归主流及94-142公法中用以确定儿童安置类型的特殊教育服务体系是根据儿童的障碍的程度来确定儿童教育环境受限制的程度,即隔离的程度的,是不公平的等级制度,违背了回归主流本身所追求的教育平等的理想;并容易将儿童的障碍作为教育问题的原因,而非学校本身条件的不足①。全纳教育的支持者们呼吁重组学校、破除教育的等级结构,使普通学校成为满足社区内所有儿童学习需要的地方。
二、何谓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的思想自W.Stainback和S.Stainback(1984)明确提出后就成为特殊教育领域讨论的焦点。尽管许多国家都将全纳作为特殊教育发展的理想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但实际上人们对于全纳教育是什么仍然众说纷纭。以下是西方文献中对全纳教育的一些解释。全纳教育是家长、教育者、及社区工作者发起的运动。它寻求创设以接纳、归属、社区感为基础的学校。全纳教育通过在邻近学校的高质量(highquality)、年龄适合(Age-ap-propriate)的普通教室来实施,并得到所有儿童欢迎、承认、甚至强调他们的价值。全纳计划寻求建立以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为目标的、尊重个体差异为基础的支持性社区(Salend,1998)。全纳教育是指在普通学校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教育环境里教育所有的儿童。
它更关心的是特殊儿童的权利而非学校校长、教师、及心理学工作者的专业判断与建议(Bailey&duPlessis,1998)。全纳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和信仰系统。全纳学校的基本信念包括ABC:即接纳(Acceptance)、归属(Belongs)、和社区感(Com-munity)。全纳强调如何支持每个儿童特别的秉赋和需要,努力使校区内的每个学生都感到被接纳、安全、及成功(Falvey,Givner,&Kimm,1995)。全纳是一种价值倾向。它以所有的特殊儿童都有权与同龄儿童一起在自然的、正常的环境中生活与学习为前提。它强调给予学生平等参与所有的学校活动的机会(Smith,Polloway,&Dowdy,2001)。全纳是指在最大程度上使有特殊儿童在普通教室受教育的努力。它倾向于让学生在普通教室,而不是抽出(pull-out)在普通教室外接受相关的支持与服务(Zionts,1997)。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全纳的定义很模糊,内涵与外延很不明确,很难为特殊教育实践与教学提供准确的、具有操作性的指导。因此,如其说全纳教育是一个准确的教育学术语,倒不如说它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价值追求,亦或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潮。所以在理解全纳教育的时候,不能仅仅将其视为简单的教育概念,而应该更多的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来理解、分析。
三、回归主流、一体化、及全纳教育概念之间的关系
全纳教育与回归主流或一体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它们有着相同的社会文化与哲学基础,都源于美国19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以西方个人自由、社会平等等价值为社会文化基础;倡导“零拒绝”的哲学。多数时候专业人士都是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些概念的,很少注意到它们间的不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更是很难鉴别究竟是在进行回归主流还是全纳教育。这些概念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回归主流本质上仍然是以特殊儿童应该在普通教室以外的隔离环境中受教育为前提的,它要求特殊儿童必须达到某种预定的标准(鉴定结果)才能被普通教室接收,这意味着儿童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赢得在普通教室接受教育的权利(Booth&Ainscow,1998)。所以回归主流由一系列不同等级的安置形式组成。全纳教育则认为特殊儿童本来就应该属于邻近学校的普通教室,他们不仅有权在普通教室里受教育,而且也应该在那里接受相关支持与服务。
因此,回归主流可以看作特殊儿童在普通教室的部分或全部学习时间的安置,而全纳教育则是全部时间都安排在普通教室里。它们的区别可以形象地归纳为:回归主流学校经常问“我们能为特殊儿童提供教育么?”,而全纳教育学校则问“我们怎样为特殊儿童提供教育”?一体化通常泛指将特殊儿童从较多向较少隔离的环境中转换、过渡的过程,因此回归主流和全纳教育都可以被包含在一体化教育运动中(Ainscow,Farrell,&Tweddle,2000)。在西方文化背景里,主流环境被认为是儿童最标准、正常的安置环境。一体化强调调整学校的物理环境以促进学生逐步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全纳教育则是一种重组学校资源、改善教学策略以适应学生多样学习需要的意愿与价值倾向(Johnstone&Warwick,1999)。总之,回归主流是一种使特殊儿童尽量在正常教育环境中受教育的哲学思潮,一体化强调的是一步一步向普通教室转换的程序、过程,而全纳教育则与特殊儿童在正常环境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有更大的关联(Bailey&duPlessis,1998)。
四、关于全纳教育的争论
人们关于全纳教育争论的焦点不在于“特殊儿童能否被全纳?”,而是儿童应该如何全纳:应该以激进的方式完全容纳进普通教室,即Fullinclusion(暂译作“完全全纳”);还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有选择的全纳,即Selectivein-clusion(暂译作“部分全纳”)?
(一)、完全全纳派的观点。完全全纳是指对特殊儿童进行全日制的普通教室安置。它是一种单一的安置形式,认为不应该根据儿童的障碍程度来安排他们在普通教室学习的时间,而应该在普通教室里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要,普通教师应该在特殊教育专业人士的支持下承担教育特殊儿童的主要责任(Zionts,1997)。完全全纳教育的支持者们主要有以下观点:1、将特殊儿童抽出教育、对他们使用标签(label)的做法是低效率的、不公平的(Nelson,Ferrante,&Martella,1999)。2、所有的儿童都有学习和成功的能力,学校应为他们的成功提供足够的条件(Villa&Thousand,1995)。3、所有的儿童都应该在邻近学校内的高质量、年龄适合的班级里平等地接受教育。学校必须成为适应所有儿童多样学习需要的场所(Sage&Burrello,1994)。4、应该让特殊儿童在具有接纳、归属、社区感的氛围中接受教育(Salend,1998)。5、在普通教室里,特殊儿童通过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合作教学、学生之间的伙伴学习、以及提供的各种相关服务而获益(Cook,Semmel,&Gerber,1999)。可见,在完全全纳教育者的眼里,全纳教育是不需经过任何经验或研究来证明的,它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伦理上的追求。
(二)、部分全纳派的观点。部分全纳即让特殊儿童部分学习时间在普通教室学习,它认为普通教室安置并不适合所有的特殊儿童。它支持等级特殊教育服务体系,尤其是资源教室的存在,提供从最多(隔离的学校或机构)到最少(普通教室)限制的多种教育安置选择(Smith,Polloway,&Dowdy,2001)。部分全纳教育支持者对完全全纳教育的批判集中于它的基本假设,即所有的儿童都能在普通教室里接受最适合他们的教育。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一刀切”的做法(Lewis&Door-lag,1995)。Daniel和King(1997)认为在普通教室里,能力强的儿童可能会因内容简单而厌倦,特殊儿童又因赶不上教学的平均进度而焦虑;完全全纳教育者对特殊儿童社会适应太过重视,很容易将学业成绩作为次要的任务。部分全纳教育者因此认同等级制特殊教育服务体系的作用,相信特殊儿童的安置选择应以儿童障碍的性质与严重程度为基础。他们的这些基本观点与回归主流很相似。有的部分全纳教育者还认为完全全纳的观点太理想化,如Low(1997)指出:“对完全全纳的追求是一种幻觉,它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p.71);Croll和Moses(2000)也认为“完全全纳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在道德上高高在上,但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却缺乏保障”(p.2)。因此,多数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完全全纳的观点过于极端、理想化,大多支持特殊儿童在必要时到资源教室接受一段时间的教育与服务。更多的情况则是观念上、原则上支持完全全纳教育的理想,但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却采取部分全纳即回归主流计划的做法。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回归主流、一体化、及全纳教育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实践中则没有什么不同,至少在目前阶段是如此。
五、启示
国内学者一般都承认我国自80年代以来实行的随班就读是在西方一体化或回归主流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由我国特殊教育工作者根据我国国情探索出的对特殊学生实施特殊教育的一种形式。“与西方的一体化、回归主流在形式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在出发点、指导思想、实施办法等方面有中国的特色”(朴永馨,1996,p.43)。我国随班就读模式既受国际特殊教育理论如回归主流或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性;又考虑了我国的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实际的条件,即具有民族性。然而,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全纳教育的概念很模糊,与一体化教育、回归主流的分野并不明晰,尤其是部分全纳教育的观点与回归主流没有什么不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则更无区别。因此,从广义地理解全纳教育思想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忽略全纳、一体化、回归主流思想的细微区别,将所有试图把特殊儿童部分或全部学习时间安置于普通教室的努力都看作全纳教育。从这个角度讲,随班就读应该属于全纳教育运动范畴。至于随班就读的民族性,它与全纳教育的理念并不冲突。因为全纳教育仍然处于摸索、发展阶段,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篇(9)
关键词:儿童;安全座椅;造型结构
Key words: children;safety chair;modeling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U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4-0309-02
0 引言
儿童安全座椅是一种系于汽车座位上,供儿童乘坐且有束缚设备的装置。在汽车发生碰撞或突然减速的情况下,儿童安全座椅可以减小对儿童的冲压力,并且通过限制儿童的身体移动以最大限度保障儿童的安全。
据了解,目前在欧洲,儿童安全座椅非常普及,甚至成为一些整车出厂的必备辅件。许多国家有明确法律规定:儿童乘车时要配备安全座椅[1]。在我国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率非常低,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有少量的人群使用。鉴于此,拟设计一款安全、舒适、易用的儿童安全座椅,以满足儿童群体出门安全、乘坐舒适的基本要求。
1 设计前期研究
1.1 儿童的身体特点 根据测试,汽车以50km/h的速度在行使的过程中突然发生碰撞或刹车,车内的物体会产生30-40倍自身重量的冲击力。假若儿童体重10kg,碰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就有300-400kg,成人很难护住儿童,儿童会被甩出车外或在车内发生二次碰撞,他们受到伤害的严重程度远比成年人更高[2]。
儿童容易受伤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没有发育完好的颈部和骨盆,身体不成比例、比较脆弱。婴儿的骨骼是软的,三岁之后软骨才开始变硬,骨化过程会持续到青春期,此期间肌肉与颈部韧带也逐渐形成。儿童时期的颈椎骨是扁平状的,无法像成年人的鞍状颈椎骨那样在人头部前倾时可相互支持。具有发育完好骨骼的成年人在交通事故中身体内部器官收到的伤害会减小,而儿童的骨盆没有骨骼结构,只有到了青春期才会发育完整。
1.2 市场上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现状 大多数儿童座椅在理论上是安全的,但事实上由于在使用方式上不够方便,使得有些座椅安全性降低。
很多儿童安全座椅短时间使用还比较舒适,长时间使用就会很不舒服,甚至会引起儿童的抵触心理。
许多儿童安全座椅的设计与汽车内部设计不协调。
儿童群体类产品越来越注重产品材料的选择及使用方式的改变。
大部分儿童安全座椅的购买者是母亲。
2 设计定位
通过对使用群体、市场现状、同类产品等方面的调研,基于人机工程学、产品造型艺术及设计心理学及等理论知识研究,设计一款儿童安全座椅,为3~10周岁的儿童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经过概念设计的学童型安全座椅,造型结构的设计以最大合理化提高儿童乘车的安全性、舒适性和易用性,同时保证与汽车内部的匹配性。
3 设计构思方案
设计构思方案一见图1,该方案椅背的设计如同母亲的怀抱,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求,不仅从心理上会让儿童产生一种强烈底被保护的感觉,同时从生理的角度上保持与儿童身体的贴合性。
设计构思方案二见图2,该方案根据人机工程学原理,座椅侧翼加宽,头枕可根据儿童的身高调节到合适的高度,提升长期乘车的舒适性。
设计构思方案三见图3,该方案综合了方案一和方案二的优点,将其确定为最终设计方案。结合产品自身的特点,基本确立了完整的设计方案。
4 设计分析
4.1 整体造型设计 根据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座椅的整体造型设计犹如母亲的怀抱。参考儿童的身体尺寸,座椅的尺寸为500mm×460mm×650 mm[3]。座椅的倾斜度、座椅的前后位置、头枕的高度可根据儿童的身体随意进行调节。宽大的侧翼,深陷的头枕,座椅的可调节性,不仅能从生理上保障儿童头部和骨盆的安全性,同时能让儿童从心理上感受到母亲温暖的怀抱,提升乘车的舒适性,减轻长途旅行的疲劳感。
4.2 坐垫设计 为了满足儿童长时间乘坐舒适的需求,坐垫采用蜂窝式充气坐垫。充气式坐垫一方面可以加速儿童的血液循环,提高舒适性,降低长时间乘坐的麻木性;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汽车在行驶中碰撞和振动产生的影响,提高安全性[4]。
4.3 卡扣装置设计 卡扣装置的设计必须即要保证锁紧状态下的牢固性,避免意外滑开脱落的危险,又要易扣易解,方便家长操作。新设计的卡扣在锁紧状态下指示灯会亮起,方便家长确认儿童的安全性。
4.4 绑带设计 肩部绑带应该有适当的束缚感,又不会令儿童感到不适。绑带太紧,长期使用会影响儿童胸廓发育,发生肋骨下部凹陷。座椅底部的绑带通过拔起紧绷的卡扣,自动锁紧。肩部绑带和底座固定绑带设计都要遵循易扣易解的原则,提高易用性。
4.5 座椅面料设计 座椅面料选用布艺类材料。儿童的肌肤比较敏感,因此座椅的包裹材料应采用精选的无毒无刺激的柔软面料。
4.6 配色方案设计 色彩能够赋予产品进一步的情感特征。基于儿童天性活泼、好动的心理特征,座椅主色调为绿色,辅以橙色。绿色所传达的是清爽、理想、希望、生长的意象,橙色明亮活泼。
5 结语
充分的市场调研可以让设计师对所设计的产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从而更明确地把握设计方向。儿童安全座椅的设计不仅要从产品造型艺术和心理学的角度考虑其造型的美观性,更要根据人机工程学等知识设计座椅,提高乘车的安全性、舒适性和易用性。希望儿童安全座椅在我国也能尽快普及,并能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保障儿童乘车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温为才.欧亚优秀工业设计案例分析:从调研、草图到模型的秘密[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篇(10)
道路交通伤害是儿童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1]。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给儿童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创伤,以及沉重的社会负担。据报道,中国每年有超过25000 名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2],死亡率是欧洲的2倍,美国的2.6倍[3]。目前我国机动车数量激增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快速,而随之而淼亩童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风险也显著提高,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本文调查了解上海市长宁区儿童乘车安全措施使用及父母对此的认知、态度情况,为预防儿童乘车伤害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在长宁区居住半年以上、拥有私人轿车且日常使用轿车接送孩子的0~6岁儿童父母。
根据公式N=Uα2*P(1-P)/δ2,以P=30%, U0.05=1.96,δ=0.08*30%=0.024计算,得到样本量为1401例,考虑无应答及抽样方法的设计效率,适当扩大样本量,即0~3岁和4~6岁儿童每层各需要调查1500人。
针对0~3岁儿童家长,以全区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通过计免/儿保门诊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对象。针对4~6岁儿童家长,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长宁区42所幼儿园和21所托儿所(包括总部和分部)中分别随机抽取36所和18所,对抽中托幼机构中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家长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主设计的问卷,经过多轮专家论证和预试验后确定。主要内容有:人口学信息,如家长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孩子的年龄、性别等;儿童乘车及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相关情况;家长对儿童安全座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和使用意识、态度情况。
0~3岁儿童家长在计免和儿保门诊候诊时,由调查专员发放问卷,家长现场自行填写,确认无缺漏项后回收。4~6岁儿童家长,则由经过培训的卫生老师发放,家长根据填写说明,在家填写完成后交给卫生老师回收。
1.3 质量控制
对社区的调查专员和幼儿园卫生老师进行培训。调查现场有调查专员对问卷内容进行解释,并对填写好的问卷进行完整性审核质控。带回家填写的问卷同时附填写说明。问卷回收后,由社区和疾控中心质控员分别抽查10%、5%进行电话质控, 以验证问卷真实性(核心信息符合率92.35%)。
调查共发放问卷3760份,回收问卷3568份,应答率为94.89%。在回收的问卷中,重要信息缺失的废卷和非父母回答的问卷未纳入分析。总共有3509份有效问卷纳入分析,有效应答率为93.32%。
1.4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0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平行双录入法录入数据。 使用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采用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3509份,其中男童占51.4%,女童占48.6%。小于1岁组儿童占14.8%,1-3岁组占39.6%,4-6岁组占45.6%。问卷应答者中,男性占33.0%,女性占67.0%;大多数应答者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88.6%);65.0%的家庭年收入在12-120万之间(表1)。
2.2 儿童乘车相关行为
表2显示,0-6岁儿童乘车方式中,以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比例最高(44.1%),其次是由大人怀抱乘车(占28.1%),18.0%独自坐座位系安全带,9.8%独自坐座位不系安全带。不同年龄组儿童的习惯性乘车方式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2=586.7,p
对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进一步分析其使用的座椅类型。使用最多的是幼儿型安全座椅(65.1%),其次是提篮式安全座椅(17.0%)和增高型安全座椅(12.5%)(见表3)。不同年龄段间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类型有显著统计学差异(?2=406.3,P
儿童在乘车时的乘坐位置以后排为主,仍有1.8%的安全座椅安装在前排,未使用安全座椅的儿童有7.2%习惯性乘坐前排副驾驶位置(见表4)。儿童安全座椅安装位置,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2=2.2,P=0.396)。未使用安全座椅的儿童中3岁及以下儿童乘坐比例高于4岁及以上年龄组,但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2=4.2,P=0.121)。
2.3 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态度和认知情况
调查显示,66.1%的家长认为儿童乘车时使用安全座椅是最安全的乘车方式,但仅37.5%的对象认为掌握了安全座椅的相关知识。
本次调查共涉及6条儿童安全座椅相关的核心信息。儿童安全座椅核心知识总知晓率为67.1%,其中知晓率最高的为“父母抱着孩子乘车,不能在汽车发生碰撞时有效保护孩子”(81.5%),其次是“儿童乘车时是否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与车速无关”(78.3%)。知晓率最低的为“1米4以下儿童乘车不能坐在后排座位上并系上安全带”(43.0%),其次是“1岁以下的婴儿应使用反向安装在汽车后排座位上的儿童安全座椅”(47.6%)(见表5)。836人(23.8%)的调查对象知晓全部核心知识,183人(5.2%)全部回答错误(见表7)。
而对于关于儿童乘车的描述“短途旅行需要使用安全座椅”、“低速行驶需要使用安全座椅”、“开慢点不能确保儿童乘车安全”的认同率分别为72.7%、74.7%和76.3%。83.1%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对安全座椅使用强制立法。
除了认为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最安全和知晓一岁以下婴儿应使用面向后的安全座椅两项外,其余知识和态度条目,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表5)。
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家长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变量赋值如下:应变量以知识得分大于等于4分为认知水平较好,赋值为1,以低于4分为认知水平较差,赋值为0;儿童性别:女孩为0,男孩1;儿童年龄:4~6岁为0,其余为1;调查对象性别:女性为0,男性为1;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大专以下为0,其余为1;家庭年收入:6万以下为0,其余为1。
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的调查对象儿童乘车安全相关知识认知水平也较高。见表6。
2.4 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认知与乘车行为相关性分析
分析调查对象安全座椅使用的态度和知识与儿童是否使用安全座椅的关系(表7)发现,认为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家长,其子女座椅的安全座椅使用率最高,达52.5%,对最安全乘车方式的认识不同,安全座椅使用也呈现显著的统计学差异(?2=256.5,P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长宁区0-6岁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的比例为44.1%,明显高于北京的一项调查结果[4],但远低于美国76%的使用率[5];其中,0-3岁年龄组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49.8%)好于4-6岁组,也较2012年该区某调查中27.7%的0-3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6]。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儿童安全座椅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中儿童伤害的发生率和死亡率[7],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在高收入国家非常普遍,但中国尚未具有国家层面出台的儿童乘车安全座椅强制性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许多家长交通安全意识薄弱、违法驾驶行为多见。本次调查中,有38.2%的0-3岁儿童乘车时是由大人怀抱的,更有46.8%的4-6岁儿童乘车时独自坐在座位上,独自坐在座位上的4-6岁儿童有超过三分之一还不系安全带,甚至还有7.2%的未使用安全座椅的0-6岁儿童是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位上。这些不安全的乘车行为使得儿童乘车安全未受有效保障,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得引起驾驶员分心,形成驾驶安全隐患,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儿童伤害的发生或加重。为此,今后我们应该强化舆论宣传,交通、卫生、教育等多部门联合,倡导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以不安全的儿童乘车行为为重点开展社区干预。
本次调查发现,0-6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随家长对安全座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的改善而提高,而且家长对安全座椅的使用态度与儿童安全座椅的实际使用行为密切相关,家长认同安全座椅是最安全乘车方式的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最高。但是,总体上来看,调查对象对于安全座椅的认知水平还较低,核心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67.1%,仅23.8%的家长知晓全部核心知识,存在不少认识误区,例如超过一半的家长并不知晓“1米4以下儿童乘车不能坐在后排座椅上并系上安全带”、“1岁以下的婴儿应使用反向安装在汽车后排座位上的儿童安全座椅”,近1/3的家长对儿童短途、低速乘车时的安全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仍持有“短途旅行不需要使用安全座椅”、“低速行驶不需要使用安全座椅”、“开慢点也可确保儿童乘车安全”这类错误的观点,与陈晓军[8]、李海[9]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根据logistic回顾分析家长知识水平的的影响因素显示,文化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对象其儿童乘车安全相关知识水平也较高。尽管长宁区属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上海市中心城区之一,但其0-6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不小的差距,除缺乏强制使用立法等政策大环境支撑外,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不高的认知水平可能是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强化儿童安全乘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特别是应重点加强对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有关儿童安全乘车的认知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家长掌握相关知识,改变对儿童安全乘车的认知,进而采用更可靠的儿童乘车安全措施以确保儿童乘车安全[10]。
参考文献
[1] 林穗,方胡艳,蒋林,等.广州市5岁以下儿童2001―2010年意外死亡趋势流行病学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2,33(12):1258-1260.
[2] 段佳丽,符筠,耳玉亮,等.北京市中小学生交通伤害流行现状及其相关危险行为[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8):1131-1135.
[3] Routley V, Ozanne-smith J, Li D, et al. Pattern of seat belt wearing in Nanjing,China [J]. Inj Prev,2007,13(6):388 -393.
[4] Purc-Stephenson RJ,Ren J,Snowdon AW.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arents’use and knowledge of car safety seats in Beijing,China[J].Int J Inj Contr Saf Promot, 2010,17(4):231-238.
[5] Macy ML,Clark SJ,Freed GL,et al.Carpooling and Booster Seats: A National Survey of Parents[J].Pediatrics,2012,129(2):290-298.
[6]姜玉,夏c华,周鹏,等. 0-3岁儿童的父母有关儿童乘车安全相关知识和行为调查[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5,19(1):31-34.
[7] Barraco RD,Cheng JD,Bromberg WJ,et al.Child Passenger Safety Workgroup of the EAST Practice Management Guideline Committee Child passenger safety:an evidence-based review[J].J Trauma,2010,69(6):1588-1590.
篇(11)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图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分裂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4.
[2]吴红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基础教育,2004(12):15.
[3]宛容,兰文杰.沙利文人格发展思想探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44.
[4]杨汉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研究,1998(4):63.